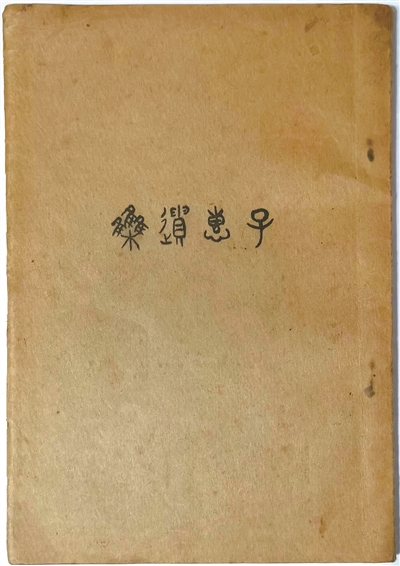1926年9月15日,徐志摩在他编的北京《晨报副刊》头版头条发表《一个启事》,文中说:“我们《诗刊》同人本是寥寥可数的,但谁想到在三个月间,我们中间竟夭折了两个最纯洁的青年!杨子惠(宁波人)在七月间得伤寒病死在上海,前六日(九月九日)刘梦苇又在法国医院亡故。”徐志摩对青年诗人杨子惠和刘梦苇的早逝表示“叹息”和“追悼”,郑重地征文纪念他们。
《子惠遗集》
稀见的《子惠遗集》
杨子惠(1904—1926)原名杨世恩,是徐志摩创办的《晨报副刊·诗刊》的重要作者,故徐志摩命为“《诗刊》同人”。后来陈梦家编《新月诗选》(1931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就入选了他发表在《晨报副刊·诗刊》上的《回来啦》《铁树开花》《她》三首诗,称之为“最可珍惜的努力”。《回来啦》后又入选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35年12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杨子惠与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和孙大雨(子潜)有“清华四子”的美誉,“四子”都有诗名。
徐志摩在《一个启事》中曾预告刘梦苇遗诗集《孤鸿》将问世,不料一直未见。但杨子惠逝世不到半年,《子惠遗集》就悄悄地问世了。此书32开本,道林纸精印,书名篆书,封面朴实无华,无版权页。书前有杨子惠木刻像,又有序:
今年七月十八日下午四点钟,“天地浑黑”的时候,子惠呼着他最后的一口气,同他一切的亲友永诀了!当五月二日子潜同子惠离京的时候,我只以为江南的青山和绿水可以洗涤他平日的忧郁。那知呀,此行竟使他伤生!
这集子是子惠多年来文艺上的尝试,他素性自虚,发表的东西非常的少;自己又不留稿本,随做随撕。所以子沅,懋德,同我经了几月的搜罗,所得到的还只有这十来篇东西,大都是在《清华文艺》和《晨报诗镌》上发表过的,集成《子惠遗集》,印赠给子惠的亲友,以志哀念。
诚如仲婴说:“宝贵的生命,尚如河流的逝去,区区数页字迹,何堪相追比拟?”
唐亮 十五年十二月
此书编者唐亮应与朱湘、孙大雨均熟。书之前环衬右上角有黑笔题字:“本强兄存”,或出自唐亮之手。全书共收入新诗《安眠》《回来啦》《铁树开花》《电杆的归去辞》《赠言》《让我安然归去》和《她》两首,短篇小说《或人的恋爱》《创世纪略》和《离国前一日》,以及长篇游记《热河东陵的旅行》,杨子惠的新文学创作大都搜罗于此矣。且录《新月诗选》未收的一首《她》,以见杨子惠新格律诗追求之一斑:
闪烁的明星黯淡在她的眼中,/乌云乱堆在枕上飞扬不起;/我象是赤日挣扎在天狗喉咙,/看见她奄息在水纹的被里。
忽然象宝鼎里飘出一缕轻烟/细细的一声问我耳边飞来:/莫害怕啊!她决不会辞别人间,/要没有美丽还成什么世界?
杨子惠是第一位逝世的“新月派”诗人,而这部《子惠遗集》是继闻一多《红烛》、朱湘《夏天》和徐志摩《志摩的诗》之后,“新月派”的第四种作品集,也是新文学史上第一种已逝作家的纪念集,意义非同一般。由于是印赠“子惠的亲友”,非卖品,《子惠遗集》到底印了多少册已不可知,印数之少可以想见,《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失收了。日前有幸得到,诚可喜也。
《诗歌月报》
再说钱君匋的新诗
一年以前,我写过《有七篇序跋的<水晶座〉》一文,介绍新文学装帧大家钱君匋唯一的新诗集《水晶座》。此文末尾称“可惜他后来未能坚持新诗创作”,这句话没有说对。因为在《水晶座》出版之后,钱君匋仍偶有佳作发表。
1934年4月,上海文坛出现了一种新诗月刊《诗歌月报》。署“上海诗歌月刊社”编,“流露社”发行。每期《诗歌月报》设“诗的创作”“诗的翻译”两部分,后来又增加了“诗的理论”部分。已知李微、孟宗、陆印全、吕绍光、王一心、林野六位是诗歌月刊社社员,这些名字现在已十分陌生,但当时都是活跃的青年诗人,也都是《诗歌月报》的作者。该刊当然也向名家约稿,朱湘(遗作)、宗白华、李金发、陈梦家、方玮德、赵景深、许幸之、艾青、蒲风、力扬、林庚等都在该刊亮过相,作者中还有南方诗人侯汝华和林英强等,还有很少为研究者提及的徐仲年和史卫斯,曾是创造社大诗人的王独清也给该刊写过信。于是,我们也欣喜地见到了钱君匋的新作。
钱君匋在1934年5月《诗歌月报》第2期发表了两首诗,一为《耳环》:
闪着鱼腹的白,/染着栀子的香,/在小绛珠串的一端。
蜷屈的玄色的云鬓,/摩挲地,/在小绛珠串的另一端。
她亲腻了朝霞的耳根,/她熟视了花唇的热吻——/终朝打着精致的秋千。
另一为稍长的《兆丰花园之冬》:
常绿的灌木,/冬日的光:/一列孔雀展开着锦屏,/在有金色之感的草上。
獭皮的领,/吐出盛装的女面,/冬日的光暖得使她们/变成一堆一堆,紫赭的,明朱的,衰绿的,玄黑的。
可以感到朔风的一隅,/三枝空树,/没有人的呼吸,/有沙漠之感的草根。
到了同年8月《诗歌月报》第5期,钱君匋又发表了一首《归舟》:
水浪,舞女的眼波样,/拍着我的归舟。/荡着笑涡的圆圆的萍。
橹声和岸边草叶间的水声对语着,/现代的妩媚的情话哪。
流云和野鸟的影在水心了,/织成往昔的宫锦一样,/不,看他又分散了。
由此可见,钱君匋并未忘情于新诗创作,偶有所感即诉之笔端。三年之后,即1937年3月,他又在戴望舒主编的上海《新诗》第6期上发表了一首《路上》:
一乘双飞掠过柏油的路面,/只扬起一些青烟的轻尘。/举着千臂的冬树,/在路上揖着,迅速地退去。
幽歌着的电讯木,/三角与立方组成的住宅,/衬着青的远天。/一切平静,我独自步行着。
这些意象别致的小诗表明,虽然仍有生动描绘乡村景色的诗如《归舟》,但钱君匋已把新诗创作的重点转移到他朝夕相伴的都市生活上来了。《耳环》写都市时髦女子的耳环,细腻艳丽;“兆丰花园”是当时上海滩的著名公园,写兆丰冬景,也写到公园动物园中的孔雀,既写实,又有些许现代派诗的况味。《路上》更写到了现代都市常见的柏油路、电讯木和“三角与立方组成的住宅”。可惜他写得少,并未引起现代诗研究者更大的关注。
至于《诗歌月报》,虽然总共只出版了七期,在我看来却是在1930年代上海文坛上,《新月》之后、《新诗》之前的一份能够展示不同追求、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新诗的诗刊,颇为难得,现在也几乎被遗忘了。
文/陈子善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