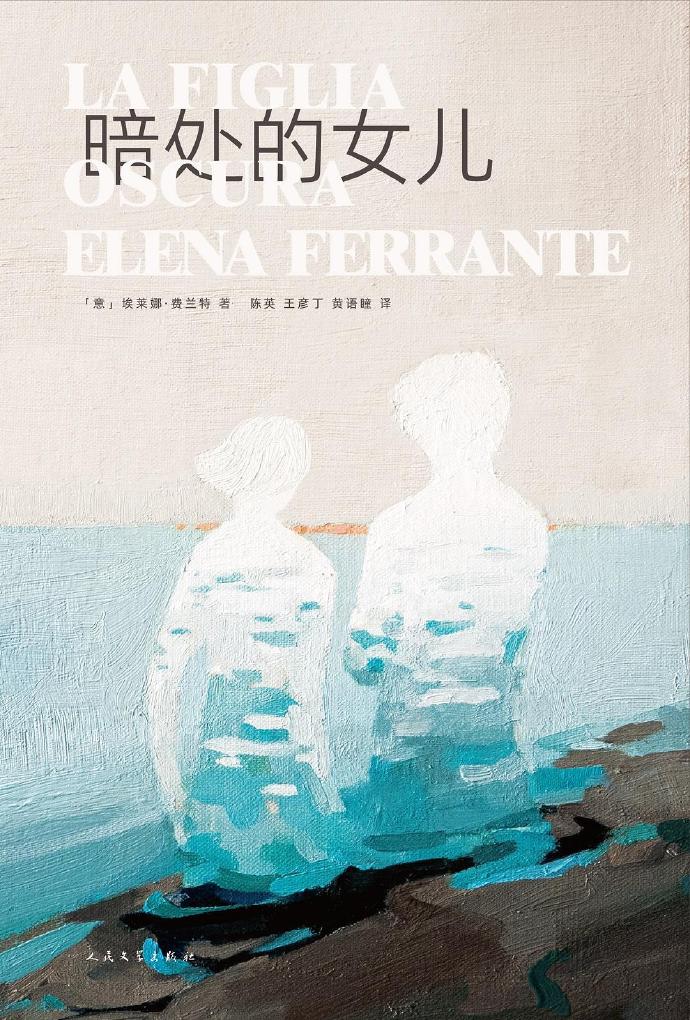在当代文学光谱中,埃莱娜·费兰特是最擅长于挖掘女性隐秘内心的作家之一。早在引爆“费兰特热潮”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之前,她就已然是一个展露出烁烁才华的成熟作家了。
在《暗处的女儿》中,费兰特的叙事有一种不受束缚的自由,人物在不同的场域中丝滑无阻地穿行——过往与当下、自我与他者、母亲与女儿、思绪与现实,所有交界的界石在笔下消融。尤其是人物意识与现实的脱轨,不经任何提示直接转接;意识开始漫漶,现实被淹没,过往伴随着意识的浮想联翩不断肆虐与侵蚀着主人公;意识不绝如缕,有时甚至像套娃一样,在回溯中进行回溯。《暗处的女儿》同样延续了《被遗弃的日子》中那混乱同时私密难以启齿的心灵湍流,费兰特持续地挑战着内心私密性的极限,也挑战着社会价值观困住女性的冰冷牢笼。
复杂而迷人的人物
费兰特之所以在女性主义作家中独树一帜,原因或许在于她那男性作家难以比拟的深刻度与洞察力——很少有男性作家能写出她那样真切的句子。费兰特证明了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写出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一个作家可以不去犯罪,也能逼真地临摹出罪犯的感受。然而任何男性作家不可能不去经历女性的体验,而逼真地表述出女性的感受。费兰特有捕捉女性身体与心理变化的能力,在她的笔下,生理和心理在女性身上同频率地变化着。这种结合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她的文字既客观公正,但同时又蕴含着深层的恐怖。
费兰特笔下的人物复杂而迷人,或者说因复杂而迷人。她的人物往往被截然相反的感情所交织着。她的人物对读者有着近乎狂热的坦诚,总是将自己拆分得七零八落,显露无遗。很多作家为了塑造人物的复杂性,常使用的方法为“双重表达”,譬如通常让人物对一个对象或者符号爱恨交织——但通常这种爱恨都仅仅浮于表面。费兰特会将这种爱恨立体化。比如勒达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感情,有着对自己母亲隐含的竞争、在社会观念下的自我约束与实现理想两者夹缝中心态的此起彼伏,以及看到自己在女儿身上某些东西得以延续——她的欢喜与失落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此,甚至导致了她对两个女儿细微的迥异态度。
费兰特的心理描写能抵达人物心灵最为隐秘的深渊。这种描写往往携带着一种费兰特式的羞耻感,是社会道德规范下暗流涌动的波澜。费兰特在关于勒达和两个女儿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描述:开始是相对常规的写法去表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困境,如“有一阵子,我一直以为路上的男人是在看我,这是二十五年来,我已经习惯去接受和忍耐的事”;随后是令人惊愕的突飞猛进——她发现女儿长大后那些男人贪婪的目光都会转移到她的女儿身上。这时她的感情犹如多层结构的晶体,警惕、高兴、伤感,而她的自嘲甚至还暗含了某种释然。这几种感觉恰如其分地混杂在一起,通过文字被提炼出来,让读者得以窥探到人物深层的光泽。
贯穿小说的不可知性
费兰特的人物同样具备了一种不可知性。她一方面几乎夸张地解析着人物的内心,其全面性与复杂性令人咂舌;但另一方面又留下了缺口——这种不可知的神秘性让读者觉得难以阐释。
《暗处的女儿》第一节的时间点位于整个故事的结尾:勒达离开了自己的公寓,随后因为某个她自认为毫无意义无缘无故的举动导致车子撞上了防护栏而受伤住院。费兰特写道“那些最难讲述的事,是我们自己也没法弄明白的事”——小说沸腾着不可知的蒸汽,以至于人物永远无法被真正看清。这种不可知不能被简单地诊断为潜意识。相反,那是女性最不可破译的自我,是生活孕育的真正的内核。
这种不可知在小说的结尾达到了巅峰:尼娜似乎马上要云破天青,热忱地下定决心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但突然之间峰回路转,勒达交给了她那个一直被自己偷偷藏起的布娃娃,此时她导师的角色轰然坍塌,一切都被推倒重来,像一记耳光一样快速、响亮而疼痛地结束了。最无法判断原因的是,尼娜为何在看到布娃娃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此回归到生活的泥潭中?没有任何解答,突然而自然地落下了帷幕。尼娜一家的生活开始如何,以后似乎就会如何。
贯彻始终的布娃娃
布娃娃是费兰特在小说中常用的意象。在《我的天才女友》中,两位女主人公友谊的开端正是源于彼此的布娃娃。而在《暗处的女儿》中,布娃娃这一意象同样贯彻始终,只是所蕴含的象征性更加复杂。
这布娃娃对于尼娜和埃莱娜母女来说“代表了一种平和、幸福的母女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尼娜在得知娃娃丢失的真相后会崩溃并决绝地告别)。对于勒达来说,布娃娃象征着某种不敢宣之于口的隐秘的邪恶。她在归还与私藏之间来回摆动举棋不定,仿佛在内心深处不断地煎熬、不断地与自我交战。同时,这个布娃娃又是勒达怀孕时的镜像投射。勒达最终在布娃娃体内取出虫子的情节残酷地呼应了之前关于她生育时的描写。某种意义上,生儿育女对她来说是一件可怖的事。其可怖之处正在于养育孩子压榨甚至减灭了她人生的意义,像是水蛭吸走了她的血液。勒达的丈夫詹尼说自己无法同时兼顾工作与孩子,那对她来讲又何尝不是?她所追寻的意义与生活是牴牾的。
所以当勒达在舟车劳顿中偶遇了布兰达之后,一潭死水的生活擦出了火花。勒达在小说中经常发生改变,但促使她改变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巨变,而可能只是某个符号或小事轻微颤动所激发的蝴蝶效应。于是她抛夫弃女三年去过她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费兰特最值得赞赏的是,当她描述詹尼的挽留时,几乎运用的是一种平淡的陈述——这反而增加了强度。费兰特也不把丈夫塑造成洪水猛兽。这样的笔法,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勒达更加离经叛道。根据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也许丈夫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对于勒达,生活的意义才是重中之重。
然而,生活似乎并没有真正改变,对于尼娜来说是,对于勒达来说同样是。勒达认为布兰达改变了她,而她即将改变尼娜。然而她的改变失败了,而读者似乎也可以隐晦地得知布兰达的改变也失败了——勒达离开了三年,最终还是相对地回归了生活。当我们再回顾这部小说的开头时,在医院中,她的女儿、她的丈夫又都来看望她,一家团聚,但她内心深处真正的话语却无法向任何人言说。她周围所有的人无法激荡起心中的水花,就像她在结尾回答她女儿的那句话一样:“我死了,但我感觉很好。”
编辑/史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