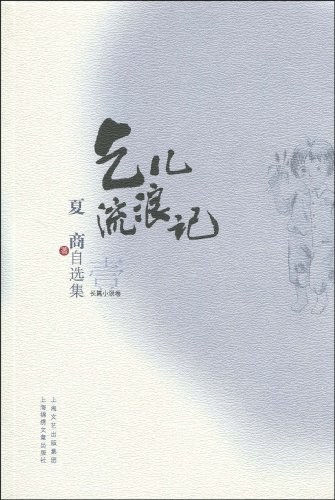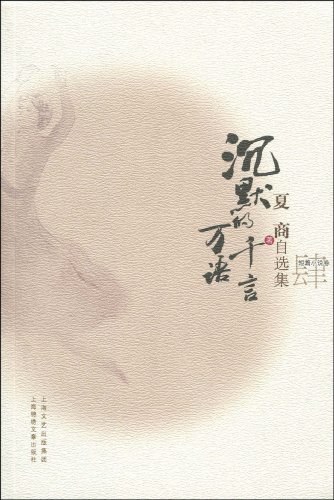在纸上的文字不再是不可替代的审美形式的今天,文字阅读已成为一个人生活中有意为之的选择。评论家张灵在这样的时代与其同代作家夏商的作品相遇,以专业评论家的眼光细读每一部作品,并在分析各方评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将作品背后联结的作家、历史、社会等因素一一凸显出来,既拓展了文本的阅读空间,更证明了文学作品独具深广的记忆能力。
与80年代相遇
在莫言、余华、苏童等带着非凡的作品享誉80年代文坛的时候,从张灵的《夏商小说论》中可以读到,1984年夏商虚15岁,刚上初二,因上物理课在书本上画画而和老师发生肢体冲突,被学校开除,成为一名社会青年。1986年,夏商到工厂当工人。1989年,80年代的最后一年,夏商的第一篇散文被刊用。从作家开始创作的客观时间来看,夏商似乎是这个时代的迟到者,没有能够成为80年代某个标签后的一员,但张灵还是把夏商创作的起点放在这个时代,将80年代的文艺思潮、人文精神求索作为夏商创作的精神源泉。
夏商虽然成名于90年代,被归类于后先锋写作群,但即使是在用先锋技艺进行写作的尝试期,写现实也是其作品的硬核。张灵注意到夏商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这种与现实的不可分割性,也发现夏商笔下的现实具有高度概括的意义,他引用上海本土评论家郜元宝在评论《乞儿流浪记》时的论断:“夏商不属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醒悟过来之后急急忙忙梳妆打扮一番就粉墨登场的‘上海文学’,……他甚至和所谓的‘都市文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很少刻意在作品中炫耀自己有关都市的知识。他也许喜欢描写所谓‘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但这也是一个灰暗暧昧的地带,无法作为标签贴在他的作品之上。”郜元宝指出了夏商作品与具体的地域、时间之间这种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关系。上海不过是作家的记忆、思考之城,而真正唤醒他文学灵感、使他产生创作冲动的是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张灵以同代人的精神共振进入夏商的这一精神故乡,看到这一丰饶的地带在作品中被或实或虚地描述,从而领略了作者将个人问题延展到公众问题、将时代问题推衍为历史问题的复调叙事美学。
张灵用客观的史家笔法记录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对比发现其作品中不少人物身上带有作家早年生活的印记,作家描写的“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带有明显的亲历感、现场感,而那些源于生活的人物形象百人百面,绝不概念化。张灵说:“《东岸纪事》里的一系列人物都能给我们一种信服感,让我们觉得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就在那样的生活环境里存在、作为。这说明夏商笔下的人物有着扎实的现实基础。”“现实基础”——亲历的生活使夏商用平视的眼光去塑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不像鲁迅对阿Q、闰土那样高高在上地俯视他们、嘲讽他们,也绝不像许多写苦难的作家那样不时地用眼泪表示同情,而是如雕塑家一样将自己的体温捏进人物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使这些人物活在尘光中,张灵由此得出结论:“鲜活、精确、传神的人物形象既是小说成功的关键,也是这片土地成功走进文字中的风俗画、‘地理志’的关键。”
夏商善于写人物,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细节,但写生活并不是他的目的。那些生活中的问题早在他被赶出教室的一刻就开始积攒了。特殊的人生经历让他过早对生活感到迷茫、失望,有时甚至感觉生活是黑暗的。他用文字向生活纵深处求索,思考该如何生存,也思考人情世相。由此,张灵从《裸露的亡灵》中读到“对‘性’与‘命’的迷思”;从《标本师》中读到“……将激情、灵感、直觉、想象与事实、理性、逻辑、思考相融合、相升华的境地”……而这种借文学之思寻找个体价值的创作方法正是80年代“人的文学”思潮留给后世的最为宝贵的思想方法。
与同代人相遇
沈从文说:“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张灵和夏商的相遇,实则是两个步入中年、思想成熟的人合力拂去岁月的尘埃,拂去年轻时的浮华、冲动,冷静地清理当年文化大潮退却后留下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灵的《夏商小说论》并不只是一部作家作品专论,而是借由作品展开的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回忆,这个回忆起于文学,扩展到80年代启蒙思潮影响下的社会的方方面面。
对80年代社会环境的熟悉使张灵得以轻松地捕捉到当年影响夏商创作的社会动因,将对作品的阅读关联到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既使深藏在作品中的文化密匙浮出水面,也使作品中的人物获得了反映一个时代的典型意义。无论是夏商专门关注问题少年的中短篇小说,还是反映社会变革的长篇《东岸纪事》,作家笔下的年轻男女的成长经历既是个人的、独特的,也是在时代潮流推动下底层人物的必然命运。
张灵在评论乔乔这个人物形象时说:“每个生命主体,他的命运除了受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历史议程、宏大叙事的主宰以外,他更受到包含着浓重道德伦理成分的文化习俗的锁链的规制、约束。”社会复杂的“他者”目光正是80年代转型期特殊社会环境的真实反映。社会从国家经济层面是开放了,可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身份意识等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乔乔就是被“他者”目光逼迫到了生活的角落。这个生活在尚未开发的浦东的乡下姑娘,原本具有实现自己梦想的一切条件,眼瞅着已经迈进了成为城里人的大门,考上了大学,却被一个小混混小螺蛳从窄门里拽了出来。其实真正改变乔乔命运的并不是小螺蛳,而是她自己的成长环境和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各种潜在的价值标准。从乔乔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所做的选择中,可以看出“他者”的认同对她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张灵对这种“他者”目光分析得翔实而到位,它本质上是深埋在一代人青春中的集体伤痛。
张灵和夏商却又是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夏商混迹社会,四处投稿寻找前途的时候,张灵正在大学教室接受正规的学院教育。面对夏商的作品,张灵犹如关在教室内的学生观看窗外的人生,自己同代人的另一种生活令他惊诧、惊喜,也让他对自由的生活由衷地歆羡。
虽然张灵有意识地用客观、平实的语言分析夏商的作品,但对作品中恣肆、野性生活的羡慕态度还是在他的评论中不自觉地显露出来。在他眼中,《乞儿流浪记》是一部“生命诗学”;《东岸纪事》也是“诗学命题”……这些社会底层人为了生存而爆发出的野力在张灵看来都具有史诗般的魅力。这种全然欣赏的态度使张灵在批评时忽略了客观分析夏商早期作品对西方现代小说技艺刻意模仿的痕迹,忽略了指出其一些作品还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
与世纪末的文学问题相遇
80年代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给文学创作“松绑”,作家不仅在创作内容上不断突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划出的红线,在创作形式上也总在求变求新,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追“新”精神是上世纪80年代极为突出的文学精神。80年代的先锋作家是幸运的,他们在躁动的青春期遇到了一个躁动的时代,这个时代接纳了他们的才华,让他们稚气的呼喊轻易产生了轰动效应。
90年代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表现出更多争取话语权的焦虑,这种焦虑感的存在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快节奏的发展不无关联。张灵在书中谈到夏商在1998年5月参与的“断裂问卷”调查,说这次调查“显示出与前辈作家在艺术观念上的某种决裂和叛逆的姿态”。今天看来,当年“后先锋”派以群体宣言的方式与一切前辈包括先锋派加以区别,却又贴着“‘后’先锋”的标签现身文坛,“后先锋”的中心语仍然是“先锋”,从这个没有新意的命名中,也可以看出当年他们的稚拙、匆忙和潦草。20世纪末的文坛涌现出一拨拨的“新”与“后”,但无论隶属于哪一派,创作出与激变的时代相匹配的大作是作家共同的野心。
在与80年代作家群的观照中,张灵有意将夏商从“后先锋”作家群体中剥离开来,从文学史的视角研究作为个体的夏商的创作道路。张灵在书中写道:“而实际上,这个年代余华苏童们也已经告别了过于执著形式实验的‘先锋’阶段而正在向传统、向现实主义文学做着‘后退’和回归。”张灵的这一论断准确抓住了先锋派作家转型的节点。余华在90年代初就自问:“我如何写出我越来越热爱的活生生来?”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苏童、余华们想要回归的现实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批评现实主义文学所要表现的现实,他们要用文字留住时代大潮中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段段热腾腾的生活。当夏商有意识地细描“众生相”的时候,他的创作终于进入了成熟期,从商业时代热切的加入者转变为主动的思想者、回答者。
米兰·昆德拉说:“文字是慢的历史,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生活得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致失传。”商业时代却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在金钱如流水般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裹入淘金的人流,作家也不例外。字数比文字更多地影响了许多作家的创作,生活轻易地腐蚀了他们的精神。夏商却因商业上的成功不需要利用文学去赚取生活。张灵写道:“写作从而可以成为他纯粹的私好,一种隐秘的幸福追求。”这应该是转述的夏商的真心话,他为自己在匆促的时代能够停下来想想文学而感到庆幸。
或许与从小就喜欢绘画、喜欢设计有关,夏商的小说很讲究形式美。张灵指出《东岸纪事》并不是依循时间线索安排人物的命运,而是在一个空间同时展开三个不同事件,他将之命名为“三叠屏”式结构。张灵还将作家的叙事策略比喻为建筑楼房,不同人物、事件如同砖瓦,可以同时开工,同时封顶,而决定楼房不同层面的则是事件背后的思想内涵。在这种从时间中随意拿取砖瓦建楼的方式中,张灵看到先锋、后先锋技术在现实题材中的自然运用,“在传统写实为主的作品中通常出现的社会生活描写和故事情节叙述的完整性、整体性和原生态般的世界外在风貌将被打碎,社会生活故事或主人公的命运轨迹将被作家的‘叙述’任意宰割和重新编排。”
如果说《东岸纪事》是由三条人物主线构成了“三叠屏”结构,那么夏商小说从表层到深层还构成了另一个“三叠屏”,这就是张灵所说的夏商作品普遍具有的寓言化的特点。张灵将夏商的三部长篇《裸露的亡灵》《乞儿流浪记》《标本师》归类为“寓言”三部曲,认为“夏商回避了浅层次的、直白的人道主义,而是把人道主义化成了‘寓言逻辑’使之表达得更为有力和强烈”。语言是外衣,“弱势群体”“中国本土原生态的生活”是寓言的内容,而内里的哲思则是含义丰富的寓意。这样“三叠屏”的结构使夏商的作品在语言盛宴之中饱含深意,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灵说夏商的小说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现实”与“先锋”在作品中的高度融合与平衡,这样的评价并非言过其实。
小说根本上还是语言的艺术,无论其结构的大厦还是细节的砖瓦,都是由一方方文字构成的。夏商说:“小说有许多奥妙,最重要的奥妙就是来自于细节。描述越逼真越精细,就会越接近于世事的真相。”而能够通达逼真、细致地描述的,自然是极其精准的语言。张灵在书中反复提到夏商作品的修辞艺术:“夏商小说善于将故事情节通过感受融合、跨界修辞和蒙太奇式的跳跃组合来达到讲述的分合转换并实现情感氛围的营造。”这种移觉、通感、错位、杂糅的方式在夏商小说的语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诗人任洪渊说:“语言的边界就是生命的边界。”词语拼接方式看起来是现代的,但与一些现代派作家在词语创新中过分追求陌生化、个性化,从而使词语变得晦涩难懂、不知所云不同,夏商的词语创新从感觉中来、从生活中来、从方言中来,词语的位移、错位、拼接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可以用极简的语言搭建作品的框架,“快刀斩乱麻”地处理情节,但在描写人物的细节处却极其精细,不厌其详。这种情节推进的快与塑造人物的慢自然调配,确实是夏商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张灵以同代人的身份感性地进入夏商的小说世界,以80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成为其阅读的互文本,读出了夏商小说中的两个“三叠屏”。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深耕细读的方式是最为老实也最为花工夫的阅读方式,它远不如炮制、套用新概念省力,但却是最贴近作品的批评方式。真正的批评家正是优秀的读者。张灵说夏商写小说是“隐秘的幸福追求”,那么能够在作品中展开一场真诚的心灵对话,这对作家和评论家来说都是幸运而又幸福吧。
作者|王陌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