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从作家田中禾家人处获悉,田中禾于7月25日辞世,“安眠长睡”,享年82岁。按本人生前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悼念仪式,不举办任何纪念会、追思会。不发讣告。
田中禾生于豫西南南阳盆地的唐河县,此地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他幼年时听到的豫剧、越调、曲剧、大鼓书、三弦书、汉剧、大调曲子等,构成了他青少年时期主要的文化生活,这种来自民间的文化营养与艺术熏陶显得丰富而自然。从1959年5月出版长诗《仙丹花》至今,田先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已至64年,他的创作早期以诗歌、文学评论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则以小说、散文随笔为主,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以及四卷《同石斋札记》散文、随笔集等。
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田中禾还是一位文学组织者与参与者,他曾历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第五、六届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部分作品以英、日、阿拉伯语译介国外。
2019年,在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暨《同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举行之际,本报对其进行了专访,在访谈中他表示,“我一直在迷失,逃离,因此没被某个流派罩住,贴上标签。流派是一种归类思维,喜欢出走的人不喜欢被归类……迷失在自己心里,埋头于文字,一门心思摆弄自己的手艺,是很快乐的事。”
田中禾女儿张晓雪新近写下的关于父亲的文字,她说,“多少年来,无论世俗的价值取向如何改变,父亲始终是一个肉体明亮,精神饱满的人,我知道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有趣、智慧的性格,归结于他的爱好和坚持。”这也是文学界同行共同的感受,借助这篇文字,纪念自在且率真的田中禾先生。
张晓雪:父亲散记
父亲田中禾是个乐天派,洒脱通透、无所顾忌的人生观,永远保持着少年般的勃勃生气。无论是三十岁、六十岁、八十岁,他的性格从来没有因为曾经遭受过生活的创伤、困顿、褒贬而改变过,也从来没有因为世俗的认同而妨碍了他的觉悟。一辈子自在、独立,由着性子做自己。反而是他身上这种可爱的天然属性,极度率真而浪漫的精神气质更加赢得众人的激赏。
父亲一生作品无数,精通小说、诗歌、散文、绘画、戏剧、音乐,每一项都像他的人生经历一样丰富,透着睿智和个性,每一页都标识着他的天赋和勤奋的品质。重读《落叶溪》,这种感觉“如隔世般的遥远又如昨夜那样亲切”:时光就这样悄然流逝,我离开县城去求学,又辗转回来。我家堂屋上的瓦松依然如昔地苍苍郁郁,灰色旧砖销蚀了墙角,门前石板多了一些不为人觉察的滴水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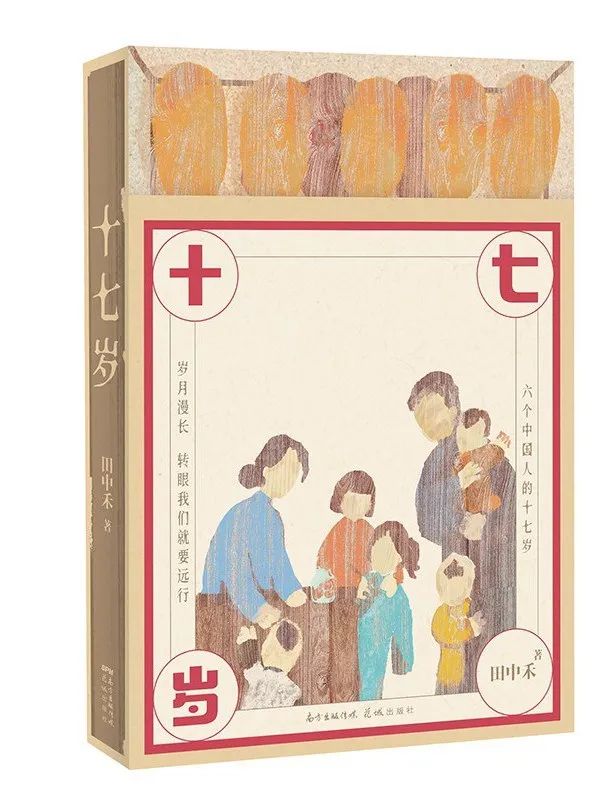
《十七岁》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
这几行不紧不慢的文字将一个美好的少年运送过来,退学后的他是带着幻想和自由回来的,而事实上他内心尚不那么超拔,强大。家的温暖,如同百柔之水消解着他孤独的处境。这本书中的很多描写让我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诗情态度和不为世俗功用的本性,无论时光流逝多久,他都是这样一个独异于人的存在。
现在阅读父亲,仿佛是在做一件类似挽救的事情,随时随地,内心都在承担着被他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瓦解的脆弱。
翻阅,确信我与他的精神和灵魂交织交融着的那种翻阅,他如雾岚一样飘来飘去,又因为他文字的色泽、质感而无比清晰:有一年,母亲带我到乡下去,我看到有一块地,全种着鲜花。微风吹动,阳光明丽,田野里的花美极了。红的,紫的,白的,摇着轻盈的花瓣,像薄绢……罂粟花太美了,它能孕育出那样奇妙的果实,使人迷醉……
又是明亮的底色,类似天性流传,让我感受到了温度,感受到了可触摸的娇艳形状,香气扑鼻而来。在平凡的生活中,父亲总是能以极为艺术的方式展露世界,沉浸式地体验和世俗一样又迥然有别的生活,连呼吸都那么细微均匀。以至于所有与他相关的蛛丝马迹都能重回到原先的光晕中,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确切,越来越孱细。
这块曾带给父亲温柔与生命启发的田野,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收藏过我的生命气息。也不知道这块田野是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平地峥嵘的广场,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将他的那种骑车追风的兴致传达给我的。大约也是一个夏天的某个黄昏,(膝盖上磕碰的疤痕是欢快的证据)父亲带着年仅七岁的我在广场上学骑自行车。那时我瘦小的身体尚不及车把高,硬是斜着身子,将小腿穿过横梁下的空挡,努力去够脚蹬子。彼时,二八自行车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庞大,由于父亲半弯着腰握定了后车架,便妥妥地将我的身心都撑了起来。
一股凌然之势俨然驾驭了这匹小野马。蹬!大胆地向前蹬!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已悄然撒手,站在距我几十米远的地方大声喊话,我当即心神发慌,孤立无援地就地倒下。这是我有记忆以来,和父亲第一次精神合作,构成了异常富足的灿烂和隐隐约约的腾跃。数十年过去,很多环境都变了,再想起发生在那个曾经赖以生存的小县城的一些情景,内心依然激动。而父亲给予我的与生俱来的安慰感和安全感,其中所包含的爱意也愈加浓烈。
多少年来,无论世俗的价值取向如何改变,父亲始终是一个肉体明亮,精神饱满的人,我知道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有趣、智慧的性格,归结于他的爱好和坚持。日复一日汹涌的时光中,他的人格和耐力一路互相衔接,是真正属于那种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的人。回忆在底层生活的年月,他这样写道:我很怀念那段拉车子的生活,装上货,架起车把,毛驴就会非常懂事地绷紧套绳,四蹄子叩地,直着脖子向前拽。汗水无管冬夏,痛快淋漓地淌过被太阳晒得如同铜铸般的脊梁,在俯身蹬直双腿的时候,胸中就有豪气冲出,让人忍不住呼喝唱歌,无穷尽的路便无忧无愁从眼前转动到身后。
忘不掉温凉河的沙滩,白花花一片,在河里洗过澡,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懵懂记得父亲这段生活,也是父亲必须安命于斯从而给予家人的生活。苦日子总是那么具体而漫长,一样的困顿面前,他并没有让自己卑微、焦虑过。即使生活再残酷,他还是会说“生活是莫大的喜悦,而不是含泪驯服”这样的话。这是他给予我的收获,在穷困潦倒之时并不怨天尤人,在困境中依然正视现实,活得那么自然随性,活得灵性而有尊严。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心情和健康,人要学会适应外界的一切变化,包括苦难。
虽然苦难被他视作是日后为写作提供的一笔财富,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从不喜欢诉苦,偶尔被家人或故交提及,他会无限地缩小、淡化它:都过去了,重要的是人要向前看。他说,苦难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不希望年轻人去尝试,幸福才是他们该有的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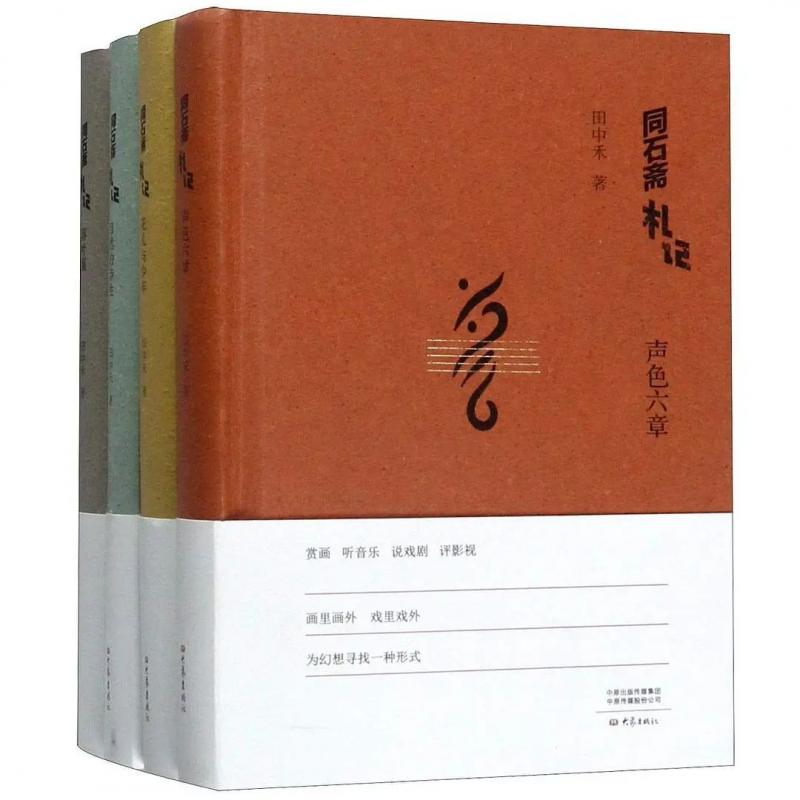
《同石斋札记》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
对生活如此,对文学的态度亦然。他输出的教益更多是针对自己,自省的言语之中从不谴责谁:将文学低谷的责任一股脑推向社会、经济、商品、时代,从而对文学衰微持以无奈愤慨的情状,印证了作家内省意识薄弱。
有些话即便是说给别人的,有很多人在场,他发出的每一次拷问往往也是先指向自己,痛快、淋漓,说来就来:是为文学而文化,还是将文学作为达到某一功利目的的手段?
这是他几十年前就展开的自我剖析,涉及到作为一个作家,文化人格够不够丰富,够不够强旺和博大等等,总之,凡是作家应该反思的问题他从来不避讳。可以说,在当代作家中父亲的才气不一定是一流的,但勇气和坦率的程度却是罕见的。
父亲同样是一个珍惜现世安稳的人,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印象中只要我进家门,只要看见他,一定是在阅读中。他著述丰厚,思维敏捷。年逾80,仍保持着不竭的创造力。但他却从不以文学翘楚自居,遇到“大师”之类的过誉言辞,每每以风趣幽默化解:“大师是骂人的。我要是大师,李白杜甫是什么呢?”关键时刻,他的真诚和谦逊,总能派头十足地笑着完成某个场面的夹击,完成某种情绪的卓异性。
如此任情恣性的父亲,不仅让我感到了荣光、安宁和可靠,还为我提供了镜子,得到了警示。最最重要的是,来自父亲的经验是唯一的,比世上任何一种语言容易理解得多,且无可替代和置换。
有人说父亲健全的心态是他维持较长创作寿命的原因。说来只能算作原因之一。因为再健康的心态都不可能百毒不侵,不可能因为你心态健康痛苦就消失了。只不过父亲的处理能力,因高出许多一般经验而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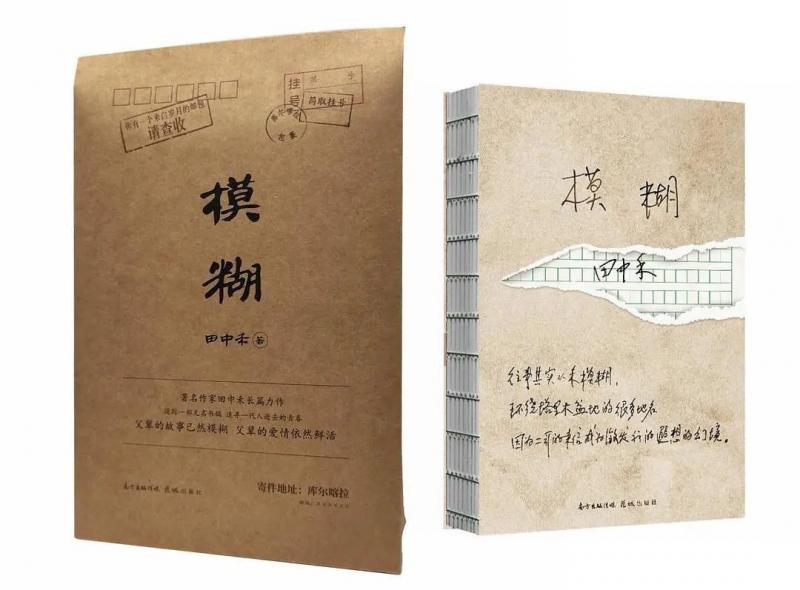
《模糊》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
在患病之前,这个无论顺境逆境对生活都怀着期冀的人,在我的印象里,从来没有记忆模糊,走路不稳的时候,在他的世界里也从来没有过可怕的沉闷与沮丧。他想写东西就能多思而敏于行动,落笔清晰,文学就和他互为生气。一种生命状态一贯在时间中不急不徐地运动着,清修、参悟,持久地沉浸于出奇的遐想、语言秘诀和旷达之境:
我对人类前景持达观态度。大宇宙在运转,文明将不息地发展,如果有朝一日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的不息掠夺使地球毁灭,那么,也许人类转移于其他星球,也许人类与地球同归于尽。那也不怕,大自然会再造一个地球再生出人,文化还会产生,循着“洛伦兹蝴蝶”的轨迹运转。如此而已。
如今,不得不说父亲的所有作品作为他存在且永恒的证据对我形成的心理支撑是空前绝后的。如今,白昼,厚厚的阳光堆过来静静地抚摸着父亲书柜里每一本书籍和文稿,与笔筒中的一把毛笔、几个相框、汝瓷钧瓷摆件互握互尊。猫咪豆豆照旧卧在父亲书桌的右侧,长久陪伴的姿势丝毫没有挪动的意思。像往常一样,望向那把椅子,等着父亲坐下来,它才觉安心。就这样,久久地来我沉湎于父亲的书房,像连续的理疗,不做任何撤离。仿佛听见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如果你生活得过于沉重,感受到了孤独和痛苦,那就想法寻找些无聊,比如打打麻将,种花、养鸟,养个宠物,看看相生小品、练练气功、书法,……如果你受不了无聊,不妨想想地球,想想人类,想想人世的不平、人性的缺陷,真正投入地去爱一次……
文/张晓雪
来源/文学报
编辑/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