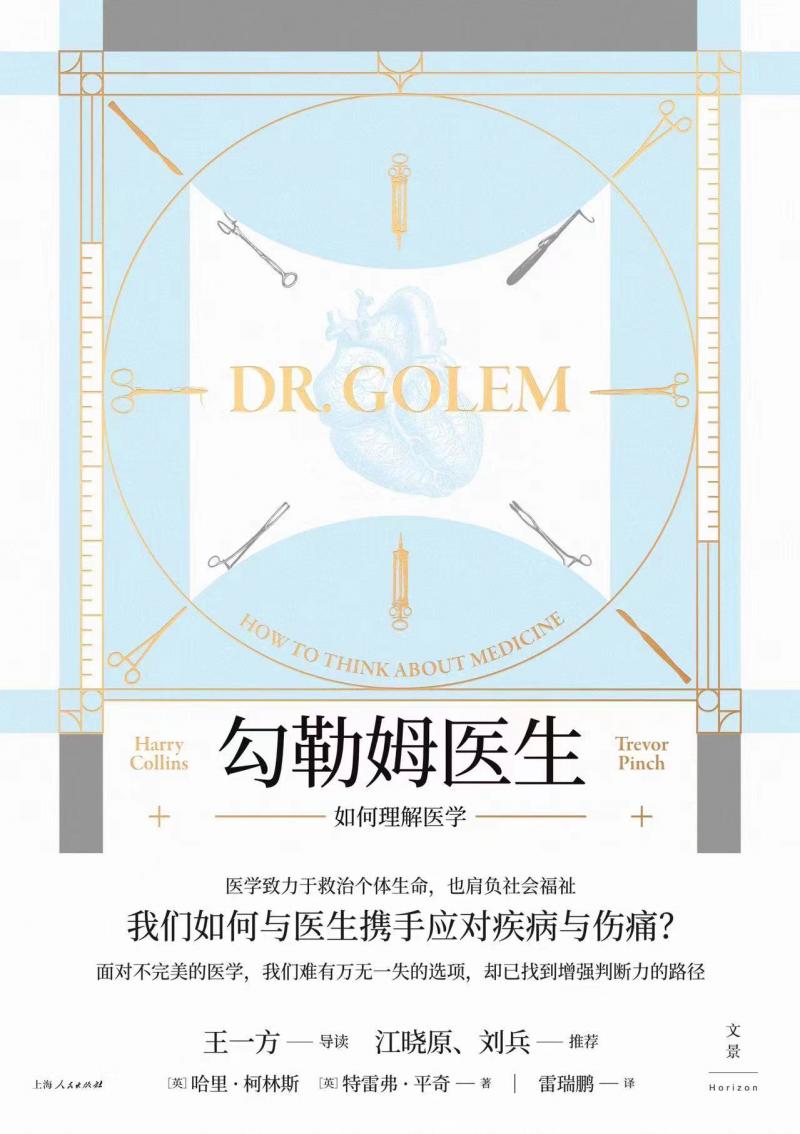乍一看书名,很容易掉入误读陷阱,把它当作传记来阅读,臆想作者讲述了一位叫“勾勒姆”的神医,如何茹苦含辛,救苦疗伤云云。在国人的记忆之中,《百家姓》里有“勾”姓。据《山海经》记载,有困民之国,勾姓。相传帝少昊一子名“重”,死后被封为“木正”,为五行神之一,掌管天地万物的生老病死,号称勾芒,其子孙皆以“勾”为姓,其中以越王勾践最为知名,其卧薪尝胆、复兴霸业的励志故事千古传诵。于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勾勒姆便与勾践归于一类,有着某种英雄主义的精神胎记。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勾勒姆不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一个隐喻式的传奇,类似于《西游记》中那位需要紧箍咒约束的齐天大圣。“勾勒姆”(golem)一词源自意第绪语,依据犹太教法典记载,勾勒姆是由某位亚圣造出来的“泥人”,因而不具备神的全能智慧。无疑,诞生于神创时代的勾勒姆具有明显的英雄主义特质,他强壮有力,而且越来越强壮,但其本性无所谓善恶,通常他会为人类福祉服务,拯救人类于苦难之中,但是,他也有笨拙、莽撞的一面,潜藏着危险,如果未加引导与管束,可能会祸害人类。这不就是所谓的“双刃剑”,或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二元思维吗?是的,勾勒姆就是那位“一刀繁华,一刀寂灭”的剑侠。
勾勒姆是作者柯林斯、平奇笔下的一个隐喻,他们试图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解读、洞悉理性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分离与冲撞。为此,他们共同完成了三部勾勒姆的专著,分别为《勾勒姆:关于科学你应该知道的》《脱离控制的勾勒姆:关于技术你应该知道的》《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以洞悉人类价值境遇中科学、技术、医学的“景深”。国人习惯于事实性评判,衡量是非高下、利害得失。隐喻的优势是回避科学、技术、医学的抽象本质和方法的优劣高下,也绕过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通过寓言人物的形象, 对科学做现象式叩问,来透视科学、技术、医学的隐忧。因此, 《勾勒姆医生》是一个重审医学的目的、价值、意义,反思医学的现代性,提升现代医学精神海拔的思想操练场,对于中青年医生而言,阅读该书,可以极大地丰富他们的学术维度,建构有品质的批评生活。
细读导论,作者借助“勾勒姆医生”的登场,给现代医学带来两道烧脑的悬题。第一道是医学目的的二元性,一面是探究生命奥秘的医学科学诉求,另一面是救死扶伤的临床功利诉求。诚如导论标题所言,“作为科学的医学与作为救治手段的医学”,既存在着鸿沟,又并行不悖,由此揭示出医学本质属性的二元性, 医学是生命科学,医学也是救治艺术。前者在生物医学模式下惯性运行,后者在全人医学模式中随机调适,前者是受控的“实验室境遇”,后者是变幻莫测的“临床境遇”。对此,现代临床医学大师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一百年前就明言“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其背后大有深意。不确定性与艺术性的杂合,揭示了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疾苦现象的混沌性,疾病过程中身心社灵交叠所导致的病况多样性,医疗干预的或然性,疾病预后与医患关系的不稳定性,比比皆是,无疑给医学、医院、医生呈现一道“不等式”,给患者、家属递上一个“万花筒”。因此, 悉达多· 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在《医学的真相》(The Laws of Medicine)一书中曾诘问:“为什么敏锐的直觉比单一的检查更有效?为什么不同的人对相同的药物反应不同?为什么看似有益的治疗方案却是有害的?”
第二道悬题事关临床认知与应对模式的分野,作者形象地比喻为“4S 店”模式与“美发(容)店”模式。在汽车普及的当下, 几乎人人都有4S 店维修的经验,一通电脑测试之后,维修工递上一份“换件清单”,仿佛是一条“忒修斯之船”,换掉腐烂的船板、置换磨损的部件之后,汽车立马焕然一新,甚至不劳维修工动手,全程电脑控制,机器人操作,标准序贯,简洁明快。而“美发(容)店”模式则需要美发(容)师首先对客户的脸型、年龄、身份、职业、审美偏好、支付能力做细分,然后提出美发(容)整体解决方案,充分征求客户的意见,不断进行调整之后才能确定发型、色泽……电脑效果呈现认可后方可开工,其过程之中还可随即调整,力臻完美。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充分体现审美与手艺的独特及个性。作者之一的柯林斯亲历了儿子遭遇严重车祸的救治历程,深感标准化的急症处置模式(心肺复苏、输血、摘脾……)的效率,但慢病时代的来临,病有百态,他又感叹“替代模式”的无力、无奈。由此看来,作者并非质疑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而是要质疑这些巨大成就给医学思维带来的板结。
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的领军人物,柯林斯与平奇从现代医学社会化境遇中截取了八个有趣的话题来深入透析,试图由此来松解现代医学的认知“沙化”与“板结”,廓清其现代性迷思。以下重点解读其中的肯綮。
安慰剂与安慰剂效应(第一章)。安慰剂效应被作者称为“医学中的重大难题”,自从抗生素诞生以来,人们对病因治疗的认知大大强化,尤其是靶向类抗癌药物的横空出世,更让药物治疗走向精准化。其实,药物治疗有四个层次,一是病因治疗,二是发病学治疗,三是症状学治疗,四是安慰剂治疗。安慰剂虽然位居末位,但并非没有疗愈效果,只是人们不解,为何安慰剂效应常常超出安慰剂本身的药效动力学解析,这不得不诉诸人文药理学, 也就是说,从“战争模型”角度看,某药物并无明显的病因对冲或拮抗作用,但患者的病况改善却十分明显,原因何在?那就是“心病还需心药治”中的“心治”,即身心社灵复合干预所形成的非药物疗效。或许该药存在未被认知的潜在靶向作用,或许是患者对于该药期待强烈,或许是医护在用药过程中的情感、语言、陪伴、抚慰等复合效应突显,共同激发了体内的某种内源性抗病因子,呈现出慢药急效、轻药重效,甚至无效之效的现象。因此, 安慰剂的疗效实实在在,并不蹈虚,更不是虚构的故事,也恰恰证明药物的效果不全集中在病灶靶点上,而有更加泛化的、迂回的药理路径存在。尤其在慢病治疗与管理中,放大安慰剂效应是照护的重要内涵,值得深入开掘。由此可见,安慰剂效应极大地冲击了生物医学模式中的药理解释机制,为人文医学开辟了新的航道。
冒牌医生现象(第二章)。古往今来,医学的专业性门槛及医护社会地位的美誉度,使得江湖骗子孜孜汲汲,跻身其中,非法行医。如书中所列举的十余位冒牌医生,每人都有独特的包装术、伪装力,危害程度也不一而论,有的只是庸术误治,还有人过失杀人。不过,并非所有的冒牌医生都是谋财害命的“浑球”,莫里哀的《屈打成医》就以喜剧的形式塑造了冒牌医生的正面形象。樵夫斯卡纳赖尔与妻子失和,其妻为图报复,把丈夫斯卡纳赖尔当作名医引荐给一富绅,为其女儿“治病”。谁承想,斯卡纳赖尔凭其智慧和勇气,准确地找到了姑娘的“病根”,而且还施展“医术”,使其如愿以偿地与所爱之人结成眷属。莫里哀的剧作告诉我们,医疗过程不仅仅只是躯体病况的识别、干预,还包括社会困境、心理纠结、文化冲突的洞悉、把握、纾解,冒牌医生虽然在医学专业知识方面远不及职业医生,也未取得相应资质,但其智商情商、社会交往能力、沟通艺术都有高水准的呈现,以至于某些冒牌医生被揭露之后,仍有许多病家笃信不疑。冒牌医生的盛行也反衬出重技术、轻人文的偏科时尚,商业化、官僚化的医院文化下,医患关系不仅失温,而且还失信、失和。因此,要杜绝冒牌医生现象,除了加强监管之外,还需改善“人文贫血”的境遇,提升医学的关怀水准。
扁桃体与一“切”了之的外科崇拜(第三章)。曾几何时,西方医学界推崇手术治疗扁桃体炎,接诊室直送手术室,不管青红皂白,一“切”了之,阑尾炎也是如法炮制,更有甚者,将前额叶白质切除术(prefrontal leucotomy)用于根治精神病。1936 年,葡萄牙著名神经科大夫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前额叶切除,是一种简单、安全、有效的手术,是一种可以高效治疗精神障碍的外科手术”。为此,他荣膺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据统计,从1936 年至1950 年代,仅在美国就有大约4万—5万人被施行了前额叶切除。随着微创技术的成熟,外科崇拜、内科外科化的趋势不减,相对内科疗法而言,外科技术直击病灶,因而见效快、恢复快,但任意扩大外科技术的适应症不可取。以肿瘤为例,并非早期肿瘤都应该即刻实施外科手术,应该有所选择,对于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等惰性癌,不一定立即动刀,而应该继续观察。对于肺部体检因CT检测增强之后大量冒出的“毛玻璃”患者,也要谨慎手术。医学大师黄家驷先生说得好,外科大夫的最高境界是“心中有刀,手上无刀”,不是泛化手术适应症,而是尽量减少手术量,毕竟手术是一种对人体完整性的破坏。
替代医学(第四章、第五章)。相对于主流医学而言,替代医学是地方性、边缘化、民间化的疗愈补充。从医学史上看,主流与非主流疗法总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服务生态,而且曾经主流的服务项目也可能演化为非主流,如传统中医,曾经是中国主流的医学体系,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替代与补充。从医学哲学上看,主流的现代医学无法克服不确定性、复杂性、偶在性,必定会给非主流的替代医学留下施展拳脚的空间,此消彼长。理论上讲,技术精进的现代医学开疆拓土,不断蚕食替代医学的领地,后者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但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替代医学的疗愈空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这是为什么?书中例举的维生素C 治疗癌症的探索并不典型,更为典型的案例应该是“疼痛症”,疼痛(pain)、痛苦(pain and suffering)、苦难(suffering),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语境下,都不是一个齐同的概念,它蕴涵着躯体到心灵的两分与递延。痛苦偏重于遭逢疾苦的主体,而疼痛偏重于疾苦的体验本身,苦难则侧重于躯体之外的复合感受。痛苦的精神化呈现出特有的“深井效应”,牵引出痛苦的文化概念—文化群体经历理解和沟通,痛苦、行为问题或困扰的想法和情绪的方式,包括:
1. 文化综合征,它是一组症状和归因,常常共同出现在特定文化群体、社区,是一种体验模式。
2. 痛苦的文化习语,它是表达痛苦的特别方式,它不一定涉及个体症状和综合征,但提供了集体、共享的体验和讨论关于个人或社会担忧的方式。
3. 文化解释或归因,它是意义标签,它表明文化上被承认的症状、疾病或痛苦的含义。
目前,现代医学虽然组建了疼痛科,专门针对疼痛进行身心干预,但疗效仍不尽如人意,依然有大量的疼痛症患者求助于替代医学(如针灸、按摩),甚至还有人求助于哲学家。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就认定:痛苦是人生的“象征性交换”工具,由此确立受苦的意义,化解疼痛的心灵压迫,如恐惧、焦虑,从而部分地缓解疼痛。由此可见,替代医学的优势不是技术上与主流医学叫板,而是在人文抚慰和照护方面与主流医学一争高低。第五章提及的“雅皮士流感”(慢性疲劳综合征)、纤维肌痛都是替代医学的适应症。
心肺复苏术(第六章)。众所周知,心肺功能的衰亡是全身衰亡的扳机点,因此,现代医学在心肺复苏技术的探索方面致力最勤,投入五个骨干科室介入其中,重症医学科、心脏(内外)科、呼吸(内外)科、胸科、麻醉科都在此发力。加上声光电磁技术的导入,也为心肺复苏提供了完美的支持,人工起搏器、电除颤仪,心肺功能替代仪,人工肺(ECOM),还有心肺移植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人类“起死回生”的能力大大加强,正在重新定义死亡,不仅濒死期拉长,濒死复活的概率大大提升,即使是进入临床死亡期,也还尚存复活的可能。心肺复苏技术的普及,不仅造就了一批不死不活的“植物人”,也使得癌症晚期、深度衰老患者临终期也要经受心肺复苏的无谓折磨,似乎,最后时光不施行心肺复苏,子女就是不孝,医护就是违背“永不言弃”的职业诺言,殊不知,死亡是人生的最后落幕,无法逆转,应该尊重死亡的自然进程。无疑,对于急病急死(车祸、溺水、摔伤等意外事件),要尽快介入心肺复苏,但对于高龄人群的慢病慢死、慢病急死,就应该避免施以心肺复苏术。犹如我们手中有榔头不必到处都去敲,我们掌握了心肺复苏术,也不可逢死必复苏。
艾滋病患者组织与患者自主(第七章)。艾滋病是一种新生的免疫缺陷疾病,虽然社会资本投入巨大,但至今并未研发出疫苗和根治药物,鸡尾酒疗法可以有效延续生命,但带病生存期因人而异。作为现代疫病的现代患者群体,艾滋病感染者喜欢抱团求生,在全世界组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患者维权团体(俱乐部),他们在药物供给、采购、药品价格,甚至研发、评估上发表主导性意见,部分改变了政策与市场格局。他们正在形成与医学利益集团、医药利益集团鼎立并存的利益诉求集团,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就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1970 年代以来,患者权利运动悄然兴起,不仅是艾滋病患者团体,肿瘤、罕见病等患者群体纷纷效仿,他们借助于现代通信技术,以各种方式组建区域性、全国性患者权益组织,为个体患者代言发声,这种趋势未来将继续拓展,值得医学、医院、医生高度关注。
疫苗接纳与犹豫(第八章)。疫苗被认为是人类应对传染病的利器,工业化的疫苗生产与接种是20 世纪抵御传染病的伟大创举,随后,疫苗有益论风靡全球,既然是经过科学家和科学程序严格确认的预防传染病的神器,百姓就应该积极接种,以期疫苗效应的最大化,但是,在西方出现了疫苗算计,继而出现犹豫与抵制一族。先说疫苗犹豫,当一定比例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之后, 那些剩下的未接种人群就可以获得免疫屏障的保护,因此,他们无须接种疫苗,就可获得被动免疫,这样一来,没有接种疫苗之后的副反应,又获得了免疫,何乐而不为。如果人们都想不“接种”而获得“免疫”,则抵达群体免疫的人口基数就会不足,群体免疫壁垒就无法形成。而且最后一批疫苗犹豫者可能被指责“自私自利”,受到道德和良心的审判。其次,联合疫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接种,导致副反应叠加,严重者会危及生命,这就给接种者带来了疫苗恐慌,作者之一的平奇就自主决定自己的孩子分开、错期接种疫苗,以减少副反应发生的概率。这显然不只是平奇一个人的选择,而是“知情同意权”的正当行使,却被医护定义为“不负责任的父母”,难道绝对服从就是负责任,坚持自主评估、自主选择反而是不负责任?这背后缠着“公众理解医学”的巨大暗箱,任何科学知识与结论,都存在着双向辩护的空间,一只黑天鹅的存在就会颠覆“白天鹅”的群体印象,只有充分知情、充分理解,才会愉快接纳。同时,社会要为疫苗副反应受害者编织保护之网,如提供救助基金,才能从社会面消除“疫苗恐惧”,减少“疫苗犹豫”。推而广之,医学的不确定性(副作用)阴影几乎笼罩了现代诊疗全程,“公众理解医学”的任务十分艰巨。
在“结语”一章,两位作者一致感叹“勾勒姆医生”(医学)的写作难于“勾勒姆科学”与“勾勒姆技术”,这显然不是因为知识谱系的难度系数更大,而是因为医学的“顶天立地”,既触摸到科技前沿的天花板,又深植百姓的生活栖居。每一个人都是患者,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与家人的健康卫士,卫生科普是最大体量的科普,健康传播是流量最大的传播,医学、医疗行业、医药产业关乎每一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每一个家庭的荣枯兴衰。因此,勾勒姆“造福”与“造孽”两面性的揭示,医学的建构(颂扬)与解构(挞伐),不能发生大幅度的偏倚,但又很难做到不偏不倚。犹如空中走钢丝的杂技表演,平衡感来自平衡杆,但愿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根“平衡杆”。
文/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