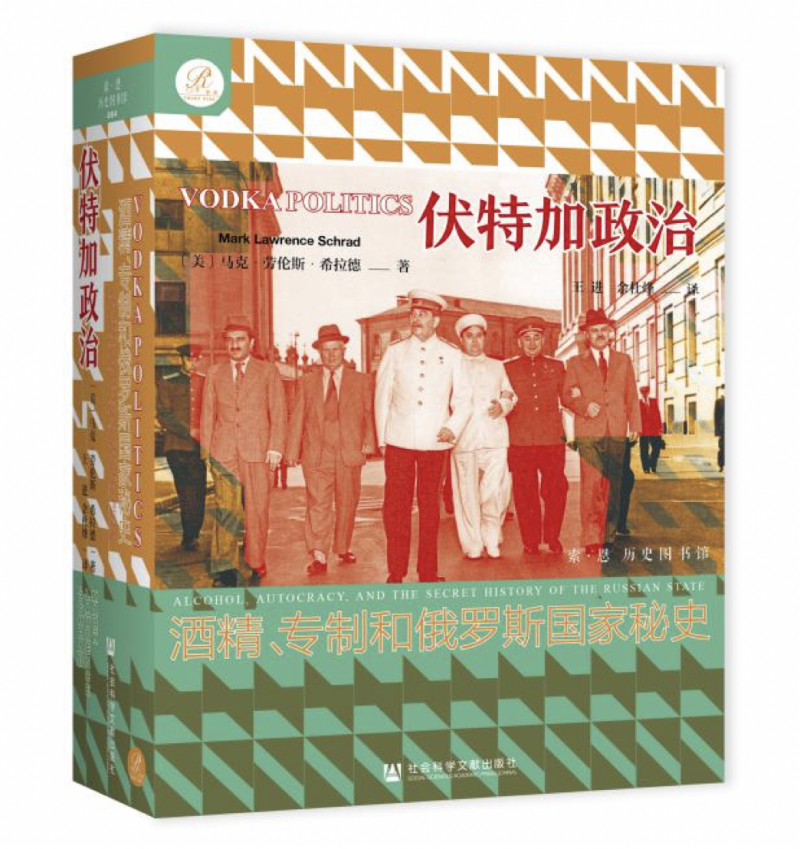如果有一本以伏特加酒为主题介绍俄罗斯的书,俄罗斯读者会如何看待这本书呢?我曾经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类似主题的文章。当这篇文章在俄语博客圈里悄悄走红的时候,我很快就看到一条情理之中的反驳:“伏特加酒?既然你写了这个,不要忘记还有北极熊和俄式三弦琴。”很显然,这条评论嘲讽的是那些轻信他人误导,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俄罗斯的人。伴随这条评论的是成堆的奚落和讥笑的段子。
毫无疑问,讨论这类陈词滥调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特别是当这种贬抑之词牵涉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话题必然会激起来自这个刻板印象所描述群体的激烈反应。很显然,要研究俄罗斯(包括其民族、文化、政治和历史),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被广泛传播且令人不安的刻板印象,这种形象在那些酗酒到无可救药的俄罗斯醉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那些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俄罗斯的人也能很快将俄罗斯与酗酒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学习俄语的人在学会用俄语说“你好”之前早就会说“伏特加酒”了。
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局限于外国人: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全俄罗斯舆情研究中心( VTs IOM)就调研过在俄罗斯人民心里最能代表 20世纪俄罗斯的主要标志:伏特加酒占据了榜首,击败了包括北极熊、俄式三弦琴、俄罗斯套娃,甚至还有 AK- 47 步枪在内的所有对手。当谈及俄罗斯未来面临的挑战时,只有大概 10% 的受访者提到了“国家安全”“经济危机”“人权问题”,大约 25 %~ 30 % 的受访者提到了“恐怖主义”与“犯罪问题”,大约50 %到60 % 的受访者选择“酗酒和毒瘾”作为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这一比例年年如此。
然而,虽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一个世纪前就解决了本国所谓的酗酒问题,但酒精问题仍然继续困扰着俄罗斯的高层领导者们。例如,在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莫斯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差点就阻挠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第三次荣登俄罗斯总统宝座。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Dmitry Medvedev)手下当了四年的俄罗斯总理了。
在重新就职之前,普京在俄罗斯杜马(俄罗斯联邦会议的下议院)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里,强调了岌岌可危的人口和健康问题将是他在接下来的任期里最为紧迫的政治挑战。普京提道,“除去战争或者灾祸的影响,吸烟、酗酒和吸毒每年夺走了50万俄罗斯人民的生命,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数字”。除非普京自己患有健忘症,不然的话他在听到这些确实令人震惊的数字的时候本不应该感到任何意外:在其前两个执政期(2000 ~ 2008年),他几乎用同样的话反复痛惜着伏特加酒所导致的可怕的死亡数字。
自1999年普京开始在俄罗斯政坛获得关注以来,俄罗斯的各项社会指标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遭受重创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倒退的基础上,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在1998年至2008年这十年里,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可以达到大约 7 %,直到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虽然俄罗斯宏观经济指标呈现反弹趋势,但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指标却更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欧洲国家。
即使在今天,俄罗斯青年男性的平均寿命超过65岁的概率,甚至低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这样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和这些极端地区不一样,危害俄罗斯的不是营养不良或者饥荒饥饿,更不是内战当中的流弹误伤:罪魁祸首显而易见,就是伏特加酒。俄罗斯人每年平均要喝下18升纯酒精,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最高安全饮用量的两倍之多。2009 年,时任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将酒精称为“国家灾难”,宣告发起抵抗伏特加酒的新一轮战斗。
俄罗斯在文化层面对伏特加酒的沉迷是颇具悲剧性的,而且这种沉迷常常被归结为“对俄罗斯人灵魂的一种折磨”。但简单地将酗酒和自我毁灭行为归结为某种与生俱来的文化特性, 看作是俄罗斯人在基因层面不可剥夺的部分,无疑是欲加之罪。俄罗斯的伏特加酒灾难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正如我论述的,俄罗斯人长期以来对伏特加酒的沉迷,以及这种沉迷所带来的各种劫难,实际上是近代俄国专制政权制造出来的一种政治灾难。在近代俄国专制政权崛起之前,中世纪的罗斯人就已经饮用着谷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啤酒和麦芽酒, 由蜂蜜自然发酵而成的蜂蜜酒,以及由面包自然发酵而成的卡瓦斯酒。富人阶层则饮用着进口的葡萄汁和樱桃汁发酵出的各类红酒。他们饮用的酒水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相差不大,而且饮用的数量和方式也差不多。
然而,在引进改变原本依赖自然发酵做法的蒸馏法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借助蒸馏法生产的烈性酒和伏特加酒的酒精浓度和盈利能力是依靠大自然力量的自然发酵酒无法比拟的。从 16世纪开始,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和沙皇们就垄断了利润丰厚的伏特加酒贸易,并迅速将其发展为从其臣属子民身上榨取财富和资源的主要手段。
政府通过酒精控制社会大众并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做法:即使是在19世纪,蒸馏酒在对非洲殖民地进行“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奴役黑奴方面都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但酒精在俄国独裁的沙皇政体和苏联的国家治理手段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根深蒂固, 而这也给今天和未来的俄罗斯联邦留下了难以处理的后遗症。
让民众沉溺于伏特加酒的做法在道德层面、社会层面和健康层面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要国力强盛,国库充盈,这些问题都可以被轻易地一带而过。至少在维护专制政权的稳定性这件事上,酗酒让民众走向酒馆而不是罢工抗议警戒线,反倒是一个额外的好处。总而言之,只要专制政权有存在的合理性,伏特加酒问题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它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分不开。
这是否意味着伏特加酒在俄罗斯是万能的呢?当然不是,但它却可以影响很多事情。我并不想用一个简单的因果来分析俄罗斯历史:如果主张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都可以用酒精解释,这无疑是愚蠢至极的做法。与此相反,我所写的《伏特加政治》一书可以作为观察、理解俄罗斯错综复杂的政治发展历程的另一个视角。这就像是以一种酒后眼里出西施的看法看待俄罗斯历史:但这并不会扭曲我们的认知,借助伏特加政治的视角查阅俄罗斯历史实际上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聚焦在关键点上。
伏特加政治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近现代历史上那些以喜怒无常的著名专制君主,以及他们统治臣民的方式。它凸显了在包括战争、政变和革命这些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中发挥重要作用,却被忽视的动因。它填补了我们在解读俄罗斯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空白。它赋予我们欣赏俄罗斯文学巨著的新视角,并以一种全新角度诠释了俄罗斯的国内动态。最后,他或许还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伏特加政治遗留问题给建设一个健康、繁荣、民主的俄罗斯未来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今日的俄罗斯民众已经意识到酗酒这一巨大问题,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也都不能不承认伏特加酒很可能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认真分析俄罗斯的酒精问题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和应对未来,这要比回避一个过于敏感和令人难安的老套话题、出于礼貌拒绝参与讨论陈词滥调重要得多。实际上,不同派系和国籍的学者们早就已经开始这项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了。
这本书不是关于伏特加酒的第一本传记,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本。俄罗斯人在国家历史中记录酒精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868年伊凡·普雷若夫(Ivan Pryzhov)的《俄罗斯的酒馆史》。之后俄罗斯国内外很多关于酒精主题的通俗文学作品均认真调研了我们现在口中的伏特加酒的起源和词源,但很多分析都局限在表面。更有价值的是那些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统计学家以及公共卫生专家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俄罗斯酒精历史这一很小的专业研究领域并写出了很多重要文献。
不同于那些粗略描述伏特加酒的社会历史作品,我的研究立足于更加严谨的学术研究以及很多来自俄罗斯、欧洲以及美国档案馆里从未被披露的原始史料,通过调查从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到2012年俄罗斯大选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伏特加酒是如何与俄罗斯政治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进而描绘出一幅酒精在俄罗斯政治历程中的演化图。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美化酒精,也不是恶意嘲讽俄罗斯的酗酒问题,更不是宣扬东方主义或者反俄罗斯情绪。这本书所讲述的是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酒精对政治事件的各类影响和催化作用(以及政治事件对酒精的反作用 )。酒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独特政治作用的现象并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实际上,W. J . 罗拉鲍尔(W.J. Rorabaugh)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酗酒共和国》以同样的新视角审视美国的早期历史:由于反对英国殖民者的革命行动都是发生在烟雾缭绕的酒馆里,当时的美国被很多人视为“醉鬼的国家”。
早在1930年代早期,美国殖民地最成功的报纸《宾夕法尼亚周报》整理了一份多达220条描述醉酒的口头语,同时还刊载了各类关于外国政府如何处理猖獗的酗酒现象的报道,这些新闻报道的作者正是年轻的费城出版商人、未来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实际上,美国多位开国元勋都与酒精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或是红酒制造商,或是啤酒场场主,或是白酒酿造商。威士忌生产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甚至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标志性领导者。
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应对酒精的历史,但或许在其他国家,酒精问题并不会持续到现在,更不会像俄罗斯这样与其民族文化、社会与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将近二十年来推动我开展研究的,我对俄罗斯(包括它的人民、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喜爱与迷恋传递给读者们。
注:本文节选自《伏特加政治》中文版序言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