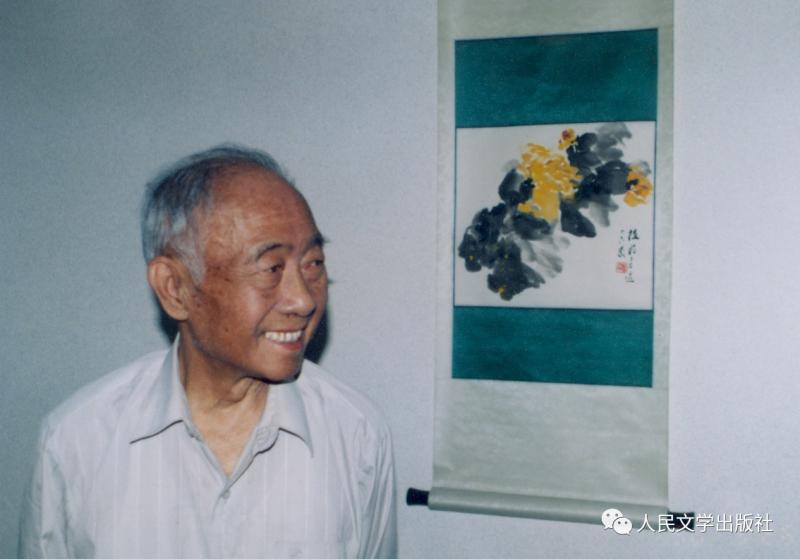汪曾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书,是在1985年。当时他六十五岁,被家里人称为“老头儿”有些年头了。这倒不是人文社以前对这个老头儿看不上眼,主要是他在六十岁之前少有作品问世,1980年后才进入第二个创作高潮(第一个是在解放前),写了不少有点儿影响的小说。有了作品,人家才有可能给你出书,是吧?
那本小说集叫《晚饭花集》,是老头儿自己起的名字,他还用毛笔写了书名。人文社对这本书挺重视,专门找人画了插图,在老头儿的作品集中,这好像是独一份。大概是因为过于重视,编排中还出了点儿小岔子,把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排成了“常规”,最后只好重新制作封面。这件事还藏不住,因为老头儿在给几个人的信里都提到过,这些信后来都收入了《汪曾祺全集》,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除了这点儿岔子,老头儿对这本《晚饭花集》都还满意。1987年他去美国参加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撑门面的主要就是这本《晚饭花集》,给作家们送了不少本,多数人不懂中文。当然也有懂的,像台湾的陈映真、陈若曦,应该还有蒋勋。蒋勋和他是同一期的,两人接触挺多。
1992年,人文社给汪曾祺出了第二本书,是“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中的一册,有小说也有散文,三十多万字,封面是浅蓝的,挺雅致。老头儿对这本书也挺满意。他在序言中说:“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要出我一本选集,我很高兴。我出过的几本书,印数都很少,书店里买不到。很多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存书陆续送人,所剩无几,已经见了缸底了。有一本新书,可以送送人。当然,还可以有一点儿稿费。”有一点老头儿说得不对。他出的书并不是印数都很少,像《晚饭花集》标明的印数是“47000册”,相当可以了,另一本《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印数也有两万多。只不过后来找他要书的人多起来,他存的书又不太多,就想当然地认为书的印数少了。汪曾祺对于数字向来比较糊涂,包括稿费。这本书与老头儿还有一份特殊缘分。1997年他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把两本蓝皮书带到了告别仪式现场,我们拿出一本放在了他的身边。如果老头儿在天有灵的话,随手翻看的应该就是这本书了。
老头儿生前,还有一本散文集准备交给人文社出版,在篇目上也做了一些挑选。这本书就是《中华散文珍藏本·汪曾祺卷》,1998年印行时他已经不在了。
人文社的编辑干起事来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儿。《晚饭花集》1985年8月出的书,编辑江达飞1983年上半年就经常上门找老头儿扯闲天了,一来二去和家里人混得挺熟,有时老头儿还留他吃顿便饭。有这等关系,想要出什么书自然是手到擒来。《汪曾祺全集》书信卷中,收录了一篇老头儿1984年写给江达飞的短信,其中说:“我今年要为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节目做点儿工作,恐怕写不了什么东西。目前只能翻来覆去地读《汉书》。”老头儿提到的《汉书》,是人文社资料室的。当时他几次表示要写个长篇小说《汉武帝》,江达飞得知赶紧把《汉书》等书籍送到家中,做点儿铺垫,等着老头儿供货。最终,汪曾祺也没写出《汉武帝》,还划拉走人家好几本书,不带还的。这些书在家里放了三十多年,后来我们连同他书房里别的书籍一道捐给高邮的汪曾祺纪念馆了,作为老头儿和人文社交往的见证。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前两年,我们整理家中杂物时,翻出了一些老头儿画的画,其中一幅画的是晚饭花,花型有点儿像小喇叭,浅浅的紫红色,上面还写着几个字:晚饭花集。看来这个老头儿对于这本书还是挺在意的。如果《晚饭花集》再版,用这幅画做封面倒是原装原配。不过人文社是用不着再出这本小书了,他们给汪曾祺出了一套大书——十二卷的《汪曾祺全集》。
这套书出得实在是费劲儿,从确定方案到2019年初正式面世,整整用了八年时间。当初商议出书时人文社的编辑刘伟的女儿刘子心还不到一岁,到全集出版时,孩子都上了小学三年级,暑假中能蹦蹦跳跳地跟着爸爸,到书展上给老头儿卖书去了。这八年,人文社的领导,有的进步了,有的调动了,也有的退休了。具体做事的编辑,好像没有什么升官的,退休的倒是有。没退休的,变化也挺大。像主持编辑工作的郭娟,头发就白了不少,刘伟的头发倒是看不出白没白,但是脑门更亮了。时光容易把人抛,一套《汪曾祺全集》,熬坏了不少人。
《汪曾祺全集》出得这么费劲儿,主要是人文社的上上下下干起事来太较真。我们家里人对于这套全集的想法原来很简单,最好能出一套“顺溜本”,把发表的作品中明显的错字和疏漏之处改正过来,便于读者阅读就行了。没想到参与编书的各方人士,非要突出全集的学术色彩,各篇文章都要找到原刊处,还要对照手稿核校。这下可麻烦喽。汪曾祺对自己的作品一向粗粗拉拉,从来不习惯留底稿,文章发表后寄来的报刊也不怎么整理,东一篇西一篇地乱扔。解放前发表的文章更是一篇存底也没有。另外,家里人也没把他太当回事,东西发表了,大家随意看看,说点儿闲话,完事。妈妈彻底退休后,给他当起了秘书,文章寄出前会复印两份,不过这已经是很晚时候了。另外老妈的主要重点是管理老头儿的稿费,文稿档案之类还在其次。如此一来,这套《汪曾祺全集》,就得到处搜寻文章的原始出处,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不过这么做确实也有好处。老头儿晚年写过一篇小说《侯银匠》,里面提到侯银匠的女儿侯菊出嫁后,管起了丈夫家一天三顿饭。原来的文字是:
“陆家人口多,众口难调。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个人吃菜爱咸爱淡也都不同。侯菊竟能在一口锅里煮出三样饭,一个盘子里炒出不同味道的菜。”
可是,既然是一口锅里煮出的饭,就应该都是焖饭,犯不上特意强调这一点。恰好这篇小说的手稿还在,最后用放大镜辨认出老头儿写的不是“焖饭”,而是“烂饭”,“烂”字写的是繁体的“爛”,因此最初发表被编辑误以为是“焖”的繁体字“燜”了。这次全集出版时,“焖饭”改成了“烂饭”,顺多了。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经过八年较真,这套《汪曾祺全集》的质量自然有了极大提升,篇幅也比当年北师大出版社的全集增加了许多,收录的小说就增加了二十八篇,其中二十五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有许多作品老头儿自己都记不清了。比如他曾多次说过,上大学时写过一篇小说,自始至终都是两个人的对话。沈从文先生看过之后对他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从此他明白了,小说中的对话也要贴到人物写,不能成为作者逞才的工具。但是这篇小说的题目和内容汪曾祺都记不清了。这次编全集时,这篇小说也被人找到收录进去了,题目是《葡萄上的轻粉》,里面确实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说的全都不是正常人说的话。若不是沈先生的教诲,这个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之路还不知会拐到什么地方呢。
1961年与沈从文先生在中山公园
《汪曾祺全集》的散文卷、谈艺卷,新收文章更多,合计有一百多篇;戏剧卷新增的剧作有七部;诗歌卷收录汪曾祺诗歌二百五十七首,较北师大版(八十八首)多出一百六十九首,其中四十余首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书信卷收入老头儿写给不同人的信件二百九十三封,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只收汪曾祺书信五十五封。这些新收入的作品,家里人提供了一些,多数都是人文社编辑、聘请的社外编辑和老头儿的粉丝从各处搜寻来的。像汪曾祺1961年底调到北京京剧团后,写的第一个戏是《王昭君》,当初只在单位油印过剧本,没发表过。“文革”后家里就再没见过这个剧本了,大概是“破四旧”时处理掉了。上次北师大出版社出老头儿的全集时,我们问过曾经演过这个戏的李世济,是否还存有这个本子,她说早就不知哪儿去了。想不到,这次编全集时,我们在旧书网上发现《王昭君》竟然还在,只是被人买走了。得知这一信息,《汪曾祺全集》书信卷主编李建新四处打探,居然找到了剧本的买主,拿到了复印件,最后收入全集中。老头儿如果在世,看到这个剧本时隔五十多年重见天日,也会高兴的。
不过,老头儿若还在世,难免受到家人的数落。因为他写东西,有时实在过于随意,给编书的人带来不少麻烦。比如剧本中的某个人物,他只写了什么时候上的场,但是等到这一场结束时,台上已经没有此人踪影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溜下去的。人文社负责全集剧本卷的编辑杨康,只好找到我妹妹汪朝,共同商量该人何时下场最为合理,并在剧本上标注出来。类似的问题不知有多少,直到把杨康熬退休了才算完,实在让人不好意思。
人文社编辑的工作环境也太差。我第一次去社里找郭娟时,开始摸错了地方,好像是到了集体宿舍。有一家的房门没关,门口挂着一块黑乎乎的布帘,透过布帘的缝隙可以看见里面摆着一张大床,斑驳破旧的桌椅,和农民工住的地方差不多。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部很有影响的电影《邻居》,说的是住在筒子楼里几户人家之间的故事,没想到当年筒子楼的生活场景居然还能在人文社见到,叫人不知说什么好。郭娟的办公室也好不到哪儿去,屋里黑乎乎的,到处堆的都是大信封和各种书籍刊物,桌椅也都是老货,很有些年头了。这种景象,三十多年前我初到报社工作时还能见到,如今可真是难找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文社的编辑们却能坐得稳稳的,吭哧吭哧编出一本又一本好书,着实让人佩服。老头儿的这套全集出版两年来,已经加印了六次,总印数有二万多套。看来,读者对于人文社的较真精神还是挺认可的。我们自然也跟着沾了光,多领了不少版税。
《汪曾祺全集》能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实在是老头儿的幸运。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