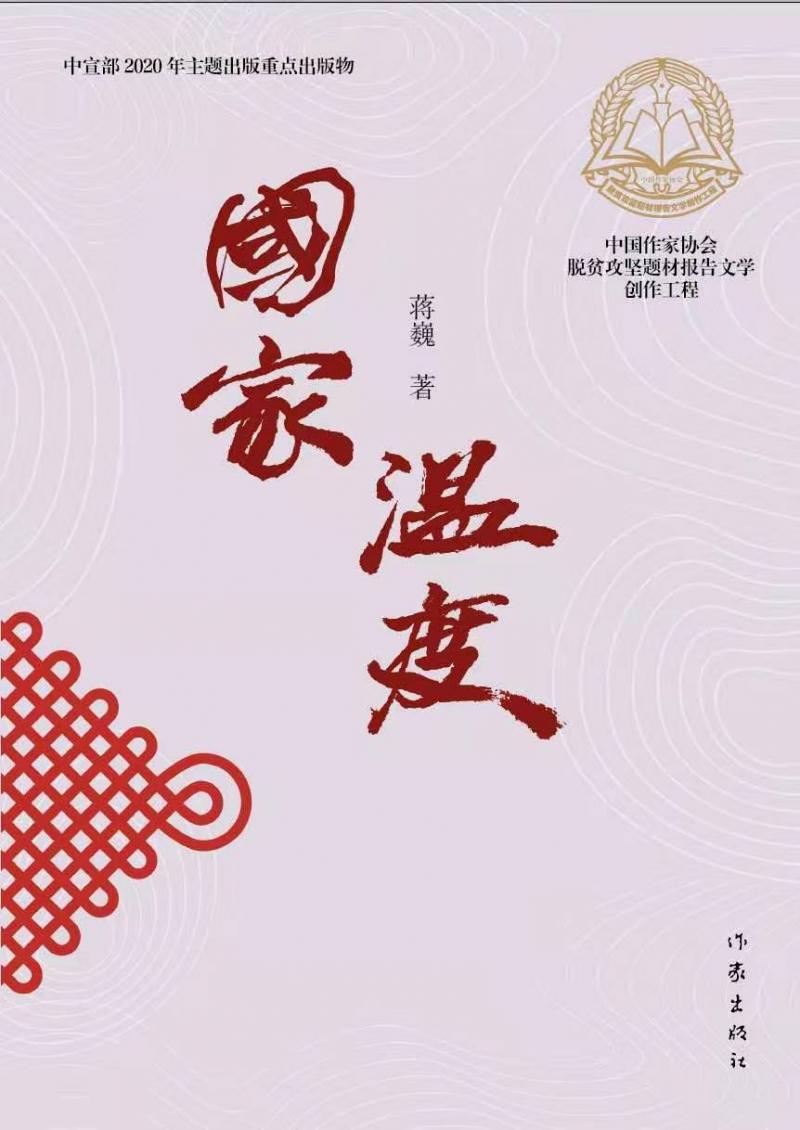从去年9月到今年6月,年过七旬的作家蒋巍从陕西榆林到新疆乌鲁木齐、和田,再到贵州铜仁、上海,直至黑龙江省佳木斯、哈尔滨,完成了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2019-2020我的田野调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12月15日上午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发布会上,蒋巍介绍这部新作时说,“好多读者说报告文学不好看,因为经常只有报告没有文学。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在真实性、文学性、思想性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我不是拿着宣传材料堆砌改写出来的,而是翻山越岭,走村入户,到扶贫第一线去打捞最鲜活的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素材。”
创作脱贫攻坚文学,绕全国一圈八过家门不入
当天上午,73岁的蒋巍出现在“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发布会上,他声音洪亮、富有激情地演讲近一个小时,模样和声势完全不显老。他笑称自己为了创作扶贫攻坚报告文学,辗转东南西北五省七地,绕全国一圈,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回过北京的家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我八过家门而不入,将家完全交给老伴打理,我确实成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
蒋巍称他习惯了这种生活,他喜欢坐在老百姓的小院里、窑洞口、炕头上聊天,他们的故事折射着这个时代发展进程的点滴变化。尤其是在扶贫攻坚一线采访,太多的故事让他泪下,以至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手指纷飞忘情地敲打着键盘,连吃饭解手都觉得浪费时间,常常弄几样小点心边写作边充饥。
在介绍《国家温度》这部新作时,蒋巍还通过书名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站位和人民立场。“可以说,脱贫攻坚这场伟大的战役和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是2020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性质、国家力量的雄辩证明。真理是比较出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事情做得这么漂亮,这么温暖,却还有某些公知一味罔顾事实,抹黑歪曲我们的国家。我在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就说过,作家不要认为只有自己的台灯是最亮的,离你的台灯越远的地方越灰暗。在我看来,扶贫后在全国农村所有地方亮起来的太阳能路灯,要比作家的台灯明亮得多,温暖得多!”
帮瘫痪男孩出版诗集,翔实记录下“一个人的学校”
提及贵州山区,蒋巍的最初印象是,多年前他的岳父去贵州绘画写生。走进山寨里,看到一间茅草屋里昏暗的灯光下,有男人和妇女穿着水泥袋子在地上行走。他们饭桌上的所谓“菜”,是从野地里抓回来的一些虫子,用盐巴腌制后当咸菜。
蒋巍还采访过一位复员军人曹以杰,他转业后在大城市里当高尔夫俱乐部经理,一直过着高级白领的生活。有一次,他回到贵州家乡,看到一个老奶奶半身赤裸坐在洞口抱着孙子,一头牛则在洞里“哞哞”叫着。曹以杰想不通,问老奶奶,“这么冷的天,快下雨了,为何不将牛牵出来,自己到洞里坐着暖和一些。”老奶奶回应说,“牛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死得,牛死不得,不能放在外边,丢了咋办?”曹以杰听了这话很心痛,决心辞职回乡承包山头创办茶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正是这种山区极度贫困与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让贵州奋起,驻村干部拼了命地干,帮老百姓脱贫。这其中,就有贵州省交通厅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萧子静,他在黔西县雨朵镇驻村扶贫。有一个孤老头来找他办事,看着行走举止动作非常困难,原来老人指甲和脚趾甲好些年未修剪过了,曲曲弯弯绕了好几圈,而且伴着肮脏、疼痛和流血。萧子静很痛心,端来一盆温水给老人洗泡过之后,细心帮他剪了长长的指甲和脚趾甲。从萧子静的叙述中,蒋巍深深感悟到,扶贫不仅仅是帮村民种地盖房这么简单,其实是生活的全部!
让蒋巍难以忘怀的是,在这个镇上,有一个高位截瘫的男孩沈江河,他每天坐在家门口晒太阳,用仅仅能动的一只手在写诗,写土地,写母亲,诗写得很温情很感人。萧子静看到这个男孩病入膏肓,决定动员社会力量为沈江河出一本诗集,以期对他有所激励和慰籍。数月后,这本诗集出版了,书名叫《一根手指的舞蹈》。看到散发着墨香的诗集,沈江河和全家都哭了。一年后沈江河去世,这本诗集随他入棺。蒋巍将这段故事写入他的新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主战场》。
沈江河
在扶贫一线每一天的采访,都是激情在指尖上跳跃,泪花在键盘上飞溅。那一次,蒋巍在同当地干部的闲聊中听说了大山里的“一个人的学校”,他立即决定:去看看!和第二天他和扶贫办的同志一起乘船渡过乌江,又翻过两座山,才到了这所“学校”,见到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乡村女教师杜典娥。
这里交通不便,村民生活极为贫困,许多年里女孩子都不上学,更不敢外出打工,因为她们领工资不会签名,上街不认识街牌。于是杜典娥毅然放弃自己外出打工的准备,在自家办起一所只教小学前三年课程的“学校”。一是因为她觉得再高的年级自己教不好了,二是教到三年级,孩子们身体壮了,胆子大了,就可以渡江去对岸上正规的小学了。山里农民很穷,交不起学费,杜典娥便约定每个学生一年只交6斤米。孩子们喜滋滋来杜家上学了,最小的6岁,最大的14岁。
蒋巍深入贵州山区“一个人的学校”对乡村教师杜典娥(穿紫红棉衣)做采访
就这样寒来暑往几十年,杜典娥青丝变白发,先后教了几千名三年级学生。迄今杜典娥还保留着那个已经发黑的6斤米账簿,其中有许多还没划钩的,是当年的学生还欠着的,有些则是学生的儿子或孙子帮着还上的。杜典娥说,她留着这个本子不是为了催账,而是为了纪念,因为这就是她的一生。蒋巍看到,如今杜家门上还挂着当年的上课铃——一个铁盘子早已锈成文物,现在用的是电铃了。
采访铜仁易地搬迁工程,脱贫消息传来扶贫干部们抱头痛哭
除了记录下扶贫攻坚战役中这些小人物的冷暖人生,蒋巍还将激情投入到易地搬迁工程中。在贵州,需要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就达188万,全国最多,且大大超过三峡移民数量。
这其中, 铜仁市是移民搬迁任务最重之地:作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全市所辖10个区县均为贫困区县,共计1565个贫困村,其中1个深度贫困县 (沿河县)、2个极贫乡镇、319个深度贫困村,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2.7万。且大多数贫困群众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寒山区,居住分散,耕地匮乏,用水艰难,基础设施、文化教育极端落后。总之,活在那里就意味着困在那里,老死在那里。别无出路,实现脱贫只能靠一个字:搬!
在铜仁市,经逐村逐户摸排统计,到2020年底,全市总共需搬迁29.33万人,占全市人口近十分之一。其中需要跨区县搬迁的达12.55万人。一个地级市易地搬迁人口数量如此之大,全国独此一家。铜仁市在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之余,也做好“后半篇文章”,在搬迁安置点配套建设了学校、医院、商超、工厂、市民活动中心、公共服务系统等。同时千方百计鼓励企业在安置点创办“扶贫微工厂”,让以前不得不远出打工的农民可以“增收兼顾家”,让搬迁群众“一步住上好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
“采访中,我看到一些女孩子们抱着电线杆子焦急地等待脱贫验收的结果。一旦抽到合格了,整个县脱贫,消息传来的时候,所有扶贫干部抱头痛哭,他们高呼口号,‘我们来了!我们胜利了!’在我眼里,这些充满热血激情与担当精神的扶贫干部值得好好记录。”蒋巍说。
冷思考:要防止扶贫解困“同质化、一窝蜂”现象,建立扶贫长效机制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如实记录下贵州、新疆、榆林等省市脱贫攻坚伟大壮举的同时,蒋巍也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首先要尽可能避免扶贫项目“同质化、一窝蜂”现象。“从北到南,我走过的很多地方,为扶贫解困,当地都在鼓励扶持发展产业,比如苹果、核桃、红枣、茶叶等等。我想,市场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多年以后,这些农副产品堆积如山、供大于求的危机将是非常现实的威胁与挑战。 农民的投劳和合作社的大笔资金投进去了,产品却难以推销甚至烂在地里,导致已经脱贫的农户又返贫,怎么办?”
蒋巍在陕北杨家沟,和老乡们聊天
对此,在他看来,要建立扶贫长效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乡扶贫的干部多是城市出身,且多是党政机关干部,他们对农村较为陌生,对市场经济运行及其规律不很熟悉。类似“两不愁、三保障”这样的“填鸭”政策谁都会,但是把农民群众推上市场经济轨道,从而获得强大的内生动力,就需要一定的智慧和本事。
蒋巍在书中列举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在某省的扶贫工作座谈会上,一位扶贫干部汇报了他的一个正在积极推进的大项目,因其帮扶村庄邻近省会,他号召全村农民大举种植蔬菜,然后在市里租一大间门市房,将那里作为村民蔬菜的“出口”,听起来很美妙,却当场遭到一位农民的反驳:门市房一年16万元租金能不能挣回来?农民租车开车送菜费用能不能挣回来?蔬菜淡季没菜卖怎么办?如果亏了,等于留下一堆后患。
这位农民当场出了一个主意:可联络联合几个大企业大公司食堂,和这个村合作社共办一个电商平台,双方共养一辆车,每天各单位需要什么菜、多少菜,在平台发布,由专用车辆送菜上门。村民不出门就可以把菜卖掉了,全场皆表赞同。
在蒋巍看来,这就是一位城市机关干部和懂市场规律的农民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在扶贫工作中,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才能激发内生动力,建立长效机制。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