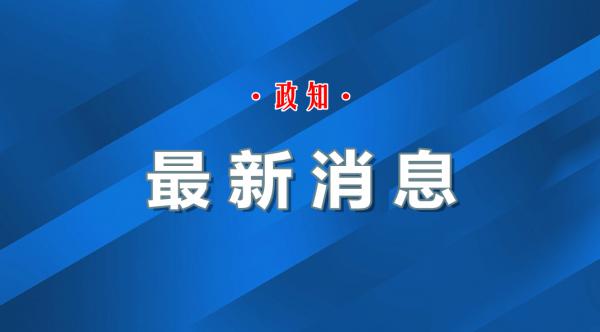10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他表示,人民检察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履行刑罚执行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有力惩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公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积极促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刑事执行检察,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强制医疗所等执行机关和监管场所执行刑罚、刑事强制措施、强制医疗措施和监管执法活动实施的法律监督。它既是法律监督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屏障。
近日,北青报记者跟随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巡礼·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媒体采访团走进安徽,实地探访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监督无死角
筑牢司法“最后一公里”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是法律监督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王勇说。
何为刑事执行检察?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贯穿刑罚执行全过程,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刑事强制措施执行监督,是对拘留、逮捕措施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的监督;二是刑罚执行监督,是对刑罚交付执行、“减假暂”等刑罚变更执行、社区矫正等刑罚执行和相关监管执法活动的监督;三是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是对强制医疗所等执行场所对被强制医疗人员的监管和医治活动的监督。
2020年至2025年6月,安徽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提请审查案件100641件,针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的严重违法情形,提出监督意见20518件。
如何让监督落到实处?安徽检察机关打出“组合拳”——惩罚犯罪与保障权益并重。
一方面“严格依法履职”。以“加强重点领域专项监督”为例。聚焦“收押难”“收监难”问题,安徽开展了审前未羁押判处监禁刑罚未交付执行监督,通过“检察建议+催办函+建章立制”工作模式,推动全省未交付执行罪犯实现“动态清零”。聚焦不遵守食药、教育行业从业限制、重操旧业等问题,开展“禁止令”执行专项检察,依法守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特定群体安全。
此外,安徽省检察机关坚持把查办职务犯罪作为强化刑罚执行监督的有力手段。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涉刑罚执行领域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2人。
案例是最鲜活的证明。合肥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监狱干警利用职务监管便利,长期捎带香烟、酒水等物品进入监区,加价贩卖给服刑人员谋取非法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以滥用职权罪提起公诉,获法院支持。
另一方面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建立完善“派驻检察官信箱制度”,规范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工作,依法受理控告举报申诉,保障在押人员生活、学习、休息、劳动、教育等合法权益。2020年以来,妥善办理刑罚执行领域信访3354件。同时,维护监管秩序安全稳定,依法严惩在押人员行凶、闹监、越狱逃脱等犯罪,重拳打击“牢头狱霸”问题,共起诉在押人员又犯罪70人。
“每个驻所检察室均配备至少两名检察人员,其中至少一名为检察官。”蚌埠市检察院检察官乔炎鑫说。
据乔炎鑫介绍,驻所检察室主要围绕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确保监管活动合法性等内容开展常态化的监区巡视,还会定期查看检察官信箱、与在押人员谈话、参加看守所的动态分析会等,“如果监室内出现违法违纪现象,或者监管民警存在对在押人员殴打、体罚等问题,我们会立刻口头纠正。如果看守所不及时改正,我们会发出《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全省95个监管场所派驻检察室均已完成“两网一线”建设,实现了执法司法业务数据实时共享,派驻检察人员轮岗交流比例达到44.76%。蚌埠市检察院将监管场所违规使用戒具、违规采用惩戒措施等违法违规情况作为派驻检察重点,持续加大监督工作力度,依法办理相关案件565件。
办案有智慧
刚柔并济彰显司法温度
“案发前,他是一家银行的部门总经理,如今却声称家庭经济困难,是真实情况还是另有隐情?”白湖人民检察院检察二室副主任、一级检察官徐明在审查罪犯邹某减刑监督案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疑点。

邹某曾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贿赂,2018年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80万元。2025年4月,邹某申请减刑,监狱认为其原案案情复杂,商请检察机关同步介入监督。
根据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
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徐明所在的白湖检察院,是安徽省人民检察院3个派驻监管场所的检察院之一,主要负责对4所监狱开展刑事执行法律监督工作。该检察院在实践中探索创新了“阅、谈、查、析”四字实质化审查工作法——书面阅卷,“阅”全实体要件;当面谈话,“谈”明深层问题;亲历调查,“查”实问题线索;综合研判,“析”出精准画像。
“邹某一案的证据材料较为齐全,但我们深入审查后就发现了疑点。首先是他作为银行原部门总经理,却提供家庭经济困难证明,真实性存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困难呢?带着疑问,我去查看他提供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又发现了问题——虽然载明了其‘家庭经济困难’的结论,却缺少其个人名下、家庭房产、存款等财产信息的描述。”徐明说。
疑点还不止于此。检察官在核查邹某财产刑履行情况时发现,邹某履行了没收个人财产80万元,至于巨额赃款有无退缴并无证据证明。“因此财产刑履行完毕属于‘以偏概全’”。
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带着这些疑问,检察官走出办公室,启动“谈”与“查”环节。
“‘谈’主要是与罪犯面对面交流”,‘查’是赴邹某经常居住地进行调查,利用当地不动产登记中心信息查询系统、车辆管理所信息查询系统。”徐明介绍,“我们查明邹某及其妻子名下有三套房产、一处商铺以及一辆沃尔沃牌SUV汽车,且房产位于市区较好地段,市场价值不菲。”
此外,检察官还利用驻监检察室工作平台,掌握到邹某夫妻在外地还有一套未登记的别墅。综合各方信息后,检察官进入“析”的环节,通过综合分析研判,精准还原出邹某伪造家庭经济困难证明、企图“投机减刑”的真实面目。
检察官作出了“不同意对其提请减刑”的检察意见。“此外,针对邹某财产未受到查封处理问题,我们将该法律监督线索移送给当地检察机关。当地检察机关依法及时核实,启动监督纠错程序,目前法院已经对邹某相关财产进行了查封。”徐明说,“通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线索移送机制,织密了一张维护刑罚变更执行公平正义的法网”。
于法有度,于情有声。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除了进行刚性监督、维护司法公正,还会在法律框架内传递司法温度,助力企业焕发生机。
“我经营的电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亟须本人赴上海、江苏等地洽谈业务,向司法所申请外出,但未被批准,特向湾沚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法律监督申请”,2020年8月,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了社区矫正对象管某某的反映。
管某某,芜湖市人,是一家电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7年前往江苏昆山办厂,2015年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其经营的公司共有员工近200名,年均销售额7000万元,年均纳税400余万元。
“公司业务一直由我负责经营管理。当时,公司销售业绩下滑约40%,面临停产危险,亟须我赴上海、江苏等地拓展加工销售市场,帮助公司复工复产。”管某某说。
接到反映后,湾沚区人民检察院立即开展了调查走访。
“经查阅管某某原刑事案件卷宗、社区矫正档案,走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综合分析其原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态度等情况,同时查明,管某某在犯罪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社区矫正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未发生漏管、脱管情况。”湾沚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副主任仇小雷说。
为何司法所未批准其外出?司法所认为,管某某申请外出进行市场调研、拜访客户、开拓市场不是外出直接从事销售和生产经营,且客户又未发出邀请函,故请假事由不充分,不符合社区矫正法规定的“有正当理由”。
“我们审查后认为,管某某所经营管理的公司主要是为其他企业生产、加工配套产品,在经营方式上更需要主动与其他企业客户加强沟通联系,而不是坐等客户发来邀请函,那样就会失去商机。管某某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决定权,其外出开展市场调研、拜访客户、洽谈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企业开拓市场,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应属于‘处理工作重要事务’的正当理由”,仇小雷说。
他还提到,同时,管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能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创业热情较高、回报社会意愿较强,现实表现良好,造成社会危险的可能性较小,其申请外出从事企业急需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关于申请外出的条件。
2020年8月26日,湾沚区人民检察院与湾沚区司法局召开联席会议,检察机关结合管某某原判罪名情节、有期徒刑缓刑考验期间改造表现、申请外出事由等情形,提出社区矫正机构应依法批准管某某外出的检察意见,并与司法局就批准管某某请假外出事宜达成共识。
2020年9月10日,司法所批准管某某外出4天。之后,管某某又因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外出共计11次,均被批准。
“我外出期间拓展业务,开辟新市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企业未出现停产、裁员情况,稳定提供就业岗位近两百个,实现销售额七千余万元、利润三百余万元,成功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走出困境。”管某某说。
科技赋动能
织密智慧监督“防护网”
在无为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检察官助理张志成介绍了一项由他们自主研发的“社区矫正对象违法犯罪及收监执行监督模型”。
根据法律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尽管法律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对象有被依法决定拘留、强制隔离戒毒、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限制人身自由情形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社区矫正机构”,但实践中信息壁垒仍然存在。

“这个模型于2024年上半年研发完成,它能通过深度整合分析社区矫正管理中心在矫人员和看守所出入所、拘留所出入所人员数据,精准筛查‘应通知而未通知、应收监而未(漏)收监’的案件监督线索。”张志成说。
张志成,1999年出生,是该项目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他说,“我们年轻人嘛,更愿意拥抱新的东西。”但同时他也坦言,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文科生,最初面对“模型”“大数据”这些概念时也曾头疼。“但真正用起来才发现,其实很方便,上手很快。”
他进一步解释,创建模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有现成的底层代码,就像使用一个高级的Excel表格。我们要做的是结合办案灵感,把逻辑理清楚,系统就能自动生成模型。遇到太专业的问题,再请教技术人员。”
模型的实用性在具体案件中得到了验证。
在“刘某收监执行监督案”中,刘某在社区矫正期间因购买并吸食笑气被无为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2日,符合收监执行条件,但公安机关未将行政拘留决定告知无为市司法局与无为市人民检察院,导致“社区矫正-行政拘留-收监执行”这一链条断裂,司法局无法依据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请收监执行,检察院亦无法监督司法局是否提请收监。
“模型筛查出这一线索后,我们迅速建议司法局向法院提请对刘某收监。同时向无为市公安局提出监督意见,督促其加强与司法局、检察院的沟通协作,及时将社区矫正对象违法情况进行信息通报,打破信息壁垒。”张志成说。
他还提到,“过去是事后监督,要靠人工在海量数据中比对,效率很低。现在,应通知未通知、应收监未收监的比例已大幅下降。”
数据显示,自2024年至今,该检察院运用数字检察模型共发现监督线索50余条,根据核查发现的不当情形,向相关单位依法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17份,检察建议书12份,对严重违反监管规定等情形的12名社区矫正对象依法建议社区矫正机构向法院提请收监执行,相关办案数同比上升80%。该模型已在全国范围内应用成案230余件。
在无为市人民检察院,像张志成这样拥抱科技的年轻检察官并非个例。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干警李建强介绍了另一套“驻所检察室AI智能视频分析监督系统”。该系统连接看守所百余个监控画面,涵盖50多个监督点,能实时监测推搡、捎带物品等行为,并立即向驻所检察官推送线索,被称作“24小时驻所检察官”。
“我们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处理系统推送的可疑线索。无问题的批量删除,有问题的进一步调查、固定证据。”李建强说,“过去回看监控就像大海捞针,几秒钟的关键画面一不留神就错过了。现在系统能一直盯着,把可能存在的问题线索精准推送到我们面前。”
这一“24小时驻所检察官”,已经“揪”出了不少问题。
就在今年9月,在无为市看守所内,一名在押人员遭受他人欺凌,被欺凌的方式诸如掐一下、踢一脚等,因动作小、瞬间发生,在传统视频监控下很难被发现。然而,该系统在一个月内针对同一监室发出的高频预警,引起了检察官的警觉。通过深入分析,锁定了个别在押人员实施的隐蔽侵害,让这些“牢头狱霸”的狐狸尾巴无处遁形。
这只是安徽省检察机关利用科技赋能监督的其中一例。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与省监狱管理局加强数据资源共享,试点建设刑事执行案件业务系统协同模块,实现减刑、假释案件网上协同办理、自动生成案卡和智能化流转,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刑罚执行工作效率。目前,全省已实现在押人员基本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合肥、安庆等地检察机关打通社区矫正数据共享壁垒,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同步实时监督。研发并推广数字监督模型104个,办理相关监督案件702件,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507件、检察建议22件。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