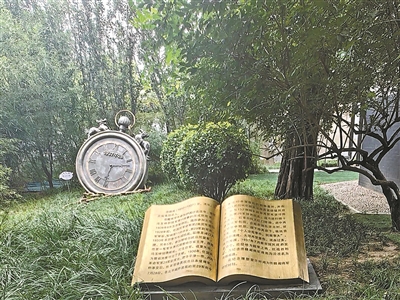北京佟麟阁路上,刻着佟麟阁将军纪念碑文
六月的阳光,洒在北京宛平城斑驳的城墙上。103岁的佟亦非老人坐在轮椅上,由后人推着缓缓行过卢沟桥。她颤巍巍地伸出手,轻抚着石狮身上岁月的痕迹,仿佛在触摸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父亲不会老……”老人喃喃自语,初夏的暖风吹起她银白的发丝,“我想再抱抱他……”这一刻,时间仿佛倒流回88年前那个血与火的夏天。1937年7月28日下午2时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将军在南苑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年仅45岁。那一年,二女儿佟亦非刚满15岁,她目睹了父亲牺牲后被送回家的情景。从此,将军的音容笑貌,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女儿的少年时光里……
近日,笔者在整理旧籍时,发现多年前从旧书摊上淘到的数封佟亦非老人于1985年6月自重庆寄往武汉的家书。信纸已然泛黄,墨迹却依然清晰。这些跨越三十余年的文字,不仅记录了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深切怀念,更让我得以窥见一代抗日名将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
印象深刻的是,在讨论以佟麟阁将军为原型的影视创作时,佟亦非在信中建议:“剧名是否用《大刀记》?”她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渊源:作曲家麦新在报纸上看到二十九军大刀队战士陈永德一人砍死9个日军、缴获13支枪的报道后,热血沸腾,当即谱写了这首荡气回肠的战歌。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佟亦非对细节的严谨令人动容。
还有关于抗战初期军服制式,她准确描述:“那时没有专门的将军服。二十九军官兵均穿灰布军装,翻领(以领章区分级别),系武装带,帽子与八路军相似,前折沿,上有两扣。”随信还附有她亲手绘制的示意图,笔触精细,一丝不苟。
在女儿的记忆中,将军的形象永远那么鲜明:“父亲检阅部队时骑马,穿着锃亮的马靴,披黑色呢大氅,佩指挥刀;平日则与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和布便鞋。每次回家,我们姐妹都会争着为他解绑腿。冬天他戴灰呢礼帽,在家戴棕色黑边毡帽。沉思时,他常戴茶色眼镜踱步。”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威严而不失慈爱的父亲形象。
更令人感动的是,即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佟将军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他要求六个子女定期寄送习字作业,亲自批阅后再寄回。殉国前一日,他还特地托人将儿子佟兵的大楷作业从战场捎回家中。这令人想起鲁迅先生那句名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将军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爱家与爱国,从来都不是对立的选择。
在家中,家人称佟将军为“先生”而非官职。他敬重相濡以沫的妻子彭静智,曾深情地对孩子们说:“我事业成就,一半归功于你们的母亲。”他赠送夫人的手镯上刻着“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这枚手镯,已成为那段烽火爱情的永恒见证。
佟亦非还回忆起父亲在任察哈尔省代主席、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时,与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著名将领在自家院里踢毽子的温馨场景。想想这些在中国抗战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像孩童般嬉戏玩闹,这幅画面既让人忍俊不禁,又令人感慨万千。其间,佟将军曾带孩子们骑马到赐儿山,一边为他们拍照,一边讲述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父亲常说,”佟亦非写道,“做人要有气节,更要有民族气节。”
轻轻叠起这些落款为“亦非”、“雅农、亦非、先煜”的信件,笔者不禁感慨:这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的何止是一个家庭的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抗战史。耳畔仿佛响起佟麟阁将军在南苑军事会议上的誓言:“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以死报国。”作为全面抗战爆发后首位殉国的高级将领,佟麟阁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88年过去了,卢沟桥的石狮依然昂首屹立,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不屈的历史。而一位百岁老人对父亲的永恒思念,则让我们明白:有些记忆,不会随岁月流逝;有些精神,将在传承中永生。(顾艳龙)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