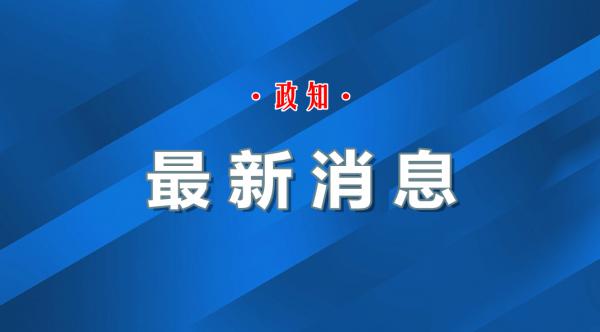近日,在第二届青岛里院喜剧节上,中国现存最早、尚可放映的电影《劳工之爱情》在青岛中国电影院与观众见面。这部拍摄于1922年的默片虽然时长只有23分钟,而且情节简单,但它从中国戏曲中提炼出幽默的智慧,展示出有别于同时代西方喜剧的独特质感。上海小人物的欢喜姻缘跨越百年时光,仍能让观众频频发笑,也让后来的创作者看到了前辈的探索。
青岛中国电影院是青岛首家由中国人创办的电影院,其创办人正是《劳工之爱情》的导演张石川。电影放映后在这里举办的第二届青岛里院喜剧节首场“里院共话”,围绕“笑看中国喜剧百年”的主题展开。陈佩斯、宁浩、黄渤等导演、演员及电影研究者,从百年前的默片出发,回望过去,也分享对当下喜剧创作的思考。
原来我们前面是有里程碑的
主持人:首先请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副研究员靳丽娜介绍一下,为什么要修复《劳工之爱情》这部电影,以及修复的难度有多大?
靳丽娜:这部影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故事片,拍摄于1922年,与它同时期拍摄的影片都没能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电影资料馆3万多部馆藏影片中,《劳工之爱情》可算得“镇馆之宝”。
胶片放得时间久了,有划痕、霉斑和变色等问题,因此中国电影资料馆在2021年启动了对《劳工之爱情》的修复,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部片子长23分钟、约有3万帧画面,我们首先用精密的扫描仪对它进行4K高清扫描,之后再逐帧修复。即便现在有AI技术辅助,但是它对于人工修复的技术要求依然挺高的。
主持人:这部电影的画面左右两边会出现字幕,是修复时配上去的吗?
靳丽娜:片中左右两边的文字叫间幕文字,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字幕,咱们常见的字幕是在影片下面。间幕文字在默片时代是比较常见的手段,作用是引导观众理解剧情,是当时就做上去的,并不是我们修复时加上去的。
主持人:从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到今天,中国喜剧的形式和内容在一百年间发生的变化大吗?
陈佩斯:大,也不大。我们的喜剧确实向前走了很多步,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某个时间段,我们的喜剧几乎是停滞的,重新起步很困难,能够借鉴的东西很少。改革开放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外国的作品,也想自己进行创作,《劳工之爱情》这样的胶片电影告诉我们,前辈人是怎么做喜剧的。
这个喜剧和同时代的欧洲喜剧、美国喜剧是有不同点的。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两位艺术家的电影以动作见长,比如表现在灾难性事件面前的动作——在山上躲石头,被汽车撞、火车轧,在火车、汽车上打斗,都是基于高难度的动作来生发喜剧,和杂技直接相关。
而《劳工之爱情》脱胎于中国戏曲,是戏曲人利用现代电影工业开始的新创作。从《劳工之爱情》中能看出中国早期电影里的演员受戏曲影响之深,甚至很多本身就是戏曲演员,他们常年在舞台上工作,所以经常带有亮相的姿态,表演老忘不了面向观众(在电影里就是镜头所在的位置)。
它从头到尾用了很多错位的方法,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计谋喜剧已经贯彻其中了:为了克服自己因为没有钱恋爱不成的困难,男主角郑木匠心生一计,用计谋和自己的木工手艺去伤害那些白天不干活晚上不睡觉的有钱人、赌徒。“有限度的伤害”造成一系列肢体动作喜剧,它承袭了我国古典喜剧里计谋喜剧的套路。
我和朱时茂在春晚上做小品的时候,没看过《劳工之爱情》这部片子,不懂有计谋喜剧这个喜剧方法。我们慢慢摸索出了很多方法来执行喜剧任务,也就是创造笑声的任务,这个特别难。所以当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像看到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前面是有里程碑的,这是一件特别让人欣慰的事。这条路有前人走,有今天的人走,一步步地走,我们是有传承的。
宁浩:我觉得《劳工之爱情》具备了很多种喜剧手法的基础,我在想男主角为什么是个木匠,干的却是卖水果的营生?这个人物设定是错位的喜剧手法,在今天也是常用的方式。
小人物的错位
让喜剧一碰就响
主持人:陈佩斯老师导演、黄渤老师主演的《戏台》,可算今年一部现象级的喜剧电影,这部作品产生喜感的“原理”是什么,它是靠什么使人发笑的?
黄渤:我觉得《戏台》也有一个经典的错位结构,就是一个大帅和一个送货伙计的偶遇。这个错位达成以后,整个喜剧一碰就响。佩斯老师这一代喜剧人,改革开放后从紧绷的状态中重新打开想象力,克服某些思维惯性是最难的。
宁浩:其实喜剧适合很多人一起看,我是一个人看的《戏台》,感觉挺凄凉的。我刚开始是带着点儿距离看的,但看着看着就投入进去了,开始乐,看到后面隐约感觉走向不完全是喜剧了,我就哭了。我又跳出来看自己,我怎么哭了?我觉得喜剧最大的力量就是喜剧人的人生感受,对我的冲击力很大。
倪萍:100年前张石川导演拍了《劳工之爱情》,又在青岛建了青岛中国电影院,今天我们坐在这家电影院里谈“中国喜剧的100年”。100年中中国发生了无数质的变化,而喜剧一直聚焦在“人”上。比如黄渤的喜剧表演,观众觉得他有扎实的人物基础,他的喜剧很高级。
我喜欢喜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被那种很“扎心的欢乐”吸引。喜剧角色往往都是小人物,生活中谁没有他们那样的苦?把小人物的苦表达出来,把那种在苦中寻找幸福快乐的能力和状态表达出来,我是很佩服的。
沿着前人的路
走出自己的路
主持人:在过往众多优秀的喜剧人和喜剧作品中,哪些艺术家和作品对各位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又是怎样启发过各位的创作?
陈佩斯:最早影响我的喜剧大师还是卓别林先生。我那时候唯一能看到的喜剧就是他的电影,包括他早期的无声片和后来的有声片。后来还有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一些喜剧电影。
1979年上映的《瞧这一家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喜剧电影,但现在看来,它只是沾了点儿喜剧的边。因为故事的整体结构并不符合喜剧的规制,它表现的内容是改革开放后人们怎么加班加点地工作、怎么追求技术革新,主旨上还是教育人的电影,但是有些人物的特色产生了笑料。
黄渤:佩斯老师之前的小品、电影,很多人都会翻出来反复看,作品对人物把控之准,真是了不得,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另外,现在没有人能光着脊梁上晚会了吧?
宁浩:我小时候住的大院里有电影院,可以经常看电影。印象很深的是我有一次看完陈强和陈佩斯老师主演的《父子老爷车》,走出电影院被一群小流氓拦住了。他们问我看了吗?我说看了。他们说你给我们讲一遍,因为他们没钱进电影院看。我就给他们讲。那时候我讲不好故事是要挨揍的,现在的观众对我好多了。
黄渤:导演的本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贾冰:我对喜剧的理解受到过两次重要的影响。第一次是在16岁看到佩斯老师的小品,然后就反复看,反复琢磨。2005年我退伍回到地方工作,参加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那时候觉得小品还可以像佩斯老师那样演,就沿着他的路走。第二次重大的影响是看了沈腾主演的电影,我就想放弃当时比较稳定的工作专职去当演员。之后徐峥导演找我拍了《囧妈》,从此我就爱上了电影。这不是我情感多变,因为无论形式上是小品还是影视,万变不离喜剧的根本。
我退伍以后在杭州工作了14年,从事喜剧创作和表演,从江浙沪一代的滑稽戏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学习了很多滑稽戏的技巧。我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尝试的一种表演形式,是把人物心里的潜台词说出来,还挺受观众喜欢,但这种表演形式不能时间过长分量过重,否则会使观众感到“腻”。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深深地爱着家乡的喜剧,但如果要把喜剧表演长久地做下去,还是要汲取更多方面的营养。
在这个时代
留下我们创造的文化记号
主持人:青岛的观众可能会更有兴趣知道,宁浩导演为什么会在《疯狂的石头》里起用黄渤老师,并且让他说青岛话?
宁浩:在与黄渤合作之前,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见过他两次,走路雄赳赳气昂昂的,但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学生。在电视剧《生存之民工》里他饰演一个小角色薛六,有一个小段儿我觉得演得特别好,而且还不是喜剧,是一段挺煽情的戏。然后我就请他来《疯狂的石头》剧组聊天,我印象很深,他当时特别疑惑地看着我们剧组的工作状况,一直在判断我们是不是个靠谱的剧组。
黄渤:因为《疯狂的石头》剧组的工作人员太年轻了,平均年龄不到30岁。
宁浩:黄渤在《疯狂的石头》里讲青岛话,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讲家乡话能给他带来松弛的状态,随之产生的表演是最好的。
主持人:里院喜剧节的诞生和青岛有着很强的关联性,黄渤、黄晓明、黄子韬、范丞丞四位发起人都是青岛籍演员。而且青岛人似乎格外有幽默的天分,是怎样的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这种喜感?
黄渤:我们青岛人可能也没意识到自己特别有喜感,是其他地方的人总结出来的。青岛本身有码头文化,有“江湖”的色彩,有放松的气息,这些会慢慢沁入老百姓的生活。这种气氛很多海滨城市也都有。
主持人:第二届里院喜剧节和第一届相比有什么变化?是否做了更多形式方面的尝试?
黄渤:这一届我们延续“一街好戏”的核心主题,设置了特邀演出、喜剧嘉年华、特别活动、音乐派对四个单元。汇集德云社、开心麻花、单立人喜剧等20余家厂牌,上演《乌龙山伯爵》《两个人的谋杀》等40余个剧目,包含脱口秀、即兴喜剧、音乐喜剧等表演形式。加上街头巷尾的800多场“盲盒”喜剧表演,意味着喜剧节的观众在为期十天的节日里,能够密集看到各式各样的演出。
去年第一届里院喜剧节举办后,也让众多喜剧厂牌与优秀喜剧人产生参与的兴趣。今年喜剧节邀请到的作品除了有传统舞台上的喜剧,还有街头巷尾上演的各种形式的喜剧表演,这是和第一届最不同的地方。里院喜剧节的嘉年华主场地,设置在青岛老城区的百年特色建筑群之间。我们想回到喜剧最初的样子,让演员和观众发生近距离的交流。其实表演不一定非要在封闭的剧场里发生,在院落之间、在街头巷尾,都可以有喜剧上演。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故意不让观众事先知道表演的是什么节目,以“盲盒表演秀”的方式给观众惊喜。
主持人:在邀请作品时,满足大众口味和艺术探索这两方面如何平衡?
黄渤:举办戏剧节展是一件工作量很大又细碎繁琐的事,同时也受到很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我们也在逐渐摸索和积累中。今年观众数量较去年增加了不少,需求的层次也更加丰富了。我们拓展了作品的类型,希望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让质量好的、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有艺术探索性的等各种类型的喜剧都能参与进来。
喜剧节的成长一定是与老百姓的接受和喜爱分不开的,我们希望把经验总结下来,把这个喜剧节办得越来越有自己的特点,越来越接近观众的需求。
主持人:现在各个城市的戏剧节展非常多,如何避免艺术活动的千篇一律,让里院喜剧节更具特色,并且能和这座城市的文化属性紧密结合起来?
黄渤:任何精彩的作品首先得有承载它的盘子,青岛这个盘子太好了,历史、建筑、文化等方面都有独特而多元的美感,再加上后来它又被赋予“帆船之都”“电影之都”等身份符号。100年前的电影人为青岛做出了这样的美学贡献,我作为电影人也好、喜剧人也好,同时又是一个青岛人,希望在这个时代给青岛留下一些我们自己创造的文化记号,也希望青岛成为一个展演的码头,停泊的都是喜剧大船。
供图/里院喜剧节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