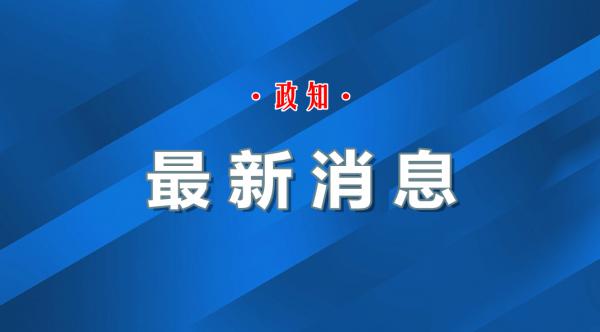在唐代,有一条特殊的“捷径”——它不是官道,却通往官场;它名曰隐居,却通向繁华。这条捷径,就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中南山,简称南山,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山脉中段。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内涵,古代隐居于终南山的人众多,比如东方先贤老子、药王孙思邈、汉初三杰之一张良这样的真隐士,他们或是不愿与官场之人同流合污,或是官场失利后追求宁静淡泊的生活。
在古代,一个人要是下定决心做隐士,别人便觉得他淡泊名利,是个道德高尚的人。然而还有一群人,他们隐居的原因比较特殊——想凭借隐居之举抬高自身声望、提升身价,以此来谋求官职。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在唐代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正是所谓的“终南捷径”。
唐武则天年间,有个叫卢藏用的人,他颇有些才气,善于写文章,然而考中进士后却未能得到调任官职。为此,卢藏用费尽心思,最终想出一个办法——做隐士。
于是,卢藏用跑到终南山隐居起来,表面看似是一位隐士,实际上却想方设法散布消息,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存在。有意思的是,皇帝在长安办公,他就住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跟着跑到嵩山隐居。于是卢藏用后来获得了一个“随驾隐士”的外号。
就这样,卢藏用苦心孤诣地在山中混了好些年。不过这种做法还真的起到了作用——后来朝廷发下命令,任命他为左拾遗。
当时与卢藏用一起被授予官职的,还有一位叫作司马承祯的隐士。武则天听说司马承祯的修行非常好,而且又饱读诗书,因此也下诏邀请他到朝廷做官。可司马承祯是一位真的隐士,他只在长安住了几天,便要求回终南山继续隐居。武则天见挽留无用,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
司马承祯离开长安的时候,许多官员都前来送行,卢藏用也在其中。卢藏用看了看司马承祯,用手指着终南山的方向,意味深长地说:“那里另有妙处啊!”
司马承祯听了,微微一笑,说:“在我看来, 终南山却是一条做官的近路啊。”一句话说得卢藏用非常尴尬,无地自容地走开了。
从此,“终南捷径”成为追求名利最近便路线的代名词。
但嘲笑归嘲笑,后来效仿卢藏用走这条“捷径”的人却越来越多——李白便是其中之一。
李白30多岁时来到长安,却没有直接进入京城,而是隐居在距离长安城不远的终南山。期间,他为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写下“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并数次到位于楼观的延生观(玉真公主修道别馆),拜见玉真公主。
当时李白有没有见到玉真公主,历来说法不一,但无论他是否见到,可以肯定的是,《玉真仙人词》最终确实被呈送到了玉真公主面前。
虽然李白初次尝试并未立即成功,但他的隐居却没有白费。后来玉真公主也确实在皇帝面前举荐了李白,使他得有机会入朝为官。
和李白一样,王维第一次隐居终南山时,年仅十六七岁,也带着类似的功利心——他在山中创作诗歌、结交名士,就是希望通过“隐居”的标签扩大知名度,为日后入仕铺路。
王维比较幸运,玉真公主极为赏识他的才华,便向主考官极力推荐,最终使王维年纪轻轻就踏上仕途,并名扬四海。
可见对很多文人而言,终南山的“隐居”更像是一场“自我营销”,本着“以隐求仕”的需求,让终南山成为仕途规划中的重要“跳板”。
可是每个人涉足的道路不同,抵达终点的难度当然也就不一样。孟浩然同样也想通过“捷径”来实现目标,然而虽得到张九龄举荐,但未见效果,再加上后来科考落第,最终落得个终身未能入仕的遗憾。
总之,这种通过隐居以求官的做法,之所以在唐代成为风尚,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一方面,社会推崇隐士的高洁;另一方面,文人又普遍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终南山”恰好成为连接这两种价值观的桥梁。
因此,这座距离长安仅数十里的山脉,不仅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更成了一条通往官场的“特殊道路”。它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梦想与失落,也孕育了“终南捷径”这个充满智慧的成语。
文/马庆民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