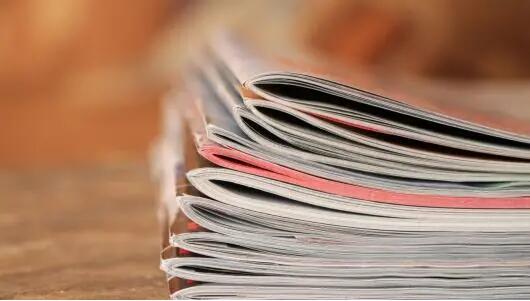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有一位专注于北京石刻艺术研究与公众教育,被称为“北京最美志愿者”的副研究馆员。她热爱古都文化,常挎着相机行走于四九城,最近,她将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了一本名叫《北京城好石碑》的书。她的名字叫闫霞。
出地铁国家图书馆站,沿着长河向东走,两岸杨柳依依,远远看到掩映在树丛中的五座小塔,就是著名的五塔寺金刚宝座塔,那里也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所在地。闫霞见人必笑,远远地从金刚宝座塔深处走来,笑容无遮无拦,周身仿佛都包裹着天真烂漫的特质,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接近。
石碑是汉文化圈流行的一种独特文化载体,其上的文字或图案被称为“凝固的墨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北京城好石碑》被称为“北京城的立体史书”,闫霞在书中系统梳理了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30余通石碑,并通过碑刻细节展现石刻之美和历史兴衰。
作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研究者,闫霞长期致力于石刻保护与公众教育,她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在著作中,还通过拓片技艺进校园等活动推动着文化传播。此外,她是博物馆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带出了一支高水准的讲解员队伍;作为博物馆金石大讲堂的主持者,她从零起步,用八年时间,组织了上百期讲座,不仅使金石大讲堂名声在外,还让京城的石刻艺术得以广泛传播。
从一块牌匾钩沉出
清初名将孙思克和末代帝师陈宝琛的故事
一张记录表和一把长尺,是闫霞研究石碑的标配工具。她说,不能迷信任何人,自己亲手量出来的才最安心。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2015年12月31日开馆,如今恰好十个年头,闫霞算是那里的老职工。当时开馆不久,很多事都是从零起步,那时馆里学习气氛特别浓厚,抄碑刻等等基本功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会,她主要负责拍照、整理基础资料,“因为我们要给馆藏文物拍图录。可是我两次都把碑拍反了,一拍错就被领导吼,结果发现原来碑本来就立反了,大家又给转过来。”
闫霞很刻苦,自己买了两套《清史稿》,单位、家里各放一套,为的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学习。她每天很早到馆,“馆里一开门我就过来晃悠一圈,经常和打扫的保洁阿姨脸碰脸。”没想到这样的晃悠还有奇遇,有一年冬至那天,早上8点45分,闫霞又到展室里,偶然发现一道阳光从地板上反射到屋子中间一尊东汉石像的脸上,很快,在8点52分左右的时候,晨光全射进来,石像一瞬间变成了通体金色。闫霞赶紧叫大家来看,但是阳光已经转瞬即逝。后来闫霞观察到每年冬至时分都有这样的惊喜,此后每到这天大家都来守候拍金身汉像。
闫霞对五塔寺石刻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上有多少尊佛像,她数过;每一张佛像的面容,她都描画过;塔基上的流云、花饰,她也都如数家珍。而对馆内的明清石刻,她更是倾注了无数心血。比如金刚宝座塔东侧的祠墓石刻展区内,有墓碑、祠堂碑、记事碑等20多通石碑,其中一通宽约2米的石牌匾与众不同。这块牌匾的石材是上等的青白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匾芯内有“兴记”二字,字迹端庄遒劲。这块牌匾是竖着立起来的,其落款下镌两印,上阴文篆书“臣陈宝琛”,下阳书篆书“太保之章”,四框镌刻缠枝葫芦花纹,竟然是末代帝师陈宝琛题写的。
匾额是京城文化底蕴的一部分,老北京的买卖,往往会请名人题写匾额。那么,这块“兴记”牌匾出自哪家店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沿着这个思路,闫霞最终从这块牌匾钩沉出了清初名将孙思克和末代帝师陈宝琛因缘际会的故事。
这块“兴记”牌匾原是孙思克的诰封碑。诰封碑是皇帝封赠官员的诏令刻石。孙思克为清初名将,战功赫赫,参与清军入关后诸多战斗,驻守甘肃37年,获康熙帝赞誉,因此获封追赠。孙思克诰封碑因晚清动荡受损。“兴记”是东四钟表店的字号。闫霞推测,估计是当时钟表店要求时间紧迫,工匠一时石料难寻,所以将孙思克诰封碑去掉碑首和碑座,并将碑阴磨掉一层,刻写了陈宝琛的题字,改成匾额。
“现在仔细看,碑身还能看出切割打磨的痕迹。”对此闫霞也不由得感叹:“石碑是历史的见证,它常因墓主的身份和事迹而诞生,又常因碑文的撰写者和题写人而传之久远。这通石碑,碑阳记录了孙思克在平定‘三藩之乱’、征讨准噶尔中立下的战功,碑阴则是末代帝师陈宝琛题写的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匾额。斗转星移,三百年之后,孙思克与陈宝琛意想不到地发生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际遇。”
藏在角落里的“小调皮”
证明了历史并非总是板着脸
闫霞告诉我,石刻馆里到处是宝贝,越仔细看,越有意思。比如勒保夫妇诰封碑和勒保赐谥碑,在遵守礼制的同时,在细节上也有创新之处。
在诰封碑底座左下角,一只灵猴扛着挂满寿桃的桃枝,憨态可掬,仿佛正欲献寿。右下角则是一只蜥蜴,口吐缭绕仙气,长长的仙气线条流畅飘逸,非常俏皮的一笔,灵动异常。闫霞说自己最在意碑上这些易被人忽略的细节。
在旁边的赐谥碑上,左下角的一只石猴抱首蹲坐。仔细看,可以看出它的神情戚戚,似有悲思;碑座右侧精心雕琢了三只姿态各异的小羊,或依偎,或张望,神情温驯可爱。
闫霞觉得,在森严规整的皇家碑制里,这些小生灵的出现击碎了官样文章的刻板面孔。它们不问王朝功烈,只载生活情味,或献寿纳祥,或感时伤逝,或稚子承欢,工匠的每一笔凿痕,都带着体温刻进了冰冷的庙堂。
“其实这些细节是清代官式碑刻中非常珍贵且罕见的‘破格’之作。”闫霞说:“它们证明了即使是在等级森严、规制严谨的御赐碑刻上,工匠依然拥有表达个人技艺与情感的空间。这些小动物,尤其是那只吐仙气的蜥蜴和形态各异的石猴、石羊,绝非随意雕刻,而是匠人有意为之的点睛之笔,寄托着祈福、哀思等世俗情感,让石碑从单纯的纪功述德之物,变成了有温度、有故事的艺术品。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小调皮’,让我们看到,古人也在体现一种轻松和幽默,它们证明了历史并非总是板着脸的。”
勒保家族墓原在朝阳英家坟,1954年部分石刻迁至圆明园暂存。1985年,这两通记录着功业与匠心的石碑落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正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特别是像闫霞这样的研究者持续不断的细致工作,才让这些尘封的“石上精灵”重见天日,焕发新生。如今,勒宝碑因其隐秘而活泼的细节,成了馆内当之无愧 的“顶 流”。游客们在此驻足、凝视、探寻、留影,石上生灵的巧思与诙谐,在闫霞等研究者的解读下,不再仅仅是冰冷的 石 头,而 承载着古人的技艺、情 感 与 生活智慧。
在田义墓地宫里享受片刻清凉
闫霞也常去石景山的模式口古街,那里的田义墓,是如今的石景山区石刻博物馆。
田义墓建成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神道区、享堂区、寿域区三部分组成。一条神道自南向北贯穿整个墓区,两侧排列着石像生,其中一文一武两尊石翁仲格外引人注目。文翁仲身着朝服,下摆的绶带和云鹤、花锦图案线条流畅,雕刻极为精美;武翁仲则头戴兜鍪(móu),身着铠甲,手持钢鞭,神态威严。
闫霞在研究中发现,田义墓武翁仲腰间革带上雕刻的是狮蛮纹纹饰,这在北京地区极为罕见,可能仅此一处,弥足珍贵。“这组纹饰以浅浮雕手法表现胡人戏狮的场景,共有七幅图案,包括胡人献宝、胡人戏狮、胡人牵狮等。每幅都独具特色,人物和狮子的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明代石刻艺术的高超水平。”
墓中棂星门以北的三座碑亭也是闫霞推荐的地方。“中庭内立着赐玉南京司礼监太监田义为南京守备的圣旨碑文;西侧碑亭立着赐太监田义押发罪藩碑;东侧碑亭则立着太监田义祭玉碑。这些碑文的篆额者沈鲤是明代著名政治家、理学家,撰文者沈一贯是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书丹者潘士元虽名气稍逊,但想必也是当时的书法名家。”在闫霞看来,这块碑文内容详实,记载了田义生前的功绩与地位,为后人了解明代宦官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田义墓的地宫是北京少有的对外开放的地宫之一,与定陵、裕陵地宫齐名。闫霞常来这里拍摄碑上的石刻、翁仲后的胡人驯狮图以及太监墓券子上的精美雕刻。天气炎热时,她会在地宫里吃些简单的面包、酸奶,享受片刻清凉。有一次,偶然有观众进来,他们彼此都吓了一跳。闫霞说:“那时的田义墓条件有限,夏天甚至会将干尸抱进地宫里保存,暴雨前又得将干尸抱回展厅。如今,田义墓经过修缮,成为石景山石刻博物馆,条件改善了许多。”
从钟鼓楼御碑到金石大讲堂
在北京中轴线的北端,钟鼓楼巍然矗立,被称为“龙尾之曜”。乾隆十年,钟楼迎来了为期两年的重建,御碑就此立起。这一方石碑,两面镌刻了两篇不同时期的碑文,分别讲述着两段历史,碑阳为乾隆帝亲书《御制重建钟楼碑记》,碑阴则镌刻着民国十四年京兆尹薛笃弼所撰《京兆通俗教育馆记》。闫霞对这通重建碑也有过深入研究,奉敕敬书碑阳的尚书梁诗正、开启民智的京兆尹薛笃弼,她都做了细致的考证和书写。令人没想到的是,她还因研究得到了刻碑者后人的关注。
闫霞说,琉璃厂赫赫有名的碑刻世家——陈家,就是这方御碑的制作者。“陈家祖父陈云亭在琉璃厂开设的‘陈云亭携碑处’,是当年京城碑刻界一块响亮的招牌,这方碑碑阴上字字端方、力透石背的《京兆通俗教育馆记》,就是出自他手。”
闫霞的研究成果不时见诸报端,陈家后代陈光铭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她研究钟鼓楼的文章后找到了她。闫霞记得,当时特意打车接来不谙使用微信的陈光铭。清茶氤氲中,老人封存数十年的记忆奔涌而出。他讲述祖父陈云亭如何“审石度势”,如何运腕下刀。闫霞说:“如果将碑放倒平刻,干起活来顺手省力,但在搬运过程中,很容易在碑上留下划痕。为了最大限度保护石碑原貌,陈云亭先生采用‘立刻’的手法完成了这项工程,每一个字的笔划都需要调动起全身的精气神。”
随着网络的发展,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逐渐火起来,每天接待大量游客。可是一般游客来,不外自拍、发朋友圈、吃特色冰棍加撸猫,任务完成就打道回府,闫霞觉得,游客对馆里的石碑和文物可能没有了解的愿望,但也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没能用到位的讲解留客”。为此馆里动过不少脑筋,在讲解上下功夫。闫霞回忆,最初,馆长要求全馆的人都得当讲解员,赶鸭子上架也得上。
后来,馆里又开展金石讲堂活动,闫霞是金石大讲堂的主力组织者。回忆起2015年第一次在金石大讲堂组织讲座,会场内听众稀疏,空旷得令人心慌。此后,闫霞工作之余也奔波于寻找学者、设计海报、组织听众等琐碎工作中,数年时间里组织了上百期讲座。闫霞的坚持感召了同道者,一个稳定而温暖的团队也渐渐凝聚起来,严谨的分工与流程使讲堂迈入了标准化运作轨道,并最终成为博物馆闪亮的品牌项目。
如今金石大讲堂每逢讲座日,馆内常常出现提前用物品在听众席前排座位占座,来宾则在馆内碑刻林中流连忘返的场景。除了提前占座,走进金石大讲堂还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奇妙氛围:讲座尚未开始,观众已然聚合成群,彼此畅聊寻碑访古的趣闻逸事,传递分享着精心准备的书籍,甚至交换着彼此的美食推荐。课后,人们常簇拥着专家热烈探讨许久,还有多位曾默默听讲的观众成了讲堂团队中热心的志愿服务者。多年耕耘,闫霞也已从任务执行者蜕变为文化品牌的塑造者。金石大讲堂声名远播,竟引得不少单位主动伸出橄榄枝,希望合作举办讲座。
对实习生倾囊相授
“老也不高兴”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静谧的院落里,历史深埋于碑林之间。闫霞的身边,常静静倚放着附近高校实习生的书包。
多年文物研究的积淀,让闫霞主动接纳并精心培养了不少实习生。他们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她的引领下,学生们以开拓性的思维,将现代科技与传统研究相结合,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比如运用三维建模技术对文物进行精准数字化记录,借助专业扫描软件优化文物摄影效果,通过iPad绘制精细的文物线描图,运用录音转文字技术高效整理复杂的碑文内容。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遗产专业的曹卜予和徐蔚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藏珍宝中,有十对姿态各异的狮子石刻,寓意十全十美。《重修三晋庙碑》碑座两侧的披发狮子尤为特别,其体型雄壮,四肢短粗,长发披肩,尾巴盘绕于脚下,一双枣核眼配着枯瘦愁容,这狮子以这副仿佛千言万语锁在喉间的尊颜,被大家戏称为“老也不高兴”。为了将这通高3.27米、青白石质的螭首方碑上777字的碑文准确抄录,闫霞特意选择了两个阳光充沛的午间,带着曹卜予和徐蔚晴临摹。她们或蹲或跪,小心翼翼地辨识每一处风化或模糊的笔画,然后一笔一画地誊写在纸上。
闫霞说:“这通碑文的撰写者曹学闵是乾隆朝进士,祖籍山西汾阳,曾力主重修马神庙并易名三晋庙。而书丹者冯廷丞的经历则与清代文字狱的严酷紧密相连。身为山西代县举人出身的官员,冯廷丞因牵涉‘字贯案’被革职。他时任江西按察使,仅因审阅过此书而未指出‘悖逆’便获罪。此案牵连近百人。”
在指导曹卜予和徐蔚晴的过程中,闫霞不仅倾囊相授碑文整理、文物信息记录、拓片技艺等基本功,更鼓励她们走出办公室,参与公众讲解与志愿服务。在这座石刻艺术殿堂的沃土中,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曹卜予和来自香港的徐蔚晴迅速成长,她们带着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汲取的学识和勇气,走进了中央财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思政课堂,以北京中轴线上的燕墩碑、钟楼重修碑为切入点发表了演讲。如今,曹卜予已正式入职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徐蔚晴则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保护专业继续深造。
目睹着曹卜予、徐蔚晴这样的学生从生涩走向熟练,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思维巧妙融合,闫霞倍感欣慰。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