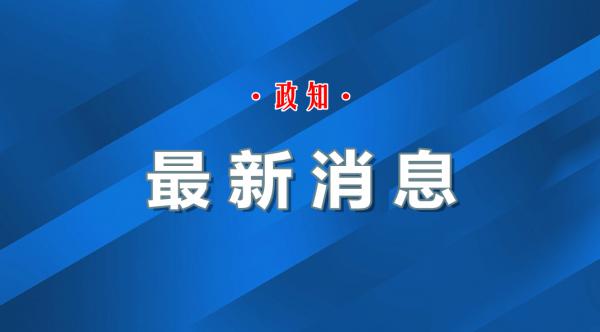悬疑化的怀旧与寓言化的历史
关于双雪涛小说中的悬疑与城市,和他同样在沈阳长大的青年作家淡豹做过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这个工业城市本身正是新时代的一桩悬案。”值得注意的是,像《走出格勒》中用“列宁格勒”命名的艳粉街煤厂一样,只有转义为一种超越其地方性的历史,“这个工业城市”作为“悬案”的意味才得以充分显现。沈阳是社会主义普遍历史的寓言。在《平原上的摩西》中,刑侦悬案的发生地艳粉街无法直接实现这种转义,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转换枢纽是作为悬疑化怀旧空间的广场与“平原”。
1995年之前,小说的主人公李、庄两家人共同居住在红旗广场旁的社区里,而在两家分离后,李守廉和庄德增唯一一次相遇,正发生在红旗广场改造的情境中:广场中央的毛主席塑像被拆移,代之以太阳鸟雕像。这是《平原上的摩西》的沈阳图绘的又一例空间叠合。“红旗广场”是沈阳中山广场1969年至1981年的曾用名,也是今天这座城市的老居民对该地点的习惯性称呼,在这一名称诞生的同一年,广场中央建成了大型主题雕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泽东全身塑像高高耸立在基座之上,基座四周是表现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革命史的工农兵群塑。这组雕塑在2007年被列为辽宁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未曾有过整体性的拆除或移动。而小说中替代毛主席塑像的太阳鸟雕像,实际上是沈阳的另一个广场——市府广场上的雕塑,其原型是 1978 年在沈阳北郊的新乐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一个已经碳化的抽象木雕,据说是鸟形远古图腾,后被命名为“太阳鸟”,1998年,巨型太阳鸟雕像作为沈阳市的标志被安放在市府广场中央,2010年,市府广场修建地铁站,太阳鸟雕像被移至新乐遗址博物馆。《平原上的摩西》将上述两座广场及其景观的变与不变叠合在一起,充满想象和洞察地书写了两种城市符号相互替换的当代史:“千禧年前后”,太阳鸟替代了毛主席像,2007年,后者又替代了前者。
关于太阳鸟替换毛主席像的情节,批评家黄平读解为历史观的变化,即“不再以‘阶级’而是以‘民族’理解历史”。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民族”与“阶级”在毛泽东时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范畴,“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共和国长子”与“工人阶级老大哥”、民族国家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支撑,共同建构起“阶级—民族”的身份认同。因此,新时期的历史叙事与其说是以“民族”取代“阶级”,不如说是以“乡土—民族”取代“阶级—民族”。以本地考古发现建构乡土或地方文化,始于80年代的“考古寻根”热,该热潮的核心是中华文明起源论述的范式转换——强调多地多源的“满天星斗”说取代了把黄河流域看作唯一“摇篮”的“大一统”说。在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市场化语境中,乡土文化建构成了“经济唱戏”的舞台,衰落的老工业基地借此招商引资,作为沈阳标志的太阳鸟雕像是为吸引外部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目光而自我乡土化的表征。而在当代沈阳人的内在经验中,所谓“乡土”记忆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记忆,新建的地方性景观反倒是古怪的外来物。因此,在《平原上的摩西》里,太阳鸟被老工人说成是“外国人设计的”,第一次城市符号替换的时刻,不仅老工人们聚集在红旗广场保卫毛主席塑像,已是民营企业家的庄德增也忍不住打车回到这里怀旧,他将广场上的毛主席塑像体认为“我故乡的一棵大树”。
这棵“故乡之树”无疑是各个阶层共同分享的记忆与认同的超级能指,无法胜任这一能指的太阳鸟最终被从广场移除,小说中的第二次城市符号替换——毛主席塑像的回归意味着基于超级能指的意识形态修复,即缝合因阶层分化而产生的表意断裂,在市场化语境中实现重构。但作为这种重构的基础,“故乡之树”从一开始便被小说置于悬疑叙事的张力中。在第一次城市符号替换的现场,庄德增望着即将拆移的毛主席塑像感怀往昔之际,他的怀旧突然被神秘的出租车司机的莫名提问打断:“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使怀旧主体陷入悬疑的他者话语来自庄德增未能认出的昔日邻居李守廉,他问的是毛主席塑像底下的工农兵塑像的个数,间离于资产者对超级能指的注目,这位下岗工人向基座的群塑移情。小说以这种记忆焦点的分化凸显出90年代形成的“锈带”底层的情感结构:一方面,这一底层对“主席”怀有最深挚的乡愁;另一方面,该乡愁蕴含的复杂历史经验无法通过常识化的怀旧表象显影。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论,情感结构伴随阶级的分化而分化,个中张力“要在那完全崭新的语义形象中体现出来或被表达出来”。
在去红旗广场的出租车上,李守廉的悬疑形象是一张盛夏中午戴口罩的脸,口罩是人物的面具,也是其创伤的外显,在小说以断片拼接的方式还原“蒙面人”身份时,对基座群塑的移情叙事,成了与面具相对应的历史创伤的标记:
父亲摘下口罩,把买好的菜拿进厨房。吃饭时,父亲说,广场那个太阳鸟拆了。我说,哦,要盖什么?父亲说,看不出来,看不出形状,谁也没看出来。后来发现,不是别的,是要把原先那个主席像搬回来,当年拉倒之后,没坏,一直留着,现在要给弄回来。只是底下那些战士,当年碎了,现在要重塑。不知道个数还是不是和过去一样。
小说中的破碎群塑是在沈阳红旗广场雕塑的真实历史印痕基础上的虚构。这组雕塑不仅是叙述中国革命史的文本,也是关于文本的文本,毛主席塑像基座四周,众多工农兵塑像姿态各异地手持一本本题名清晰的经典革命著作,但也有不少人物塑像显豁地举手空捏,其手中的“红宝书”作为异质历史的标记在新时期被清理凿除。意识形态文本的历史凿痕被《平原上的摩西》身体化了,与李守廉叙述的破碎群塑同构,小说中的各种底层身体的伤残——李守廉自己被击穿的左腮,其女李斐截瘫的下肢,以及他所关注的小贩女儿被烫伤的脸,无不是具体历史过程的留痕。从超级能指向基座塑像的移情因此是反询唤的质询形式:在社会变迁中断裂的意识形态可以缝合并重塑,铭刻历史创伤的普通生命也能随之修复吗?
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历史创伤是老工业区悬疑叙事的缘起,但双雪涛的小说却并非抚摩旧创而悲情徒叹的新伤痕文学,悬疑叙事既是质询历史的形式,也是基于历史对未来可能性的富于张力的探究。在《平原上的摩西》的结尾,庄树和李斐在北陵公园的人工湖上重逢,故事和历史的僵局成了小说的终极悬疑,而小说的标题则在此时展现为面对历史的创伤性僵局的主体姿态:庄树用“把这里变成平原”的承诺来回应李斐引述的《旧约·出埃及记》(Exodus)中摩西率族人过红海的典故。如果说“摩西”意味着打破僵局的创造性“出走”(Exodus),那么“平原”则是参照历史经验构想的愿景。庄树最初调查艳粉街悬案时,在蒋不凡的遗物中发现了一颗平原牌香烟的烟头,该品牌香烟的烟盒上印着十多年前傅东心为李斐画的像,这条线索并未对破案起到实际作用,却成了单纯的刑侦视野的一条裂缝,让年轻的刑警逐渐回想起自己童年时代的社区生活。小说收束于庄树视角的特写:再现“我们的平原”的烟盒漂在水面上,载着当年的李斐走向岸边。这一镌印记忆的特写寄寓着关于未来的愿望。而愿景的最初描绘和命名则是来自李斐自己的回忆:
很多年之前,傅老师在画烟盒,我跪在她身边看,冬天,炕烧得很热,我穿着一件父亲打的毛衣,没穿袜子。……画好草稿之后,我爬过去看,画里面是我,光着脚,穿着毛衣坐在炕上,不过不是呆坐着,而是向空中抛着“嘎拉哈”,三个“嘎拉哈”在半空散开,好像星星。我知道,这叫想象。傅老师说,叫什么名字呢,这烟盒?我看着自己,想不出来。傅老师说,有了,就叫平原。
“平原”图像及其绘制密切关联着一个具体的生活空间——东北平房民居中的火炕,紧接着这段主体动作丰富的炕上回忆,李斐想起了自己经历艳粉街罪案苏醒后的局促空间:失能的身体躺在一张床上,孙天博坐在床边曲里拐弯局促地摆着扑克。两段回忆的对照无疑有器物使用习俗上的依据:区别于私人意味明确、仅以睡卧为功能的床,炕在家庭睡眠时间之外,是社群人际交往的空间,从成人待客、聚饮到同学少年读书、游戏,皆可“上炕”进行。但是,炕并不能在地方民俗的意义上成为“平原”的原型,它在小说里的社群含义是高度语境化和历史化的。在回忆“平原”之前,李斐首先叙述的是搬家之后的炕:
……第一天搬进去,炕是凉的,父亲生起了炉子,结果一声巨响,把我从炕上掀了下来,脸摔破了。炕塌了一个大洞,是里面存了太久的沼气,被火一暖,拱了出来。有时放学回家,我坐在陌生的炕沿,想得最多的是小树的家……
陌生、冰凉、塌陷的炕 , 意味着有机性的生活世界的解体,在此前提下,小说中作为“平原”原型的炕与局促的床的对照不是空间性的,而是时间性的:李斐与庄树在有机社会环境中度过了共同的童年时代,她与孙天博则是从阶层分化的时刻开始一起走向成年,在前一个时代,拖拉机厂工人的女儿在哲学教授女儿的辅导下阅读《出埃及记》,自后一个时刻起,两个下岗工人的孩子一直身处逼仄的底层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平原”似乎就是分化区隔的语境中关于有机社会的怀旧意象。
然而,更为复杂的是,像有机社会的消逝一样,它的形成也是《平原上的摩西》叙述的一桩悬案,并且这桩更久远的旧案几乎从小说一开始就幽灵般地与“新时代的悬案”如影随行。小说以庄德增为第一位叙述者如是开篇:“1995年,我的关系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从1995年向前回溯,创业者的自述履历很快转向妻子的家世:傅东心的父亲是大学哲学教授,“文革”时身体被打残,三个子女“全都在工厂工作,没有一个继承家学,且都与工人阶级结合”。这同时是新时代成功人士对自己从中分化出来的旧社群历史的旁白。但在傅东心的叙述中,旁述历史的局外人成了历史罪案的参与者:一伙红卫兵在广场兵分两路,一路抄了傅东心的家,庄德增所在的另一路打死了他未来岳父的同事。1995年社区拆迁之际,傅东心向李守廉提起这桩旧案,在她的记忆中,他当年救了她父亲的命,李守廉却表示“不记得”这回事。在故事层面,李守廉的否认是对具体人物关系的回避或遗忘,而在对话性历史叙事的层面,“不记得”是一种阶级话语的失语,相对于以断片形式表达90年代经验,如何在工人立场上叙述曾以其为主体之名的有机社会的遗产和债务,是更加难解的悬疑。
作为工人的女儿和“平原”的回忆者,李斐没有直接提及她出生前的历史悬案,但在对自己童年经验的叙述中,却展现出与傅东心的旧案经验发生共鸣的对现实压抑的敏感。傅东心因为看到她喜欢“玩火”——对压抑的另类反抗而做了她的老师,“平原”图像中如星辰般抛在空中的三个“嘎拉哈”,正对应着她曾经抛向天空的烧成火球的火柴盒,以及她未竟的在艳粉街高粱地烧出一片圣诞树的愿望。作为愿景的“平原”的确来源于怀旧,但被缅怀的对象不是“呆坐”在炕上的过去的现状,而是在当时条件下进行有创造力的另类想象(另“抛”/“烧”出一片人生天地的想象)的空间。传统工人阶级有机社会的消逝瓦解了工人子弟畅想丰富的人生可能的现实条件,此时李斐像对“平原”一样念念不忘的是傅东心讲的最后一课——摩西的出埃及,一个从不可能中创造全新的可能性的故事,小说的两个主题意象由此相契。重新构想作为平等的人生想象基础的有机社会,是作为创造性主题的“平原上的摩西”的核心,而在前述由“新时代的悬案”与其旧案前史共同构成的悬疑叙事框架里,这一重构的前提是承担有机社会建构历史的全部遗产和债务,无论故事中的相关角色对此有无明晰意识,一旦年轻的“摩西”领受了重返应许之地——再造“平原”的使命,他/她便不可避免地肩起了历史的重负。
在上述意义上,《走出格勒》可以被看作《平原上的摩西》的主题意象的注解:“我”不知道“列宁格勒”实际所指的城市,也不理解曼德尔施塔姆的同名诗歌的含义,但“我”在煤厂里发现和背负的尸体却具有这一名称所象征的历史的全部重量。在双雪涛的这类以旧工厂为悬案现场的小说里,进行第一人称叙述的主人公往往不经意间扮演了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使”的角色:面朝与“进步”相反的方向,用废墟和遗骸代替“一连串事件”来表征历史。和这些同龄主人公/叙述者相比,《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李斐和庄树似乎不完全具备“历史天使”的特征,因为小说没有对凋敝厂区的直接描写,然而,也正是由于直观的工业废墟的缺席,作为老工业区历史再现方式的悬疑叙事,才更加卓著地显现为与废墟同构的寓言:“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
在当代文艺介入老工业区衰败史的最初时刻(以1999年王兵进入铁西区拍摄同名纪录片为标志),物质废墟的直接呈现便是从罹难者立场传达废墟化历史体验的寓言。但随着老工业区尤其是大型工业城市被整体纳入消费社会的空间生产,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后,间或浮现于光艳都市景观中的废墟表象,已被资本逻辑的霸权叙事重重编码。如《跷跷板》中废弃的旧工厂,表面上是因为怀旧而被保留下来的,实际上却掩藏着国企改革历史中的秘密,而既得利益者的临终解密则是意图再度掩埋遗骸的霸权的再符码化。物质废墟的表象因此不再是历史废墟的显影,而是对罹难者历史的屏蔽,只有通过悬置霸权符码的探寻和发现,真正的废墟体验才可能从废墟表象的屏蔽中释放出来。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悬疑叙事成了新锐的电影和文学作者书写老工业区的主要形式,作为悬案现场的旧工厂重新显出寓言的质感,但这种质感的来源已从直观的工业废墟置换为制造悬疑的经验和话语断片。
因此,《平原上的摩西》尽管没有直接写工厂,却使一座工业城市的乡愁空间——从广场到炕头——在非连续性的怀旧中成为一种普遍历史的寓言。小说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是抚今追昔的对话主体,几乎每一位对话者的回忆都存在不同意味的悬疑,其中最具元小说意味的是,李斐将自身记忆的建构自觉地称作“谜案”,她在经历艳粉街罪案后,一边阅读《摩西五经》等书籍,一边写着关于《平原上的摩西》的主人公们的小说。老工业区悬疑叙事由此自我指涉为工人子弟对失落的社群的象征化救赎——与废墟同构的寓言的辩证含义,同时也留下了更令人期待的悬念:作为对不同世代心怀应许之地的罹难者的承诺,一部21世纪的《出埃及记》是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