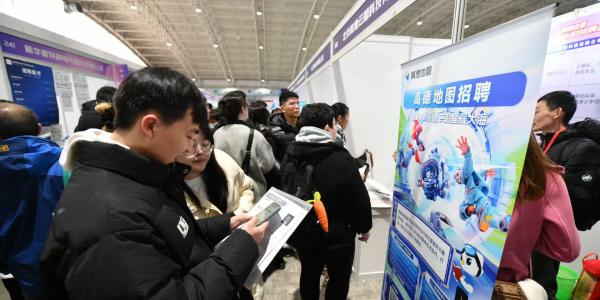5月25日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近年来,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成为了热门话题,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市安定医院了解到,儿科门诊每天接诊的患者中,有一半是因为出现了抑郁、焦虑、双向情感障碍等情绪问题。
面对患病,有的孩子和家长在筋疲力尽后选择了向疾病妥协,释然面对患病的事实,有的则选择了和抑郁症来场“硬碰硬”的“格斗”,考上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抗抑”的同时去帮助他人认识疾病。
安定医院的医生表示,有很多青少年患者因为治疗恢复社会功能,甚至数年不曾复发,其中许多人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着光,“患病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
十年间门诊接诊量从十几人变成近300人 住院孩子中有一半是抑郁症
在距离北京德胜门门楼百米外的冰窖口胡同里,一个从外边上看有些“老气”的院子,却有着全国最好的精神专科医院之一安定医院。
每天从早上6、7点钟开始,门诊二楼的数百张座椅,就被患者和家属占满。走廊上,也站了一排排人,时不时抬眼看看诊室或检查室门口的电子牌上显示的患者名字。大多数时候,门诊是嘈杂但不喧闹的,只是偶尔,会有几声年轻又尖锐的吵闹、带着哭泣的“我太难受了!”或者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哭喊从走廊最内侧的12诊室里传来。
这些声音的主人,很多都是十几岁甚至更小的少年儿童,而这样的孩子,北京安定医院儿科门诊每天要接诊300个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因为抑郁、焦虑、双向情感障碍等情绪问题前来就医的。
安定医院儿科副主任陈旭告诉北青报记者,她在儿科工作的这十多年里见证了太多,“现在的儿科是精神科中的‘热门’,可十多年前的儿科,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一天有十几个病人来就诊就算多的了。”
据2021年,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教授带领团队发布的《中国首个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调报告》结果显示: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抑郁障碍占3.0%。另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有21.4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抑郁风险,45.2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焦虑风险。青少年抑郁症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安定医院儿科不大的病区里,因抑郁症而住院治疗的孩子有三十几个。面对陌生人的到访,有的孩子会热情地主动上前打招呼,有的则将自己藏在朋友的身后,探出半个身体,对来访者投以好奇的目光。
儿科心理治疗师徐高阳告诉北青报记者,许多被收住院的孩子,是因为出现了自伤、自杀或者伤害他人这种极端的行为,“住院意味着孩子们将远离学校,这对于他们回归社会环境会是个考验。所以在收住院方面,我们很谨慎。”徐高阳说,虽然如此,但对于病情较重的孩子来说,住院对治疗更有帮助,“治疗的实施会更系统、稳定。就像心理治疗,对于抑郁症患儿帮助很大,但是在门诊,挂号都很难。相比之下,住院期间每周1到2次的心理治疗就显得尤为稳定。”
10岁时差点遭到侵犯不敢告诉他人 反复住三次院才找到患病关键
从外地到北京就医的小林在儿科病房的存在感并不高,14岁的她梳着乍一看上去和普通少女差不多的长发,但是在造型上,她又留下了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就像期待别人能够在人群中发现她的与众不同。
小林患的是抑郁症,患病的原因要追溯到她10岁时的一段经历。小林的家住在镇上,在一次和同学外出游玩后单独回家的路上,小林遇到了两个男人,“他们抢了我的钱,还撕了我的衣服,是一声狗吠救了我。”小林说,那时候的她还没意识到被撕衣服的严重性,所有的恐惧集中在担心妈妈知道她丢了200元压岁钱上。直至去年,进入青春期的小林在回看日记时才知道,3年多以前的她差点遭受到侵害。
“她在前年就已经出现抑郁的症状了,情绪低落、烦躁、乏力等,直到后来陆续出现捶墙等自伤行为。”心理治疗师侯威威说,小林在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前,曾在当地医院治疗,但效果不明显,“她的情况比较常见,因为童年创伤(留守、校园霸凌、情感忽视、性侵害等)导致现在出现了行为、情绪问题。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深,她甚至会刻意地去埋藏这段记忆。直至来北京看病,她才告诉我们、告诉家长曾经发生过什么。”
5月23日,小林接受了入院后的第三次心理治疗。“我觉得最近状态很好,没有犯病,0-10分的话可给自己打10分。你教我的深呼吸放松和蝴蝶拍都很有用。”当侯威威问起小林近况时,小林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
治疗的时候,侯威威曾让小林给这件事取一个中性的名字,以便让她慢慢地接受,不再恐惧,小林十分干脆的选择了“狗吠”两个字。对于小林来说,狗吠就像是她的救赎。侯威威说,他现在给小林做的EMDR(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治疗就像是在循序渐进的帮她解开这个“心结”,擦拭心头的“黑色斑块”。
在治疗过程中,小林虽然说不上活跃,但是配合度很高,整个治疗中没有使用过她和侯威威约定的“停止”手势,也没有用言语表达过不舒服,甚至在治疗时还和侯威威说起出院的话题。可是侯威威却在近1个小时的治疗中发现,小林似乎为了尽早出院而隐瞒了记忆力下降的事,“很多孩子会呈现给别人一种,她想让别人看到的状态,这其实是他们的自我保护。他们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我们都需要格外留心去观察才能知道。”侯威威说。
孩子患病三年 母亲自己也做了6、7次心理咨询 从难以相信到释然接受
患病前的小希是一个喜欢笑,喜欢闹,喜欢缠着爸爸妈妈要好看的裙子、首饰的女孩子,因为性格好、长相好,小希从小就备受他人喜爱。患病后的小希变得沉默寡言,精神萎靡,不再喜欢那些好看的衣服,甚至连踏出房门对小希来说都变得十分艰难。
“我现在想想,她的改变应该是从2016年,她10岁时开始的。”小希的妈妈张媛说起小希的病,不断叹着气,“刚开始的时候,她没有那么严重。”直到2020年,小希的学习成绩突然大幅度下降,还将自己关了起来,不想让别人找到。
在那之后,小希就开始拒绝社交,拒绝再去学校上学。张媛说,那时候她和丈夫只以为是小希学习成绩不理想,在闹脾气,“我还很生气,因为她不去学校,网课也听不进去,为此我说过她。”张媛说小希在变得越来越不对后,她终于意识到,孩子可能病了。
“她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但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憋在心里不和我们说的,我带她去做心理咨询,她也很难对咨询师敞开心扉。”小希的情况让张媛和丈夫变得焦虑,并且不太接受女儿患上了抑郁症这件事。
小希患病的这几年里,张媛几乎想尽了办法,“我们给她换过学校,不行。想带她去旅游散心,不去。像以前那样给她买新手机、买好看的衣服、首饰,她完全不感兴趣。每天连房门都很少走出去。”张媛说。
小希的情况久不见好转,张媛在陪小希的这段时间里,觉得自己也快抑郁了,“这两年多,我也见了6、7次心理咨询师,每次见完,能舒服一点。”张媛说,小希爸爸最开始知道小希可能患上抑郁症后,也很担心焦虑,“我们家最疼闺女的就是他,从小到大,要什么给什么,连重话都舍不得和女儿说那种,所以当知道女儿病了,他更难以接受。”但后来,小希的爸爸却成了家里最先释然的那一个,“我老公和我说,他身边很多朋友家孩子都有心理问题,甚至不少孩子比小希还重,天天闹自杀什么的,相比他们,小希的情况已经算好的了。”张媛说。
小希患病后,病情其实一直都在改变,她从最初完全抗拒和外界接触,到2022年,小希突然主动和心理咨询师提起了想上学的事,“她虽然现在也很不舒服,但是开始觉得不上学不行了,她主动和咨询师说,想找个可以接受她这样孩子的学校去读书。”张媛告诉北青报记者,小希现在在一所社区学校上学,“那里有一些和她情况很像的孩子,所以更包容她一点,”现在张媛的目标就是,哪怕小希每天能去学校上两节课,她就满足了,“无所谓她学到了什么,只是希望她能通过学校和外界建立起联系,不再‘社恐’。”
同样,小希的积极也影响着张媛对于抑郁症的看法,“我之前挺怕吃药会影响孩子的,她和我提出想去上学后,我觉得我也不能太畏首畏尾,谈‘抑’色变了。”张媛说,前阵子,小希已经开始服用医生开的药了,“复查的时候,医生觉得小希的变化很明显,这也让我看见了一些希望。”
曾因抗抑郁症漫画走红 与抑郁症“硬碰硬”考上北师大应用心理研究生
在寻找和自己和解方法的路上,22岁的姗姗决定和抑郁症来场“硬碰硬”的“格斗”。
姗姗是个北京姑娘,却有着江南女孩温润的性子。2019年10月,在外地上学的她,突然状态极差地在寝室床上躺了整整一周,“我当时就觉得生活没有希望,躺在床上莫名其妙地流眼泪。感觉不对后,我是自己去的医院,没敢告诉家人和朋友。”经过医院的检查,姗姗被学校所在地医院确诊为中度抑郁症、中度焦虑症。
拿到诊断书的时候,姗姗看着抑郁症几个字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就是情绪不好,我能自己调整,医生让我吃药我也是拒绝的。”直到寒假回京,姗姗因为抑郁症加重又进了医院,这一次,她被安定医院的医生确诊为重度抑郁。
姗姗病得很重,不得不休学进行治疗。在治病期间,她数次想要自杀,最终在朋友和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消了轻生的想法。2020年7月,姗姗在朋友的建议下开始用画笔记录起“对抗”抑郁症的历程,还因此在那段时间当了一阵子“网红”。
2021年,情况好转一些后,姗姗重新回到了学校,但她依旧“社恐”,笑容虽然时常挂在少女白皙的脸上,但和熟人说话时,姗姗偶尔也表现出局促不安。一次聊天,姗姗犹豫了很久,小心翼翼,用很小的声音对北青报记者说,“我想去学心理学,想考北师大应用心理的研究生,但是这好难啊。”
在备考的一年多里,姗姗就像与世隔绝了一样,“就像被传送到副本里那样,感觉外边的事和我都无关。”姗姗说,她也有“犯病”的时候,“一‘犯病’就很难集中注意力,但是那时候的我已经不害怕了,知道这就是病情在反复。”但姗姗也说,这种隔一阵子就会突然冒出来的“boss(首领怪)”给她的备考路增加了不少难度。
今年的4月末,姗姗终于结束了漫长的考研路,“姐姐,我考上北师大应用心理学的研究生了。”在确定被录取后,她很兴奋地给北青报记者发了一条又一条信息,“我是第一名。”“我终于成功了。”
时隔两年后再见到姗姗,北青报记者发现,她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整个人都变得更开朗有活力,说话也不再小心翼翼。姗姗告诉北青报记者,她的病虽然还没好,但是,“管它呢,反正我不怕它了,‘犯病’时候就吃药,大不了就难受一阵子嘛。”姗姗觉得,患病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因为生了这个病发现大家对抑郁症的认识真的太少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从设计改学心理学的原因,我想用我的方式结合我的亲身经历去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的人,也想用我的方法去让大众更了解这个疾病,不要再说‘抑郁就是矫情’这样的话了。”姗姗说。
大多数孩子生病初期都曾向家长求助 希望所有出院的孩子都能回归社会生活
陈旭告诉北青报记者,虽然现在人们在对抑郁症的认识上有所加强,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想,等到什么时候门诊首诊的孩子都刚刚出现抑郁状态或表现为轻症时,那样人们对青少年抑郁的认识就算达到一个合适的程度了。”
专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的徐高阳则说,很多孩子在刚出现抑郁状态时曾向家长发出求助,但未获得恰当的理解和回应,很多家长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求助是“矫情”或者是青春期的“叛逆”,“家长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孩子出现情绪波动肯定会第一时间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在家长面前表现出来。家长一定要在日常生活给予孩子积极的关注,学会共情和理解孩子的内在世界。”徐高阳说。
“当出现抑郁问题时,到医院寻求精神科诊疗或心理治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陈旭说,抑郁症和其他疾病一样,“解决问题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在治疗方面,不要有抵触心理,“并不是所有程度的抑郁都要吃药,但即便医生要求吃药,也不要抵触,举个例子,大家都能很轻易接受感冒、发烧需要吃药这件事,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是极为正常的治疗过程。”陈旭说,她经常会遇到家长提出,“担心吃药有依赖”“会不会越吃药越笨”“会不会引起肝功能损伤”“是不是需要终生服药”……之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陈旭说,“精神科用药非常谨慎,儿童青少年精神科更是如此,都是从小剂量逐步加到治疗剂量,在服药期间,还会定期检查孩子各项功能,并随时了解孩子服药感受和症状变化,所以十分安全。当孩子经历完整的治疗过程并且症状得到改善后,完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减药、停药。”
抑郁症在治疗上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徐高阳告诉北青报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患病的孩子离不开医生、家人、老师、朋友的共同努力、支持和陪伴,“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地把孩子调整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结果生活环境没有给予充足的支持,孩子的症状就可能出现波动和反复。”徐高阳告诉北青报记者,别看病房里的孩子年龄都不大,但是有的孩子甚至已经反复有过数次住院经历了。
“孩子病了,家长其实也是需要接受‘治疗’的。”在治疗过程中,陈旭、徐高阳、侯威威等儿科医生在给孩子治疗症状的同时,又肩负起帮助他们调整生活环境的职责,“有些孩子患病与家庭因素的影响关系密切,所以每到探访日,或者给孩子做完治疗后,医生、心理治疗师都会和家长进行联系。告知治疗进展之外,还会与家长探讨分析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侯威威说,他们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家长反思下孩子的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
除了家庭因素的影响外,陈旭也担心部分学校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多孩子接受的教育模式太卷了,这样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心理影响?”陈旭说,“担子的重量和成长的速度不匹配,为一些孩子患病埋下隐患。”
陈旭和儿科的医生们喜欢把这些小患者称作“自己的孩子”,在为孩子们诊疗的同时,陈旭和其他医生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尽早摆脱病痛折磨,回归到社会生活。
徐高阳说,他们其实也很理解这些住院患儿的处境,“这些孩子正是爱玩的年龄,在封闭病房接受治疗,对孩子的天性是有挑战的,但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徐高阳说,为了让孩子们更快适应环境,提升对于治疗的依从性,在康复科医生带领孩子们进行的折纸、做手工等活动外,儿科医生们也会不定期地带着孩子们开展活动。
“许多活动我们会让孩子们自己去组织,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他们的住院生活有些乐趣,我们还想通过活动,让孩子们锻炼与人接触、组织协调的能力,这也是一种治疗。”陈旭说,她对待病房里的孩子从来不会过于谨小慎微,“我们的治疗是要让孩子们回归正常的生活,融入社会,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更有助于他们治疗。”
“我以前带孩子们做过一个做小灯笼的活动,灯笼做好后大家把灯笼挂在活动室里,等到出院的时候,就把属于自己的那只带走。”徐高阳说,每看到活动室里的灯笼又少了一个,他都会为孩子们送上祝福,“希望他们很好地融入属于自己这个年纪的生活。”
无论是陈旭、徐高阳还是侯威威,每一个医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回归属于他们的生活。“看着孩子们因为疾病影响而无法展现应有的活力、纯真,甚至有些孩子选择极端的应对方式,我们心里挺难受的。但是,孩子又是希望。”陈旭说,每每看到一个又一个孩子因为治疗恢复社会功能,甚至数年不曾复发,她都十分有成就感,“我的这些孩子们,许多已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上大放光彩,我相信他们。”陈旭充满希望地说。
(除医生外,文内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天琪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峻
编辑/朱葳
校对/罗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