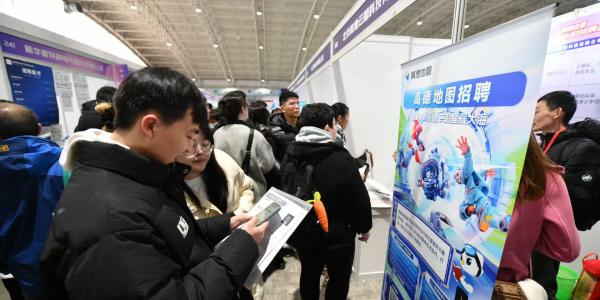近日,英国当代著名作家D.M.托马斯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白色旅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重磅推出。本书出版当年即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托马斯曾凭借此作与萨尔曼·鲁西迪、伊恩·麦克尤恩、多丽丝·莱辛、穆丽尔·斯帕克等知名作家共同角逐1981年布克奖桂冠。此次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陶磊倾情新译,使这部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间隔十一年再次与中文世界的读者相见。
托马斯以颠覆性的叙事手法将个体宿命和历史命运两种观念编织成一条阿里阿德涅之线,读者循此才不至迷失在语言、记忆、幻觉构成的迷宫中。透过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试图治愈疾病的经历,《白色旅馆》对二十世纪欧洲一段被掩盖的黑暗历史给出了直白、惨烈但绝非耸人听闻的文学呈现,是“对世纪创伤的灼热描绘,也是一次治愈创伤的尝试”。
差一点击败萨尔曼·鲁西迪的英国鬼才作家
D.M.托马斯于1935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早期作品以诗歌为主,他尤为钟爱弗罗斯特、狄金森和叶芝,三者作品中共同的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以及对爱情、死亡、孤独等主题的偏爱塑造着托马斯独特的文学气质。在《两种声音》《爱与其他死亡》《蜜月之旅》等诗集中,他反复吟咏人类心灵的不可解,死亡的摧枯拉朽之力,爱的强大与虚幻。
托马斯直至40岁才开始进行小说创作。44岁出版第一部小说《吹笛子的人》,获牧羊神奇幻奖;46岁出版代表作《白色旅馆》,获《洛杉矶时报》虚构类“年度最佳图书”、英国切尔滕纳姆文学奖,并入围当年布克奖决选名单。1981年布克奖颁奖典礼当天,《白色旅馆》的赔率起初遥遥领先,托马斯被认为是当年的夺冠热门人选。直至晚上七点半,形式突然逆转,最终萨尔曼·鲁西迪凭《午夜之子》摘取桂冠。
《白色旅馆》作为布克奖“准获奖作品”,一经推出便收到各方赞誉,迄今已被译为30多种语言全球发行。鲁西迪曾评价此书“兼具炫目想象力和智性魅力”,厄普代克则盛赞其“梦幻般的流动性与轻盈质地”。本书延续了托马斯早期关注的主题,全书由一个引子和六个篇章组成,透过一个女人倒错的欲望和预言性的死亡幻想,揭开二十世纪欧洲被掩盖的黑暗历史。故事融合了诗歌、日记、病历、书信等多种文体,叙事颠覆性媲美纳博科夫《微暗的火》。
一个女性的狂想中潜藏着整个世纪的创伤
小说以一首“非理性意象泛滥成灾”的粗劣诗作以及据此改写的私人日记开篇。星辰坠落,熄灭于水中;橘树成林,自窗边飘落;群山聚首,如鲸鱼般高歌……坐落于高山中的白色旅馆,宾客自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宴饮、起舞、畅谈;山中的冰泉能洗去一切罪恶,唯有纵情享乐一事不可辜负,哪怕四周燃起熊熊大火,洪水与山崩将人们吞没。这些奇异而荒诞的内容是女主人公丽莎自奥地利盖斯坦的温泉旅馆度假归来后“产下”的。她罹患歇斯底里症多年,饱受梦魇的折磨,有时还能看见可怖的幻象,似乎是对某种灾祸的预示。丽莎为此向弗洛伊德求助,希望后者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挖出疾病的根源。
第三章中,托马斯让丽莎以“安娜女士”的化名与虚构的“弗洛伊德”相遇,伪造出一份精神病医师的病历。通过安娜亦真亦假的讲述,“弗洛伊德”了解到她童年曾目睹过一桩家庭丑闻,以及丽莎后来在亲密关系中经历的诸多不顺。依据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确信丽莎的病症源于过往的创伤。
经过治疗,丽莎似乎已经痊愈,逐渐回归日常生活。直至第五章,托马斯对巴比亚尔大屠杀幸存者普罗妮切娃口述的化用,让小说从虚构的故事走向血淋淋的历史真实。前文四散的线索密集收束,在丽莎与儿子柯利亚背对纳粹枪口即将坠入万人坑的时刻汇聚为一点。她“穿过不可知的未来,穿过死亡,穿过超越死亡的无限空间”,明白了走到生命尽头的犹太女人丽莎和诗歌中那个放荡不羁的女人、那个无意间得知家庭丑闻的孩子始终是同一个人。时空的界限被洞穿,她意识到,年轻时频繁出现的梦魇和幻觉并非源于童年创伤,而是对将要到来的灾难的恐惧。
托马斯写道:“人的灵魂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无法接近,亦无从探访……哪怕有一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亚当时代就开始聆听和记录,他仍然连某一族类、某一个人都无法探索穷尽。”“弗洛伊德”的诊断被丽莎的悲剧命运证实为偏颇甚至是可笑的,托马斯以精神分析理论为饵“引诱”读者上钩,最终反转为一套“反精神分析”叙事。精妙的理论面对人类心灵的复杂性时显得力不从心,尽管如此,个体创伤的疗愈依然是可能的;而巴比亚尔大屠杀以及二十世纪,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暴力事件背后的集体性疯狂,是否还有被治愈,纠正,根除的可能性呢?
“只要真诚地去爱”
小说末尾,经过与开篇的情欲描写同样极具感官冲击性的大屠杀叙事之后,托马斯将丽莎带往一座死后的乐园。在这个“营地”,人们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大家都被剥夺了一切,也都将重新开始。“迦南”“朱迪亚”等直接取自宗教典籍的地名似乎暗示着这里是神明向犹太民族许诺的,“流淌着奶与蜜”的天堂,而语言班等教学活动,电影放映等娱乐项目,监狱等公共设施又为此地增添了几分现世的气息。托马斯融合宗教和政治学意义上的乌托邦概念,为逝者打造了一座安息之所,又机敏地引入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形式和规训机制,以削弱乌托邦式的结尾对小说反思意味的侵蚀。
“营地”不仅为被侮辱、被损害者们提供了永恒的安宁,也让人们生前所受的创伤得以疗愈。丽莎与母亲在此重逢,后者向女儿坦白自己失控的爱欲对家庭造成的伤害。聆听着母亲回忆自己命丧大火的经历,丽莎意识到死亡的无可避免,更感到分裂和破坏的欲望被另一种更为强大而恒久的情感所征服——“只要有爱,无论哪种形式,一定会有救赎的希望……只要真诚地去爱。”
死亡将所有人带向同一个终点,心灵得以回归未经冷漠和仇恨污染的原初状态,无论是在日夜弥漫着欢笑的白色旅馆,还是人们携手劳动、共同开拓新生活的营地,是爱、宽恕与希望将所有的心灵相连。面对大屠杀造成的世纪创伤,尽管小说充满反讽性的结尾暗示着作者不乏悲观的态度,但也同时传达出众多文艺作品对于人性光明一面的共同感知。正如布克奖评委会所认为的:“这部作品是对二十世纪创伤的灼热描绘,也是一次治愈创伤的尝试。”
《白色旅馆》D.M.托马斯 著;陶磊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2.10
执笔:苏牧晴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