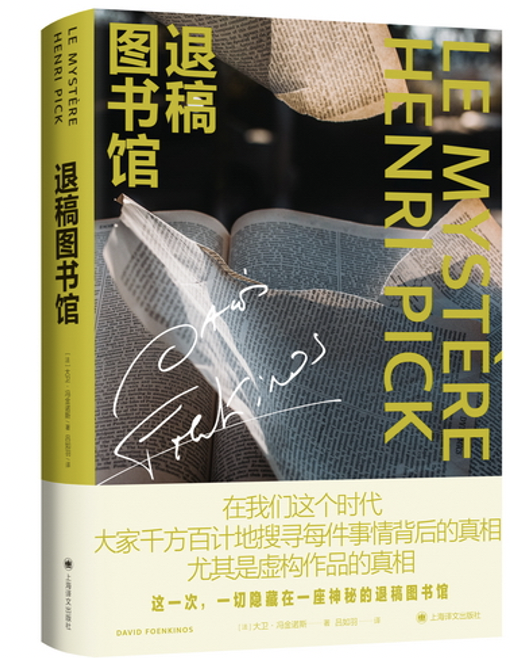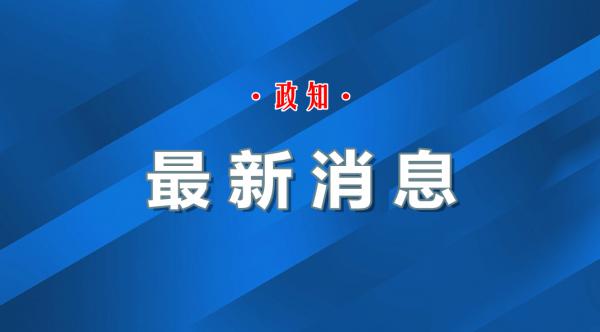1
一九七一年,美国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出版了小说《堕胎》。 故事讲述了发生在一名图书馆馆员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十分特别的爱情故事。女人有着令人惊艳的姿容。在某种程度上, 她是自己身体的受害者,就好像美丽是一道诅咒一样。 这位女主人公薇达说,因为她,有个男人在开车时失去了生命。司机着迷于眼前美得出奇的行人,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开车。 撞车之后,年轻女子冲向汽车。司机倒在血泊中,垂死之际只来得及说上一句:“小姐,您真美。”
实际上,薇达的故事不如图书馆馆员的有意思。因为小说的特别之处正在于此。男主人公工作的图书馆接收所有被出版社退稿的书。比方说,在那里可以碰上一个男人,在被拒绝了四百多次之后,他终于把书稿交了过来。如此这般,一部部千奇百怪的书稿汇集到了叙述者的眼前。在那里可以觅得一篇叫作《在一个酒店房间里的烛光下种花》的散文,或者是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提到的所有菜谱的合集。这家机构有个好处:由作者本人来决定书稿的馆藏位置。他可以任意翻阅不幸同行的作品,再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来存放书稿,不再希冀出版传世。相反,任何邮寄而来的书稿则不被接受。作者必须要亲自提交那无人想要的作品,就好像这个行为象征了他彻彻底底放弃的决心。
几年之后,在一九八四年,《堕胎》的作者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波利纳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暂时搁置布劳提根的一生,也不谈促使他走向自杀的境遇,先关注这所源于他的想象的图书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他的想法得到了落实。为了向他致敬,一位热心读者创立了“退稿图书馆”。 于是,专门接收失宠于出版社的书稿的布劳提根图书馆在美国诞生。这所机构如今已经搬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粉丝的创举一定会让布劳提根动容。不过, 我们真的能得知一位死者的感受吗? 图书馆建立时,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在法国人们也对此有所谈论。而布列塔尼大区克罗宗市的一位图书管理员想要如法炮制。一九九二年十月,他建立了法国版的退稿图书馆。
2
让-皮埃尔•古尔维克对设在图书馆入口处的小小布告牌很是得意。那是一句齐奥朗的箴言,对于一个从没离开过他的布列塔尼的人来说有些讽刺:
巴黎是过一事无成的一生的理想地点。
他属于热爱自己家乡胜过祖国的那一类人,但也不会因此就成为民族主义狂热分子。 他的外表则会给人相反的印象:身躯干瘪瘦长,脖子上青筋毕露,皮肤明显泛红,人们会立马把他的模样与暴躁易怒画上等号。但绝非如此。古尔维克是个审慎周全的人,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只要在他身旁待个几分钟,就能抛弃掉原本错误的第一印象;我们感觉得到,这是个能够自我管理、十分井井有条的人。就是他调整了市立图书馆的藏书位置,为所有渴望容身之所的稿件留出了一片空间。这一番大动静让他想起了豪尔赫• 路易斯• 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把一本书从图书馆里取出来再放回去,这会让书架疲乏不堪。”它们今天该累坏了,古尔维克笑着想。这是博学者的专属幽默,并且得是孤独的博学者。这是他的自我定位,事实也的确如此。古尔维克天生少了根善于社交的筋,他很少会和邻居们为了同样的事情发笑,不过,听笑话的时候,他知道要努力逼着自己笑一下。他甚至时常会去街尽头的小酒馆喝一杯,和别人聊些有的没的,主要是聊些没的,他想。在那些热热闹闹的时刻,他甚至能来一局扑克牌。他并不会因为被看作一个普通人而感到困扰。
除了独居,人们对他的生活所知甚少。他在五十年代结过婚,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后就离开了他。有人说,他是通过征婚启事遇上她的:他们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信才见面。这是这段婚姻失败的原因吗?古尔维克大概是那一类人,别人会不管不顾地爱上他激情昂扬的告白,而在漂亮的文字背后,现实却让人失望。当时也有些恶意的流言蜚语,认为他妻子这么快离开他是因为他性无能。这番推测并不可靠,但是,当从心 理学上很难解释问题的时候,人们就喜欢找一些更加基础的原因。所以说,这段感情经历彻头彻尾是个谜。
在妻子离开之后,他不再拥有公开的稳定感情,也没有子女。很难对他的性生活有所了解。或许可以把他想象成寂寞女人的情人,和一群艾玛•包法利谈着恋爱。她们在一排排书架间寻寻觅觅,大约不仅仅想在小说里感受罗曼蒂克。这个男人会阅读,因此懂倾听。在他身旁,她们可以从机械单调的生活中获得解脱。但对此,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古尔维克对于他的图书馆的热情从未减退。他专注地接待每一位来访
的读者,留心听取他们各自的需求,在纷繁的藏书中开辟出一道道私人通道。 对于他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喜不喜欢读书,而是要知道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本书。每个人都可以热爱阅读,只要遇上那部对的小说。它会让你欢喜,对你说话,使你手不释卷。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发明了一个看起来有些怪异的方法:通过细致观察读者的外表,他便能推导出对方应当要读的作家。
他孜孜不倦地致力让自己的图书馆更加兴盛,因此,他必须不断扩张藏书规模。在他眼里,这是个巨大的胜利,就好像架上的书籍是一支力量日益削弱的部队,任何一点对消亡的抵抗都带有浓浓的革命意味。克罗宗市政府甚至同意,为他增加一位助理人手。因此,他张贴了一张招聘启事。古尔维克喜欢选择要订阅的书籍、整理书架以及许多其他事务,但做出事关选择一个人的决定,让他有些害怕。但是,他还是希望找到一个文学上的同道中人:能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花上好几个小时跟他讨论塞利纳作品中省略号的用法,或是一起研究托马斯•伯恩哈德自杀的原因。这个雄心壮志只存在一个障碍:他心里很清楚,不管来的是谁,他都无法拒绝。 因此事情也会很简单。谁第一个来应试,谁就会被雇用。于是,玛嘉利•克罗泽进入了图书馆工作。她拥有这项无可辩驳的优点:能够快速响应工作岗位的招聘。
3
玛嘉利并不特别喜欢阅读,但是,作为两个年幼男孩的母亲,她必须得迅速找到一份工作,特别是因为她的丈夫只有一份在雷诺汽车维修厂的半日工作。本土制造的汽车越来越少,经济危机笼罩着九十年代初期的法国。 签下工作合同的那一刻,玛嘉利想到了丈夫的双手;那双永远沾满油污的手。而她成日都在摆放书本,不会有那样的烦扰。这将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从手的角度来看,这对夫妻走上了全然相反的轨道。话说回来,古尔维克也挺喜欢和一个并不过分看重书本的人一起工作。他意识到,不用每天早上都讨论德国文学,也能够和同 事保持融洽的关系。他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而她来负责后勤保障;这个二人组运行得十分平稳顺当。玛嘉利不是会质疑上司创举的那种人,但她还是忍不住对收藏退稿这件事提出了疑问。
“存着这些没有人要的书稿有什么好处?”
“这是个美国人的主意。”
“然后呢?”
“是为了向布劳提根致敬。”
“那是谁?”
“布劳提根。您没有读过《巴比伦私家侦探》?”
“没有。那不重要,这是个奇怪的主意。并且,您真的希望他们把书稿都放过来吗?我们会招惹来这一带所有的精神病。谁都知道作家是疯子。那些没能出版的就更没救了。”
“它们总归得找个容身之处。您就看成是做善事吧。”
“我知道了:您想我做失败作家们的特蕾莎修女。”
“对,差不多。”
“……”
渐渐地,玛嘉利接受了这个主意的美妙之处,并竭力以善心参与这件奇事的操办。当时,让-皮埃尔•古尔维克在一些文学类报纸,特别是《读书》和《文学杂志》上都登了布告,邀请所有想要将书稿放置于退稿图书馆的作家来克罗宗一趟。他的想法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许多人纷纷赶来。有些作家穿越大半个法国,只为卸下自己的失败果实。这段旅途像一条神秘的道路,一条文学上的孔波斯特拉之路。他们踏过数百公里,以求终结未曾发表带来的悲 伤沮丧,这里面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穿过这条道路,写下的文字 便会消失在世间。而这种力量在克罗宗所在的这个省份似乎显得尤为强大:这里是菲尼斯泰尔,是大地的终点。
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