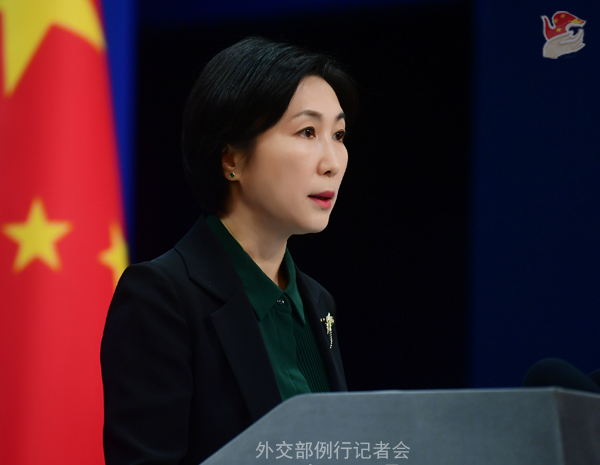主题:余华和他的《兄弟》
时间:2022年7月22日20:00
地点:PAGEONE书店(花园胡同店)
嘉宾:余华 作家
俞敏洪 “新东方”创始人
这个人那么好玩儿,却写着这么悲苦的书
主持人:《兄弟》是余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故事,并通过他们的故事反映了中国社会四十年间的变迁,可以说是一部又深刻又好读的大众史诗。今天,借着《兄弟》新版上市的契机,我们有幸请到了余华老师和俞敏洪老师。
余华老师已经是家喻户晓,读者关于余华老师的热评是“把快乐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读者”。
俞敏洪:我一直是把悲伤留给自己,把快乐也留给自己。
主持人:两位一开始怎么认识的,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余华:我们之前见过一次面。以前看到视频里他说话,有一些是会议上的发言,有一些是朋友的聊天。他早期上课的视频我也见过,“新东方”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跟中国的不少家庭都有关系。
俞敏洪:余华老师的《活着》出来的时候,我应该算是第一批读者。那个时候是1992年,我的新东方还没起来,所以读《活着》特别有感悟。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拼命挣扎的一种情况——能活下去就好了。读完《活着》,他出的每本书我都读过,《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文城》我也读了,所以神交已久。后来我看他的采访视频,觉得这个人那么好玩儿,而写着这么悲苦的书。自己这么快乐,这是折磨别人,享受自己的生活。
主持人:你们第一次见面也像网友见面,跟网上的印象相比有什么反差吗?
俞敏洪:没有什么反差,我看过他的很多采访视频,包括央视的《朗读者》也都看过。他能稍微喝点酒,我们一上来就能碰碰杯,他酒量我估计不如我。因为我不是真正的文人,所以不存在文人相轻。我对他有崇拜,中国我喜欢的小说家也是能数得过来的,特别是现当代,他的书是最能够打动我的。他写的大量的书是农村背景、城镇背景,我是在小城镇长大的。我1962年出生,他写的那个时代或多或少我是亲身经历过,所以那种感觉比较亲切。我知道这一个类型人群的生活状态大概是什么,所以尽管有一点超越现实,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或者浓缩的现实主义,但是如果把一个人的命运扩大成那一群人的命运,实际上是八九不离十的。把《活着》中间的一个人带着一个家庭的命运,扩展成一个村庄的命运,那个基本能吻合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读起来比较亲切。
我从他的书中读到,人生悲苦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你能掌控的。你能掌控的是出现人生悲苦的时候,如何更好地活下去。这是我当时读《活着》的感觉。
我们两个人是同龄人,都是南方小城镇长大的,这种感觉非常亲切。原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大作家,我是一个小商人,我要攀附他的话不太好。刚好有一个机会,朋友之间互相认识,说你想见见余华吗?我说他想见我吗?后来传过来的信息是他也想见我。所以后来一起喝了一顿大酒。
余华:我以为下一次见面还是喝酒,结果是工作,就是这一次。
五个凌晨重读新版《兄弟》 不断地笑、不断地哭
主持人:余老师创作《兄弟》的时候,是从具体的情景出发,还是从人物出发?
余华:是因为《兄弟》涉及到两个时代,我和老俞都是这两个时代的人。这两个时代太不一样。但因为你经历在这样两个时代中,有的时候其实是麻木的。我印象中,从1995年开始,我经常出国,有机会到国外去,跟国外的同行们或者记者们聊天,聊到我小时候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他们很惊讶——难道这都是你的经历吗?对西方人来说可能不会有那么反差大的时代,所以我回来就想写《兄弟》这样一本书,兄弟两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选择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是因为可以敞开写。这在写作时给你带来发挥的场地、环境会更大一点。没有血缘关系,把兄弟情写出来比有血缘关系的还感人,但是写到他们背叛的时候,从传统观念讲也能接受,否则你接受不了。所以,有时候写作有点像当年老俞管理“新东方”一样,好多细节、人事安排,谁应该在哪个岗位上,谁应该做什么。只不过是我可以修改,他一旦指令发出去之后不能改。
俞敏洪:也能修改,弥补。
主持人:为什么想要用“兄弟”做小说的书名?
余华:没有别的书名更合适。有的小说一开始就有书名,比如《活着》,《第七天》。《兄弟》是中间知道肯定就是它了。
主持人:哪一个瞬间?
余华:大概上部没有写完就知道肯定是“兄弟”了,因为再合适不过,无法找到别的用词。
俞敏洪:我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因为《兄弟》这本书,它既体现中国传统意义上兄弟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们两个又不是血缘关系上的兄弟,最后实际上是共同在苦难中成长,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由于个性的不同,某种意义上是分道扬镳了——只是表面上个人生活命运的分道扬镳,两个人在背后由于过去共同经历的时代紧密相连,已经是超越血缘关系的情谊。实际上是用两个人物的命运,描写整个时代的变迁。从传统上的兄弟情谊到兄弟在面对新时代的时候,个性的冲突或者命运的冲突。这种关系在两个男人之间,只能用“兄弟”这两个字或者“哥们儿”能够表达出来。
主持人:听说余华老师收到新版以后花了五个晚上重读了一遍。距离您当时创作已经过去比较久了,这次重读,您有什么感受?
余华:这次重读是有原因的。之前我刚好读了首师大张翔教授写的关于《在细雨中呼喊》的一篇文章,《在细雨中呼喊》发表已经有31年了,我看那个文章的时候,发现我对小说有点陌生了。《兄弟》到了,干脆就把新版重读一遍,是五个凌晨,从凌晨一点读到五六点钟左右,不断地笑、不断地哭、不断地笑、不断地哭,把它读完了。
俞敏洪:你自己还这样?
余华:确实是这样。《兄弟》创作时间比较近,是16年前完成的,所以很多细节我还记得,但是顺序记错了。中间有很多描写,包括像宋钢卖白玉兰,很多读者都很喜欢这一块,我已经忘了,读的时候想“那段写得真好”。我写宋钢下岗以后做了很多工作,每一段工作都是叙述性的,基本都是写到位,以这样的方式。
民营经济就像荒原长出松林,前提是有一个环境
俞敏洪:现实中有兄弟的原型,还是并没有?兄弟的形象只是你作为小说家创造出来,放到时代中间的?
余华:肯定有原型的,但这个原型肯定不是一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甚至更多。他们都具有某种代表性,每一个人物代表的不是自己一个,而是代表着一群人的形象。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让读者产生共鸣。
俞敏洪:不管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的场景,是不是跟你的家乡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余华:就是因为我们海盐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过去只有不到一万人,现在整个县城有十万人。
主持人:《兄弟》里的人物就是从您生活经历的千千万万人里面提炼出来的。
余华:有的不一定是海盐的,有的是在北京、杭州、海南、外国的。
主持人:有读者说,李光头这个人就像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想问余华老师,李光头的性格根基在哪儿?怎么会想到写这个故事?
余华:这个老俞更有发言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最早富起来的有一批是个体户,这里面包括一些刑满释放人员,他们从监狱出来没有工作,只能自己做个体户,就成了万元户,90年代开始起家。像李光头这样的人我见过好几个。李光头这种做法,在我们当年那个时候是乱中取胜。
俞敏洪:紧卡的规矩突然被放开,脑子最灵活、胆子最大的人,就变成第一批改革开放的个体户。从个体发展成小工厂,跟《兄弟》书中描写的李光头成长经历或多或少有一定的相似性。当时我们村第一批致富的人,不少都是以前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的,他们脑子灵活,胆子非常大。放开以后,这批人变成较活跃的人。他们已经丢掉了一切,突然国家的经济逐渐放开、允许大家做生意,是一个天天扛着锄头到地里干农活的老实农民做生意,还是那些本来就已经没有面子、没有身份甚至可以不顾面子的人做?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慢慢开始正常化,有了真正第二批开始把企业做大的企业家,到第三批开始跟科技结合的企业家。
一切从混沌开始。混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一个环境。就像一片荒原中间,不需要去播种任何松树的种子,先是由草长成灌木丛,然后成为快速生长的树木,再慢慢就会长起松树,坚韧不拔地长高,把快速生长的树挤没了,后来变成非常壮观的原始森林。民营经济就是这样的。余华老师的《兄弟》里描述的李光头这种大胆的、什么都敢往前冲甚至不守规矩的人,恰恰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的代表。这些代表后来的发展大部分都不可能长久,因为他们胆子太大、太不守规矩。他们恰恰是第一批长出来的荒原上的草和灌木丛,是未来更高的树和更永久的树成长的基础。前提条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经济环境在,雨露滋润。没有这个经济环境是不可能的。
没有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只会为自己的内心需要写作
主持人:我记得余华老师多次在采访中提到,《兄弟》是您最喜欢的作品。一开始在国内出版的时候,其实您非常期待好评如潮,结果却发现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余华:当时我真实的想法现在可以说了,我想:“这帮人真笨!”
现在我知道什么原因了,因为《兄弟》是2005年和2006年分成上部和下部出版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很开放了,但我们的审美观念非常保守。所以为什么这个书在法国、在英语世界、德语世界好评如潮,没有人认为这本书过分,而我们会认为很多地方的描写已经都不是粗俗,而简直是放肆了。法国人经常把《兄弟》跟拉伯雷的《巨人传》相比,和左拉的作品相比,因为左拉作品里有很多自然主义的描写。德国最有意思,当时德国的报纸有一个评论,叫“中国鼓”。意思是,格拉斯的《铁皮鼓》当年出版的时候,被德国一群评论家骂成“垃圾”,就跟《兄弟》当时的遭遇一样。英语世界是把《兄弟》跟狄更斯相提并论的,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也有点夸张。所以主要还是一个审美观念的问题。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的时候,当时的批评不是说这两部小说写得不好,而是一个先锋派作家怎么突然写这样的小说?我当时说过一句话,后来铁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把我这句话好好赞扬了一番,我当时说:“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只会为自己的内心需要写作。”
主持人:网上有网友评论您的作品是“余华痛苦套装”,里面包括《兄弟》《活着》等等。也有读者说《兄弟》是余华老师“把悲伤留给读者最多的一次”。您怎么看?
余华:没有,笑声留得更多。
俞敏洪:对,以《兄弟》为例,大家经典的评论叫做“又笑又哭”。中间大量的描述是会让你不自觉笑出来的,但是人物整个命运走向以及命运给人们带来的无可奈何,在某种意义上是让人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某些场景或者某种阶段。我读《兄弟》,笑的时候肯定比哭的时候多,因为觉得描写得太好玩儿了,但实际上又有看着人物命运最后流泪的时候。
一部小说如果完全是沉重、没有美好肯定是不对的;如果都是美好而没有沉重,它就没有深入到人性的最根本处。就像《活着》这样沉重的书,也是用第三个人听主人公叙述的方式,放在一个人经历了人生的风吹雨打以后,坐在田埂上跟陌生人平静地讲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其实这种场景的设计,会把人的悲伤缓解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设计,读《活着》会有崩溃的感觉,因为人生就是一系列的苦难。但是开场就碰到老农民在地里跟牛讲话,安静地耕地,人生有苦难,又回归平静。用一个老人孤独的身影,陪着老牛讲述人生一辈子,已经把那个紧张部分消除掉了。因为不管人生中遇到多少亲人的去世,遇到多少苦难,最终获得了一个平静的结局。这就是非常重要的读小说时候给人的缓冲。
我认为《活着》,包括《许三观卖血记》,是把生活中的美好和苦难糅在一起,来给人产生一种超越现实,但是又无比接近现实的生活的真实感。
不要为了时代去写故事和人物,是为了写人物和故事写时代
主持人:您觉得和《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相比,《兄弟》的特别之处在哪儿?
俞敏洪:两个不同个性又互相无比信任的人共同成长的经历。真正导致两个人命运不同的是时代,如果一直在旧时代或者出生在新时代,他们两个人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人物的个性和性格决定人物命运,在这个小说中间会得到印证。其实这是对一个真实时代变迁的描述,给人带来比较深刻的思考。
主持人:有读者评论说《活着》比较像《老人与海》,《兄弟》像《百年孤独》,余华老师怎么看这个评论?
余华:评价太高了。《老人与海》是我非常尊敬的小说,它里面的圣地亚哥和《活着》中的福贵,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一样的。
主持人:余华老师喜欢“混世魔王”李光头的形象吗?
余华: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我也很喜欢宋钢,这次重读,宋钢让我好辛酸啊。
俞敏洪:大部分人都是宋钢而不是李光头。他代表了大部分人面对命运的无奈。
余华:当时代剧变之后,大部分人不知所措,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儿,该往哪儿走。宋钢代表了这样一个群体。李光头这个人物更有时代感。老俞有一点说得特别好,人物把时代带出来了。我的小说里面为什么有时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个时代,一定要写这个时代。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不要为了时代去写故事和人物,是为了写人物和故事写时代,是这样一个关系。这样的书读者才会读下去。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您特别喜欢李光头,为什么呢?
余华:因为他真的是代表了中国八九十年代社会中的一种勃勃生机。虽然有很多很多毛病,但他不是一个坏人。这代企业家现在已经不多了,但是他们走出了第一步,这个第一步我们不能否定。法国写《21世纪资本论》的皮凯蒂,是世界受欢迎的经济学家,他在新书里面也写了《兄弟》。就像丹尼尔·科恩写的那段话,新经典用在腰封上了:“这是一本让你对小说重拾信赖的书。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哲学的传承,因为它能够让你理解人类的灵魂,它也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传承,因为它还能引导你理解社会的机制,以及人类的激情是如何被社会捕获、被社会利用,从而被社会塑造的。”这是巴黎高师的经济系主任。
主持人: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生动、丰富的,也在这个作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两位老师会觉得那个年代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很重要的影响?
余华:我们是这两个时代的穿越者,经历这两个时代,弥足珍贵。因为以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个反差之大,难以置信。
俞敏洪:我想说的是,一个时代的苦难,或者说一个苦难的时代,也可以留下弥足珍贵的传承和历史的记忆。也许未来的小说会慢慢缺乏描写这种大时代变迁的广阔和悲伤,但是在任何安宁的时代也有个人的悲欢离合和情仇爱恨,或者是绝望悲苦和时代相结合。某种意义上,余华老师描述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到现在,改革开放40年往后的时代,能不能写出不断繁荣时代的人生故事,这也是对余华老师的考验。
文/新经典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