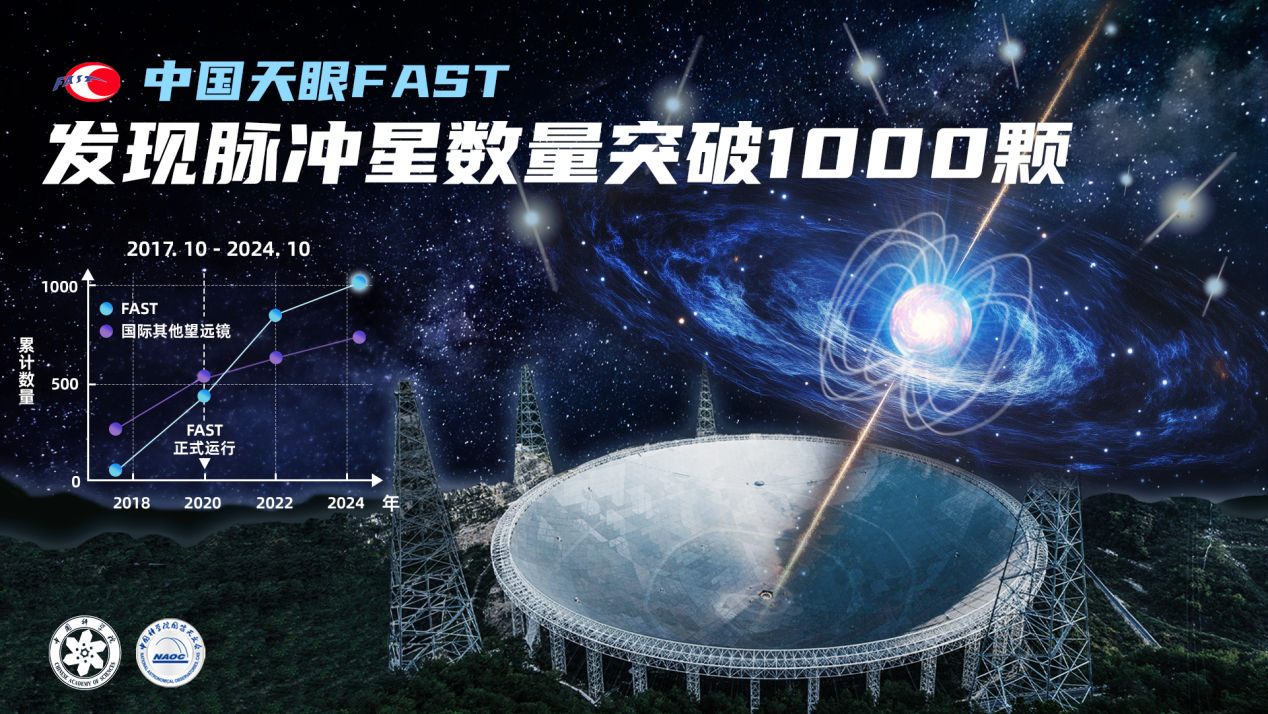古籍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特辟《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栏目,以期在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出版以及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等方面展开讨论,以促进古籍事业的发展。
在东西方几个古老文明当中,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注重书写的国家;与印度、伊朗以史诗传唱,经典传诵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文明不同,中国人更相信书写下来的文本,并以文本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文明。中国是最早发明纸张的国家,这就为书写提供了廉价而又实用的书写载体,较之羊皮、简牍、石板、铜器,能够书写更加丰富的内容,承载数量更多的文字。而且,中国还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让书籍文本利用印刷的手段大量复制出来,使得中国的典籍比世界其他文明的典籍更早地被大量复制,并流传广远。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喜欢收藏图书的国度,举凡官府、学校、寺庙以及个人,都喜爱收藏,各朝各代都有公私收藏,保存了大量的图书典籍;而这些公私机构还组织抄书、印书,使得中国的古籍既得到保存,又不断推陈出新。因此,延至今日,海内外都有大量的中国古籍的留存,有许多还是善本。
然而,分散收藏在海内外的古籍需要信息收集、编目整理;通过研究,确认价值;重要典籍,则应当标点校注,出版弘传;有些古籍精华,还需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广为大众所知,甚至译成外国文字,弘扬海外。为此,有一批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者,多年来一直为古籍工作投入大量精力,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做出可喜的成绩。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今后的古籍工作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无疑对今后的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工作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借此机会,我也想就多年来参与古籍工作的体会和本人熟悉的领域,对今后一些整理研究工作,提出一些展望。
古籍数字化是重中之重
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古籍是善本,作为文物,要妥善保管,因此一般不轻易示人;而一般古籍的数量又十分庞大。由这两个特点,要将古籍为一般读者所用,最好的保护和使用方法是扫描存储。而我们又拥有最多的标点本古籍,因此也最具备进一步数字化的条件。目前来说,古籍的扫描工作有些单位积极,有些单位迟缓,也有一些单位拒绝,而数字化古籍虽然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数量上还赶不上个别私营的企业成品。这方面需要国家的投入,也需要国家层面的组织和命令,如果能够像“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那样,对各公立单位有数字化的投入和要求,必将有较大的进步。我曾发表《数字化关系到国家命脉》一文(《中国文化报》2019年12月20日),希望把这个事情提高到国家层面来推进。
古籍整理要出精品
迄今为止,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传世古籍方面,我们有标点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有标点校注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新编诸子集成》等古籍整理的精品,现在正在进行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本,更是推陈出新之作。但不能不说,经过多年来的整理工作,一些重要的古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整理,近年来不论是提交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古籍整理项目,还是申报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领导小组的出版项目,有不少是不太重要的作家别集,甚至乡贤著述、地方志书、普通医籍。这些不能说没有必要整理,从我们历史研究的角度,可能某些书有其特殊的用途。但从整个古籍整理出版来说,我们还是应当选择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精品,在标点之外,做深度注释、研究,乃至外译,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值得规划和推进。
海外古籍的调查与整理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量的古籍流散到海外,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许多珍贵古籍被殖民主义强盗掠走,成为中国文化的“伤心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海外古籍,也客观上推动了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多年来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大量的海外古籍的传存情况已经调查清楚,甚至有不少以影印或标点本的形式整理出版。然而,还有一些重要的古籍收藏是此前工作的盲点或做得不够的地方,比如俄罗斯收藏的汉籍,还有日本私家的藏卷,我想还有一些欧美小国的藏书,也还没有系统的调查。我们近年来一直在调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斯卡奇科夫旧藏的汉籍,其中就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五十年代苏联曾送还我国64册《永乐大典》,由此也可以推知其收藏之富,尚不为外界所知。如果从丝绸之路研究的角度来讲,也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海上丝路文献,收藏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瑞典、丹麦这些曾经从海路来华的国家当中,我们应当像调查敦煌卷子一样,一个类别、一个卷子、一张残片都不放过地调查、记录,才能摸清底细,做出进一步整理的规划。
敦煌文献的深度整理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因为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伤心史”,因此历来备受中国学人关注,特别是1980年以来,随着海内外几大敦煌文献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公布,引发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热潮,产生了不少成果。此后又有大型图录的出版,较缩微胶卷更胜一筹,大大推进了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目前又有大量高清彩色照片在网络上公布,使得先前以缩微胶卷和黑白图版为依据整理的敦煌文献,有进一步深度整理的必要。但目前还有不少敦煌文献没有数字化,比如倡导“国际敦煌项目”(IDP)的英国,就没有把英国图书馆的藏品全部上网(不到一半),所以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与此同时,敦煌文献作为写本文献,其整理的方法与传统以刻本为主体总结出来的校勘整理方法并不完全一致,而与今日新的“书籍史”“写本学”“古文书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需要吸收这些学科的成果,对敦煌文献做出“深度”的整理,并为敦煌学之外的学界提供把握敦煌文献的工具和“善本”。
新疆吐鲁番、库车、和田以及内蒙古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既有写本,也有刻本,也应纳入与敦煌文献相同的整理工作当中,因为它们之间都拥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有时候必须放到一起整理,才能够做出一个完整的文献,比如郑玄的《论语郑氏注》,不可能把敦煌和吐鲁番写本分开整理。相对来讲,吐鲁番文书的收集、整理,特别是数字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只有在这些工作充分完成以后,吐鲁番等文献的整理才能达到一个与敦煌文献相匹配的高度。而吐鲁番、库车、和田等西域地区出土汉籍的整理,又包含着中华文化在西域地区流传的另外一层重要意义。
民族古文字文献
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民族古文字文献,也是今后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点。这方面过去受到材料和语言人才的限制,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是落后于欧美、日本。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学者已经在多种民族古文字的解读、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各国收藏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也在陆续出版,这些出版物由于晚于汉文文献,反倒有些直接出版了彩色高清图版,而国外也有一些网站在上传民族古文字文献方面较汉文文献更为积极,所以在材料方面甚至更胜一筹。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这些梵语、龟兹语、焉耆语、于阗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叙利亚语、藏语、回鹘语、西夏语、蒙古语等各种典籍中,有些译自胡语,有些翻传汉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珍贵文献,其意义甚至较汉语文献更为重大。这些文献的系统整理,包括图版刊布、文本转写和翻译、规范出版,将极大丰富我们的古籍整理内容,也会大大充实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内涵。
作者/荣新江,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
编辑/崔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