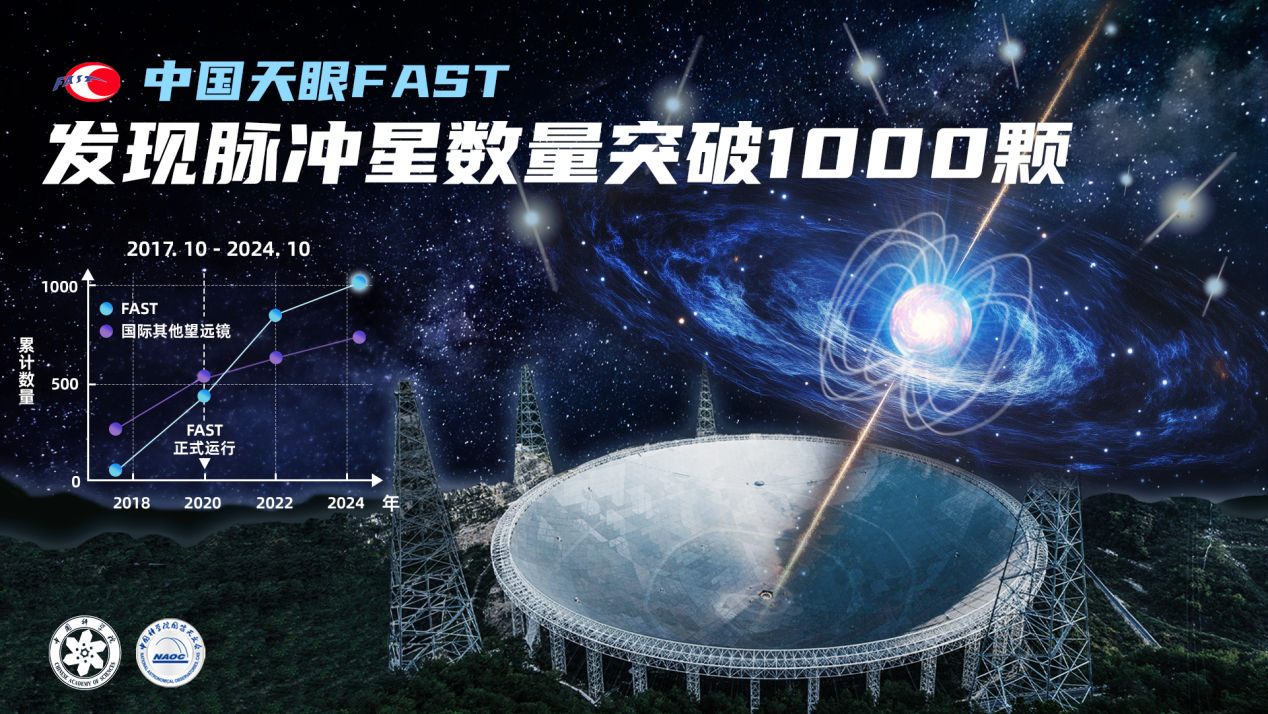长篇纪实散文《娘》是一部关于湘西女性的史诗,也是一部关于母亲的史诗。《娘》真切地描述了湘西大山深处一位母亲所遭遇的的屈辱和苦难,以儿子的视角,全景记录了母亲牺牲自己的名誉、饱受苦难,以血泪和生命抚养儿女、保护儿女,以品德和精神教育儿女、培养儿女的经历与恩典。
作者以深情的口吻、回忆的笔触,讲述了自己幼年被父亲抛弃,跟母亲相依为命,直至母亲过世,母亲为儿女付出所有精力、熬尽所有血泪的苦难岁月。迫于生计,柔弱又坚强的母亲带着儿女两次改嫁。可为了维护儿子的成长,母亲毅然决然离婚,并不再改嫁。母亲以铁人般的意志艰苦劳作,只身一人抚养起整个家庭。母亲曾经濒临瘫痪、儿子高考落榜三次复读、小女儿所嫁非人,母亲历经重重磨难,但却以中国妇女特有的吃苦耐劳和牺牲精神支持儿子一路走出大山……
《娘》第二十章
在我左右彷徨时,乌云沉沉的天空里,突然间漏下一线光来,照射到我人生的十字路口。阳光和雨滴同时飘落下来,架起了我人生的一段彩虹。
我出生的老家——熬溪来人找我了。
来的是彭文贵二叔和我同爹不同娘的哥哥四龙。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同爹不同娘的哥哥四龙。
哥哥四龙木讷、沉默、寡言。皮肤黑红黑红的,一身的肌腱。三十来岁的大男人了,一讲话就脸红、低头。
兄弟第一次见面,没有那种抱头痛哭的场面。十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已经在我和我哥之间隔了一堵很高很厚的墙,我们彼此是陌生的。特别是当我从乡亲们口中得知我是被爹抛弃的时候,哥的到来,没有在我的心中激起一点涟漪。
娘却是惊讶和欣喜的。
娘虽然也这么多年没见到我这同爹不同娘的哥,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娘怜惜地喊了声:四龙。
娘把我拉到四龙身边讲:这是你哥,四龙。
我没喊。
我十八年漂泊的字典里,没有“四龙哥”这三个字。
哥也没喊我,倒是先喊了声:娘。
哥的这声娘,让我非常惊讶,并有了一丝感动。这些年,我一直怨恨娘,我都没怎么喊娘,同爹不同娘的哥居然喊了。我对哥有了一丝好感。哥喊的这声娘,让我想象出当年娘对哥很好。
彭文贵二叔讲:老家人听讲你们搬回保靖县了,都很高兴。你们几母子一走十八年,都不晓得你们是死是活,现在你把一尺大的学明养这么大了,大家都想学明转去看看,想你们把户口迁到熬溪去。
彭文贵二叔讲话时,哥一直在悄悄看我。他慌乱而迷离的眼神,看得出激动和不安。激动的是他有了丢失十八年的弟弟,不安的是这个弟弟会不会认他。
娘讲:我米有(没有)什么意见,看学明的。学明同意,就去;学明不同意,就不去。我们走断脚杆,就是为了转到一个好安生的地方。
娘话没讲完,我就斩钉截铁,冷冷两字:不去!
二叔讲:你是不是放心不下你娘和妹?她们都去。
我摇头:不是,就是不想去。
哥哥讲:二佬,你放心,我和你嫂子会对娘和妹好,不会让娘和妹受苦。
我冷笑:不会受苦?受得还少吗?不去!
我嘴上只这几个字,心里却有很多话:十八年了,我们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你们哪个来找过我?哪个想过接我回家?现在,我长大成人了,可以自食其力了,你们假惺惺地来接我,我会去吗?还有,我自己对我娘和妹都这个样,你们会对我娘和妹好?鬼才信!
哥和二叔,就这样被我冷冷地打发走了。
我对那个老家,对那个老家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怨恨。我不需要他们这时候来献殷勤。十八年了,离开老家,我还不是照样活了下来?哥和二叔踏着夕阳离开时,夕阳的余晖,撒给我的不是秋天的炎热,而是冬天的悲凉。
那条从家门前穿过一片油茶林的泥土路,就此定格了哥和二叔有些失落和伤感的背影。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哥和二叔的背影,特别是哥的背影。那条红壤的泥土路,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条脐带,连着我和哥,连着我和老家——那个我不到一岁就离开了的故乡。
我开始想象我的那个老家、那个故乡,想象哥住的木屋,想象我出生的那间房,想象寨子上的那些从未谋面的亲戚。那都会是什么样呢?我对故乡的情感,不知不觉开始生根、发芽。这时,我才发现每个人都有一条根深埋在故乡,只要稍稍飘来一丝故乡的气息,根,就会紧紧地把你和故乡箍在一起,长出新芽。我对故乡的情感之所以慢慢苏醒、复活,就是因为哥和二叔带来了一丝丝故乡的气息。
我有了去故乡看看的欲望和冲动。
可是,当这种欲望和冲动出现时,娘找爹要伙食费时抢我的情景就会强烈再现,娘和我们兄妹所受的苦难就会一幕一幕在脑海重放。有一种声音在呼喊:不能去!不能去!不要忘记你是怎么离开那里的!不要忘记你是怎么吃苦的!
我第一次因为故乡陷入煎熬。
娘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讲:儿,想去就去,不远,就七八里呢。
娘讲:娘跟你爹离婚,不是你爹不好,更不是你这个哥哥不好。他们都好。你爹是个老实人。心好。人好。脾气也好。你爹的爹娘也死得早,你几个叔叔,都是你爹讨米带大的。你爹还养他四叔四婶娘,给他们养老送终。你爹就是太懦弱,米有(没有)主见。什么都听他四叔四婶娘的。要不是他四叔四婶娘作怪,你爹也不会不要我们。
这是我十八年来,第一次听到爹的有关信息。十八年来,我知道自己没有爹,就从来不跟娘问爹的情况。娘也知道爹对我幼小的心灵伤害很大,从不跟我谈爹。爹在我的生活里连个影子和符号都不是,就是虚无。
也的确是一个虚无。爹一生连一张照片也没留给我,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到现在都不知道。想象的余地都没有。
娘讲:你看到你四龙哥了,你爹就跟你四龙哥一样,脱的壳壳。我没想到,娘因为爹而受了这么大的磨难、这么多的苦楚,娘居然讲爹人好、心好,是好爹。
娘讲:我晓得你恨你爹,你爹不是不要我们,你爹是死得早,你五岁不到你爹就死了,你爹不死的话,肯定早把我们几娘仫(母子)接去了,你莫恨你爹。你爹也活得不容易,有时间去跟你爹烧根香。
去跟我爹烧根香?开玩笑!
我真不知道娘是怎么想的。
我才不去!
娘讲:你更不要恨你四龙哥和那些家务堂,你四龙哥从小就米有(没有)爹娘,是孤雀一样的孤儿,比你还命苦。这个世界上,米有哪个欠哪个的,只有各人(自己)欠各人的。该有还是不该有,都是命上带的。都在农村,都苦,各人都爬不起来,哪门(怎么)还扶得起人家?你彭家人在熬溪大根大族、大家大业,你是彭家人一根马鞭子发下来的,哪能不认祖归宗?
舅舅舅娘劝我不要去,舅舅舅娘讲:你喰(吃)苦受难把学明养这么大,他们哪个来看你一眼?现在大了,他们来接你们了,早到哪里去了?他们是看学明大了,是好劳动力了。
娘讲:我这一辈子就欠学明最多。水玉、学翠几子妹的爹都活得好好的,她们想看就看得到,学明生下来就不晓得他爹什么样子,就米有(没有)他爹那边的家务堂(家族)痛过他。现在,他爹那边的家务堂好不容易想痛他了,我哪能不让他们痛?痛学明的人越多越好。
舅娘讲:你忘记当年他们是哪们整你的了?你眼泪水泡饭喰的日子忘记了?你忘记了,我们米有忘记。
于是,舅娘给我讲起了生我时落难的场景。
舅娘讲,你娘生的时候,你爹他们哪个都米有拢边,你娘各人扯断脐带生的你。米有喰的,米有穿的,就连一根柴都米有。我那天背了屋里几十斤米、捉了屋里唯一的一只鸡去看你娘,你娘和你二姐都挨了一天饿。我想烧火给你娘杀鸡修鸡,一看,一根柴都米有,我火冒三丈,跑到你爹屋里跟你爹和他四叔四娘大吵了一架,他们不要以为你娘屋里米有人!我要到你爹那里搬柴,你爹和他四叔四婶娘,死死扯到我,不准我搬,我就一边骂一边把你爹夹的壁板撤了几块,给你娘杀炖鸡。哼,你娘鸡肉喰完了,把这些苦全部忘了!
讲完,舅娘眼泪双抛,悲伤难抑。
娘也抹着眼泪讲:我米有忘,那些苦,是我各人熬的、受的,哪门(怎么)会忘?只是那些苦过去了就过去了,人不能各人把各人泡在苦水里天天去想,越想就越不过味。上一代人是上一代的人,只要他们对学明好,那些苦喰了也值了。
舅舅舅娘不再说话,看着我。
我经不住对故乡的好奇和诱惑,在娘的再三劝说下,回到了那个模糊而久远的出生地——熬溪。
当娘站在小山腰,指着一片村庄讲这就是熬溪时,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蹲在地上,呜咽抽泣。——家啊!我终于见到你了!
十八年,我在他乡异地从没流过眼泪,哪怕再大的委屈,我都没有流过眼泪。那些苦难和委屈,早就变成了坚强的骨头,支撑我生命的历程。可是,当我踏进故乡的土地,看到故乡的瓦房和炊烟时,我的泪居然决堤似地奔涌出来,怎么都控制不住。故乡,是可以让游子尽情流泪和安放悲伤的地方。
我出生时远走他乡的第一滴泪,漂泊了很久,落回了故乡。
夕阳在故乡的天空烧着。红色的云,不是一块一块、一朵一朵,而是很长很宽的一溜,像是某个画师拖着狼豪泼的浓墨。确切地讲,应该是胭脂。凝固的胭脂。而天空,依旧如洗的蓝。红色的胭脂,恰如蓝天的一抹口红。一只鹰舒展着双臂,在故乡上空低低地盘旋。这是故乡的主人还是远方的来客呢?它飞翔的姿势,为什么如此潇洒和优
雅?那条劈开山丘的公路,从故乡的腰边穿过,把故乡的两个小寨挑在肩头。肩的这头是我出生的那个寨子,肩的那头是另外一个寨子。两个寨子之间,是一坝田园。几堆满含柔情蜜意的稻草垛,像蹲在田边解手的妇人;满田齐刷刷的稻草桩子,像是男人刚理的板寸。有一群鸭。有一群鸡。还有几只猪和狗。都闲来无事,跑到田里打牙祭。
我迫不及待地穿过几丛竹林,寻找我记忆中的那棵古树和那口古井。那棵高大的枫香树早已被砍掉,荡然无存了。我看不到华冠入云,看不到红叶满地,更看不到深埋大地的根。那口古井却依然丰沛地流淌着故乡的乳汁和甘甜,哺育着故乡的乡亲和万物。我捧起井水一口又一口地喝、一把又一把地洗,让故乡把我从身到心,浇灌,沐浴。一
条背井离乡的鱼,游了千山万水,今天终于游回生命的源头。
我回乡的消息,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传遍了。整个寨子的人,不管是不是家务堂和亲戚,都迈开喜悦的脚板赶到我哥屋里,来看我这个离开了十八年的孩子。甚至别个寨子的人,也远天远地赶来,看过究竟。
一连几天,哥屋都过年娶亲似的,人来人往,喜气洋洋。就连故乡的鸡和狗都不断跑来,给我讲着土话和乡音。
一个寨子的鸡鸭鱼肉和禽蛋,全摆在了桌上,迎接我这个离家十八年的亲人。
亲人们得知我成绩一直全校第一,高考只差一分,一致同意斗(一起凑)钱让我补习。这天大的好消息,的确是我阴沉沉的人生里一抹最亲的亮光。仿佛高高的云端里,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正上下翻飞着,飘落。
哥和大家旧事重提,希望我把户口迁回熬溪,跟他们在一起。我想起小时候我们母子三人被人欺负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帮忙时,我就答应了。一下子有了这么大一个家务堂和这么多的亲戚,哪个还敢再欺负我们呢?
我平生第一次有了靠山的感觉。
可是,当村委会把这件事交给全体村民讨论时,嫂子的娘家人坚决反对。他们只同意把我一个人的户口迁回熬溪分田分土,不同意娘和妹的户口迁回熬溪分田分土。借口是我是熬溪出生的,娘和妹不是。
我一听,不高兴了。我尽管恨娘、埋怨娘,可我从没想过要抛弃娘。我怎么能抛弃含辛茹苦养育我十八年的娘而独自回到老家呢?那我成什么了?瓦孔雀?还是白眼狼?
瓦孔雀是我们湘西特有的一种鸟,不知学名叫什么,全身灰扑扑的,像瓦的颜色,所以叫瓦孔雀。传说瓦孔雀长大后是吃娘肉的。我脾气再暴躁,良心再坏,也不至于坏到瓦孔雀吃娘肉的地步,也不会是一只没有人性的瓦空雀和白眼狼。
我断然拒绝了哥和乡亲们的好意,回到了娘的身边。
没有泥土就没有大地,没有石头就没有高山,没有母亲哪会有我?
没有母亲的故乡,那不叫故乡。
我青春的梦想,的确就像人生的一节彩虹,转瞬即逝。
当娘听我讲我不愿做瓦孔雀和白眼狼时,躲在一角,喜极而泣。
十八年的千辛万苦,换回儿的这一句话,就够了。
命里注定,儿与娘,是前世今生都无法分割的骨肉。
【选读完】
本文选自彭学明长篇纪实散文《娘》第20章
作者:彭学明,土家族,湖南湘西人。著名学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全国第九届人大代表、全国第十届人大代表。多次任茅盾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五个一工程”奖评委。主要代表作有轰动全国的长篇纪实散文《娘》及散文集《我的湘西》《祖先歌舞》等。
来源:收获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