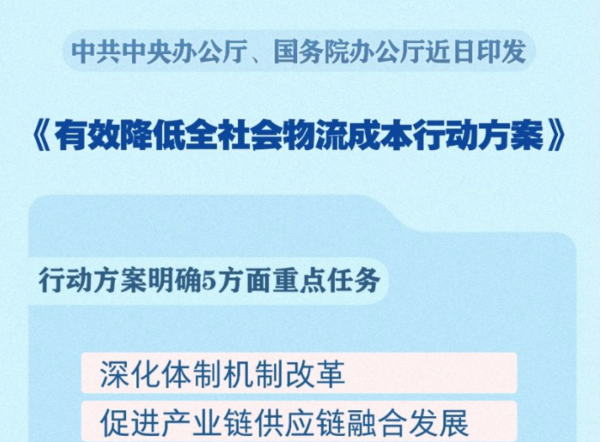一
民国十三年,我太叔爷贺恺年病逝了,享年四十四岁。他患的是肝病,曾四处求医,但始终无法治愈。据说死时很痛苦,腹水把肚子胀得很高,像个孕妇似的。后来,从上海请来一位德国医生为他抽掉腹水,并用鸦片来减轻痛苦,这才好受点。
贺恺年一生有过辉煌,也见过大世面。他早年投军,出生入死,吃过不少苦,后来解甲归田,经营实业,富甲一方,是《霍川县志》上记载过的名人。虽然他早年与我太爷爷失和,但看在亲兄弟的面上,县太爷秦尚义家灭门案发生后,他施以援手,一心想把我太爷爷救出来,可结果并未如愿,这也导致他后来与卫家翻脸,结下了几代冤仇。
灭门案发生后,贺恺年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卫孝衡。“这事八成与他有关。” 他当时就有这样的预感。
当然,这种预感不是无缘无故的。霍川新政开始后,私盐贩卖受到严厉打击,而卫家首当其冲,遭受重创。不仅如此,卫孝衡的外甥白小虎也被开刀问斩。用卫孝衡的话说,姓秦的把事情做绝了。按照他大魔王的脾气,岂能善罢甘休?因此,灭门案一出,贺恺年马上就想到了他。为此,他特地去了一次卫家埠。与其说是想证实这件事,不如说是想排除这件事。“俺真不希望是他干的。”贺恺年私下里曾对人这样说。
卫家埠离大贺村七十余里地,贺恺年到达时已近正午,正赶上饭点。卫家热闹非凡,欢声笑语。新年将至,前来送礼的人挤满了院子和前厅。各路生意伙伴和大小头目蜂拥而至。肩挑车拉的礼品堆积如山。各色人等,进进出出。厅屋里已摆出十几桌酒宴。仆佣们忙忙碌碌地张罗着、照应着,人声沸腾,一片喜庆。
卫孝衡的情绪很好,在众人簇拥下,有说有笑地招呼客人。见到贺恺年,卫孝衡便向他招手,让他在客厅里坐下喝茶。贺恺年也带来了年礼。每年他们两家都要互赠礼品,这已成了多年的惯例。吃了一杯茶,叙了几句闲话,由于客人多,有些话不便说,贺恺年瞅准一个空子,便把卫孝衡拉进书房,问起秦府的事。
“啥事啊?”卫孝衡起先还装聋作哑。“你难道没听说?”贺恺年道,“秦家被灭门了!”
“哦,你说那事啊?”卫孝衡表情淡淡的,一副恍然醒悟的样子。贺恺年对他的反应感到有些奇怪:这么大的事他居然一点不在乎?“听说一家十七口全杀了。”他接着又说。
“活该!”卫孝衡这时朝地上啐了一口,“这个王八蛋也有今天,真是老天开眼啊!”他一边说一边大骂起来。
贺恺年说:“四哥,话不能这么说,不论咋说,这事做得有些过了。”
“有啥过的?死得好!”卫孝衡一跺脚,又骂了起来,说姓秦的坏事做绝,他来了之后好事不做,处处和俺作对,连小虎也不放过。“他娘的,”他说,“他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老子恨不能扒了他的皮。”
卫孝衡的态度让贺恺年半天无语。难道这事真是他干的?他心里想着,等到卫孝衡骂完了才开口道:“大哥,俺知道你心里有气,今日小弟来有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啥事?”
“这事……”他迟疑了一下,说,“俺是说,这事和你没关系吧?”
卫孝衡一听这话,愣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贺恺年,忽然仰起脖颈,哈哈大笑起来。“咋了?你啥意思啊?”他说。
贺恺年说:“俺只是有点担心。”
“你是怀疑俺?”
“这倒不是。”
“那是啥?”卫孝衡说完这话,突然瞪起眼睛,勃然大怒。“别和俺来这个!”他说,“俺问你,你还是不是俺兄弟?”
“当然是。”
“可俺看你屁股早坐偏了,不像是俺的兄弟,倒更像是那姓秦的兄弟!”
“四哥,你咋这样说?”
“俺说错了吗?自从姓秦的来了,你就一直在帮他说话。现在竟怀疑到你大哥头上,难道姓秦的不该死吗?这都是他自找的!”
谈话进行不下去了。这时,外边有人来催促开席了。他们便一起走了出去。这顿饭,贺恺年吃得索然无味。席间,众人推杯换盏,十分热闹。尽管卫孝衡一如既往,与他频频碰杯,但两人都显得有些不大自在。
当晚住下,直到次日吃早餐时,卫孝衡才又重提昨日的话题。“老弟啊,”他说,“大哥脾气不好,你可别往心里去。”卫孝衡是专门来陪贺恺年吃早餐的,屋子里就他们两个人。提起秦尚义,他又大骂起来:“这个姓秦的,不是个好鸟,你看他来了之后都干了啥事?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当他是谁啊?还和老子叫板?俺卫孝衡在霍川地界上可不是好欺侮的。”骂了一阵之后,他话题一转,又说老弟你别担心,你大哥可不傻,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自然是心中有数,说着,还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
卫孝衡的这番话虽未明说,但实际上撇清了自己。从卫家埠回来,贺恺年心里多少有些释然。“也许真不是他干的,”贺恺年当时心里想,“新政得罪的人可不少,想杀秦尚义的也不是他一人。”及至我太爷爷被抓,从他那里得知,凶手中有一个人很像白团总时,心里便扑通一下,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
白团总名叫白立贵,土匪出身。他是霍川三里店人,早年因抢劫杀人,负案在逃,后上大牯岭当土匪,绰号“老洋人”,因其长得鹰鼻凹眼,满头鬈发,故而得名。白立贵上山之初,由于心狠手辣,一度深得山寨老大刁狗子的信任,但他色胆包天,居然勾搭刁狗子的女人,事发恐惧,遂生异志,于是配合官府,里应外合,将大牯岭匪巢一锅端掉,立下一功。此后,他投靠卫孝衡,得到重用。当时,霍川私盐贩子分成几大帮派,相互明争暗斗,白立贵敢打敢杀,很快打出了名声。光绪二十八年,即灭门案发生的前一年,他当上了新成立的霍川商会民团团总。
这当然是卫孝衡一手提携的结果。因此,当我太爷爷提到白团总时,贺恺年马上联想到卫孝衡。“他没和俺说真话!”他心里当时就这样想,并立即叮嘱我太爷爷把话放进肚里,千万不能说出去。应该说,他很担心这一点。凭他对卫孝衡的了解,这事如果让他知道了,他决不会放过,但只要我太爷爷不露口风,也许就会无事。即便退一万步,不看僧面看佛面,卫孝衡也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因为毕竟贺继年是他贺恺年的亲兄弟啊。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太爷爷还是未能逃脱一死。
这一来,贺恺年无法容忍了。在我太爷爷死讯传来的第二天,他便去找卫孝衡了。当时,卫孝衡正在商会议事厅与人议事,看到贺恺年他还笑嘻嘻地打招呼,并唤人泡茶来吃,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俺哥死了?”贺恺年劈头就问,“你听说了吗?”
“啥的?”他挑起眉头看了贺恺年一眼,“这是咋弄的吗?咋会出这种事?”他一边说,一边还咂着嘴巴,好像十分惊讶。其实,这事早已传遍了全城,卫孝衡不可能不知道。“你难道没听说?”贺恺年说,“这太奇怪了!”
贺恺年话中有话,卫孝衡当然听出来了,但他依然故作镇静。“老弟,你啥意思嘛!”他说。
“你心里明白。”
“明白啥?”
“俺要你说实话,这是谁干的?”
卫孝衡听了这话便坐不住了。“你这是啥话吗?”他说,“难道你是怀疑俺?他娘的,这和老子有屁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俺会查清楚。”
“你疯了!”
“俺可没疯,”贺恺年道,“疯的是你。俺一直相信你,把你当兄弟待,可你连俺哥也不放过。”说到这里,我太叔爷十分痛苦,“你哪还讲一点兄弟情谊?俺明说了吧,你不用抵赖,这事再明白不过了。还有秦家的案子,你也脱不了干系!等着瞧吧,这事没完!”
卫孝衡勃然大怒,说你血口喷人。两人大吵起来,彻底翻了脸。卫孝衡说俺没你这个兄弟,贺恺年也割袍断义,与他誓不两立。
打这,贺恺年开始四处查访,下决心要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据家族的老人说,我太叔爷办事向来有股子狠劲,不办则已,一办就不惜代价,非办出个名堂来不可。
果然,他的查访没有白费工夫,半年后有了线索。
在我太爷爷冤死的那一年的六月,贺恺年终于在英山县抓到了那个潜逃的牢子。该牢子姓陈,名不详。据他交代,是白立贵授意让他下毒,害死我太爷爷,收受“贿银三十两”(县志语)。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白立贵的嫌疑进一步上升。如果说我太爷爷那天晚上看得不清楚,无法确认凶手的身份,但从白立贵指使陈某下毒看,反倒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据家谱记载,贺恺年抓到“陈某”后,便将人犯秘密押至甘露寺。该寺位于北门附近,原为一处寺庙,后改为驿站,人们仍习惯地称其为甘露寺。当时负责查办灭门案的钦差大人陆景芙就驻扎此处。
灭门案发后,朝野震惊。这种野蛮地杀害朝廷命官,且手段之残忍,实属罕见。谕旨严查,各级衙门层层督办。春节过后,一应查办工作迅速展开,各路大员先后驾到。钦差大人陆景芙也驾临霍川,亲自坐镇。陆景芙时任刑部侍郎,是着名的能吏,娴于刑案,且公正廉明。早年曾在天津办过洋务,热衷于求新图变。秦尚义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当年他去霍川任职也是由他力荐。对于霍川新政,他全力支持,充满期待。然而,没想到功业未成身先死,这让他极为愤慨,痛心疾首,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彻查此案,严惩凶犯。他强烈谴责凶犯的暴行,认为此案极为恶劣,是目无法纪,公然对抗新政,其手段之残忍,为国朝所未见,必须严查不怠,以正视听。他还主动请缨前往霍川,在将近半年多的时间里,废寝忘食,事必躬亲,勘查现场,阅卷查访,对于案件的每条线索、每个证据、每个细节,以至于每个疑点,都像过筛子似的不知过了多少遍,能查的都查了,能找的都找了。他还走访了当地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尽管如此,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案卷堆积如山,但却毫无进展。
陆景芙非常焦急。就在他苦于无计可施之时,贺恺年抓住了陈某,这让他大喜过望。当晚便进行了提讯,并录下口供。为了谨慎起见,他避开当地衙门,特地从颍州府巡防营调来一队人马,实施抓捕行动。
行动开始后,按照事前的布置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商会民团驻地,实施布控;一路则包围了梦云馆。根据可靠情报,白立贵当晚就在这家妓院里与苏州新来的花紫云厮混。花紫云是姑苏名妓,芳龄二八,不仅姿色过人,而且技艺超群,弹得一手好琵琶。白立贵迷上了她,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晚上都在这里过夜。
这天晚上,他邀来一帮狐朋狗友,正在梦云馆吃花酒,由花紫云弹琴助兴。巡防营突然出现,他吃了一惊。因为事先没有听到任何风声,而这些穿着巡防营制服的陌生面孔以前也从没见过,心里不免敲起小鼓,但表面上依然满不在乎,拿着势子说:“咋啦?咋啦?俺可是民团团总,你们是何人?敢到这里撒野!”酒桌上的人也都附和起来,七嘴八舌地鼓噪道,这可是俺们白团总,你们可别乱来啊。
领头的队官是个身材壮实的汉子,胡子拉碴,不修边幅,一看就是个老兵油子。他黑着脸,二话没说,掏出枪,便朝天放了一枪——砰的一声,众人都吓住了。白立贵一看对方来势不小,连忙脸上堆笑,连说别误会,这事四爷知道吗?他说的四爷就是商会会长卫孝衡,他本想亮出这个旗号,镇住对方。哪知对方根本不买账。“什么狗屁的四爷五爷?”那个队官说,“老子是奉钦差大人之令。走,快跟我们走。”
一提到钦差大人,白立贵心里便扑通了一下——糟了!这八成是冲着灭门案来的!他心里慌作一团,同时也打定主意,决不能跟他们走,否则那就死定了。于是说:“有话好说,好说。”一边应承着,一边装作要穿衣服,退到床边——他的枪套就挂在床头——上前一把摘下,迅速掏出枪。“都别动!”他转过身来喝道。
在场的官兵一愣,随即向后一退,接着便都端起枪。屋里噼里啪啦响起一阵拉枪栓的声音,领头的队官喝令白立贵放下枪。
“放下,快放下!”
白立贵眼珠快速转动着,迟疑不决。那队官又喊道:“再不老实,老子就要开枪了。”这句话仿佛提醒了白立贵,他马上扣动扳机,胡乱地开了几枪,屋子里一下子乱了。人们四处乱跑乱躲。白立贵乘机从后窗跳入院子,想从那里脱身。但院子里早已布下兵丁,立时一片呐喊抓人。
白立贵见势不妙,一边开枪顽抗,一边踅身上楼。兵丁们这时也都开起枪来。白立贵连滚带爬,钻进楼梯口的一间房子。这时整个梦云馆已被团团围住。枪子打得叭叭响,门窗上灰土木屑乱飞。楼下有人喊话,要他投降,可白立贵死也不肯。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白立贵希望拖延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民团驻地离这不远,听到枪声会很快赶到。可是打了半个多时辰,民团连半点影儿也不见,最后子弹也打完了。白立贵彻底绝望了,最后只好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当巡防营的兵丁冲进房间时,只见他仰面倒在地上,手枪扔在一边,额头上的血已经凝固了,像糖浆似的挂在半边脸上。
白立贵一死,最后的一点线索又断了。虽然卫孝衡的嫌疑很大,但没有证据,陆景芙也束手无策。他一度抓了卫孝衡,却审不出半点头绪。卫孝衡一口咬定,他是清白的,与此案毫无关系,加之卫家频繁活动,动用各种关系,游说于督抚和京中权贵之间,陆景芙迫于压力只好放人。
随后,此案搁置,不了了之,但卫、贺两家的仇冤却进一步加深了。卫孝衡与贺恺年从此你死我活,处处针锋相对。后来发展下去,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次,贺恺年的马车被人放了炸弹,炸得四分五裂,连马和马车夫都炸死了。多亏他人不在车内,否则性命难保。再后来,卫孝衡也遭到了伏击,马车被打得像筛子似的,不是他跑得快,小命也早玩完了。
这些事件发生后,一度引发了恐慌。但究竟是谁干的,始终无人承认,卫家不承认,贺家也不承认。但毫无疑问,这样下去对谁也没有好处,不仅卫、贺两家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对地方治安亦不利。当时霍川县令是费经三。出于稳定地方的需要,他出面邀请当地头面人物进行斡旋,并亲自登门,分别前往卫家埠和贺老圩说服卫孝衡和贺恺年,终于把双方拉到一起,在地方大佬们的见证下达成协议,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包括贺恺年和卫孝衡遭袭之事,一概既往不咎,从今往后各方严加克制,井水不犯河水。
就这样,几年过去,卫、贺两家都信守承诺,倒也相安无事。直到宣统三年才又起波折。
二
宣统三年夏季,霍川附近的几个县连降大雨。大雨持续下了半个多月,听说淮河又决堤了,许多地方都被淹没,霍川城里也到处都是逃荒的灾民。有人预言,天象示警,要出大乱子。果然,到了秋天,天下就大乱起来。
这一年的阴历八月,寒露过后不久,有人从城里带回了消息,说是武昌革命党造反了,撵跑了巡抚大人,把武昌城也给占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有人从省城回来,说安庆也闹起来了,革命党架起大炮朝城门楼上轰轰直放,黑烟冒起几丈高。“乖乖,俺的娘,那可是动真格的啊!”有人咂起嘴巴说,一副既惊讶又不安的样子。
不久,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传来了,说是革命党朝霍川开过来了。城里的头面人物都紧张起来,聚在县衙里开起会来。出席会议的有政界、军界人物,还有地方士绅贤达。会议由知县费经三召集,守备大人也来了。众人都对眼前的局面一筹莫展。守备大人绰号“杨大嘴”,平时耀武扬威,吆五喝六,这时也蔫了。外界有传言说,他已派兵在夜间偷偷押运车辆向老家转移财产。会议开始后,谁也不说话,大家各怀心事,互相观望。费经三请杨大嘴先发言,这既是出于礼节,也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杨大嘴连声说道:“俺,俺(这是他的口头禅),这可是民变啊,民变啊……”他咕哝了半天,谁也没听懂他的话是啥意思。
杨大嘴在当地职务最高,而且他还掌握着军队。除了驻防绿营外,从省城调来的一个巡防营,约三百人,也归他节制。从隶属上,他归巡抚调遣,平时并不把州县一级的官员放在眼里。如今,省城早乱了,他连续致电请示方略,但都没有得到回复,一时也慌了神,没了主意。
杨大嘴态度不明,别人也不好表态。说打吧,兵力明显不足;说不打吧,这话谁也不敢轻易出口,因为这不啻是背叛朝廷啊。会议僵持了半天。费经三有些急了,他睃巡了一下会场,目光最后落到了卫孝衡的身上。
“四爷,你是商会会长,德高望重,请您老先说两句吧?”他说。但卫孝衡听了却摇起头来。“采臣兄,”他说,“你是父母官,还是请你先拿个主意吧。”他一脚把球踢了回来,显然不想出这个头。
费经三被他将了一军,表情有些尴尬,连忙推托说自己是晚生,还是先听听各位的高见。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二爷不知是啥主张?”
“是啊。”
“要么二爷先说说?”
有人附和道。
二爷是人们对我太叔爷贺恺年的尊称。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尊他二爷。听到有人这样说,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贺恺年。贺恺年进入会场后,一直没有说话。由于肝病发作,他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这次会议原本不想参加,但架不住费经三反复敦请,说是事关重大,务请发驾,他才抱病前来。但在这种场合,他同样不想抢先表态。因为形势并不明朗,还是谨慎为好。“不了,”他皱起眉头,摆摆手,“还是诸位先说,俺还是先听听诸位的。”
大家都推来推去,谁也不肯先开口,一时间僵在了那里。如果照这样下去,到了晚上也议不出个名堂来。费经三无奈,只好说:“今天诸位都到了,大家都得说一说,就从这边开始吧。”他把手朝右边一指,正好指到我太叔爷。
县衙的议事厅,按座次,守备等官员都坐上首,卫孝衡是商会会长,也坐上首。下首右起第一个座位即是我太叔爷。费经三这样提议,表面看好像是无意的,实则却是有心。在开会前,他曾与我太叔爷通过气,知他主张和平解决,这一点与他不谋而合,因此他希望我太叔爷能够带头表态,起引导作用。我太叔爷尽管有些不大情愿,但见推托不掉,只好从命。贺恺年的发言讲了十多分钟,先从全国大势讲起,又讲到省里和县里,内容大体是:眼下革命党声势浩大,各地纷纷光复响应。如今大兵压境,霍川兵力单薄,势难抗拒。一旦动起兵戈,必定生灵涂炭。最后归结到一点:霍川乃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何忍糜烂地方?因此避免兵燹之祸,乃为上策。
他的话一说完,会场气氛便热烈起来,与会者纷纷附和。
“说得是哩,最好是别打。”
“这些革命党可不好惹,省城都守不住,何况小小的霍川?”
“可不是。”
“战火一开,生灵涂炭,枪子可不长眼啊。”
大家七嘴八舌,主和意见很快占了上风。费经三频频颔首,乐见这个局面。接下去,又有几个人发言,除了少数人,指责乱党谋反祸国外,大多数人均主张以和为主。一个小时后,大家的发言都结束了,这时轮到卫孝衡了。对于他的态度,费经三也拿不准。按照以往,卫、贺两家一向是唱反调的。卫家赞成的,贺家反对;贺家赞成的,卫家反对,总之是相互对着干。费经三也有些紧张,担心他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让他意外的是,这一次卫孝衡居然没反对。他说这样很好,只要能避免战火,他举双手赞同。还说打不赢,还打它干吗?这不是祸害地方吗?对谁也没有好处啊。
他的话音一落,费经三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霍川两大实力人物都已表明态度,剩下的就看杨大嘴了。他转过脸来征求他的意见。哪知杨大嘴一开口又是几句脏话。“这是要投降吗?”他说,“俺,革命党还没来,就一个个包了吗?”
他这样一说,众人全都哑了口。毕竟杨大嘴手握兵权,他要打别人谁也拦不住,如果他恼了,再要给大家扣个背叛朝廷的罪名,那麻烦就大了。费经三赶紧解释说:“杨大人千万别误会,这不是在商讨吗?谁也没说要投降啊。”
杨大嘴说:“老子深受皇恩,守土有责……俺,老子食君禄,忠君事,不能乱党来了,就装孬啊?”
“那是,那是,”费经三附和道,“那依杨大人之意,这是要打吗?”
杨大嘴又说:“打?怎么打?这可不好打!这是民变啊,民变啊……”他不知所云,没头没脑地咕哝着,让人哭笑不得。
会议开了半天,并无结果。不过,费经三心里已经有底了,因为大多数人都拥护和平光复,特别是卫、贺两家均已表态,这就好办了。
第二天,他又召集了一次会议。这一次,与会人数大为减少。不仅杨大嘴被排除在外,而且只有少数可靠的人被邀请到会,其中包括卫孝衡、贺恺年。
会议开得相当顺利,一致通过了费经三提出的响应革命、和平光复计划,决定接受革命党的条件,并成立一个过渡性的机构——霍川临时军政府,推举费经三为都督兼民政长,卫孝衡为副都督兼城防司令,贺恺年为参议长,此外还有参谋长、秘书长、安抚长、监军等一应人事均做了安排。起义主力以商会民团为骨干,加之各地乡团武装。为了对付驻防的绿营和巡防营,大家具体分工,利用各种关系,包括金钱收买等手段,说服瓦解,各个击破。
关于霍川光复,留下了不少文史资料。一九八一年纪念辛亥革命爆发七十周年之际,县政协还专门出版过一本专辑。从有关文章看,霍川光复,费经三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贺恺年和卫孝衡也功不可没。特别是在策反巡防营上,卫孝衡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时,和平光复的一大障碍是巡防营的态度。霍川的驻军以绿营为主,他们驻霍多年,与地方关系较熟,费经三通过工作,或收买,或说服,很快就取得成效,许多军官都表示愿意弃暗投明,积极配合,但是巡防营态度始终不明。这支部队刚从省城调来,旨在加强当地防务。其兵力最强,人数也最多,一律配备套筒毛瑟枪,武器装备也最好。如果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使和平光复存在变数。
费经三颇感头痛,便请卫孝衡帮忙。后者一口答应。有文章称,巡防营的金管带与卫孝衡相识,因其父是卫孝衡的拜把兄弟,一直对他以世叔相称。巡防营调防霍川后,他经常去卫家埠走动。卫孝衡虽是枭雄人物,但他还算明事理,看到清王朝大势已去,便决定响应光复,答应说服金管带,促使该营归顺。
十一月中旬,就在革命党逼近霍川的前一夜,从各地抽调的乡团武装(包括联防队)和商会民团等近千人开进城内,以白布为旗,臂缠白巾,密发口令,分成五路,分别接管四个城门,其中一路镇守县衙。绿营和巡防营均按兵不动。原以为守备杨大嘴会负隅顽抗,没想到在这前一天,他已弃城而逃。几乎没费一枪一弹,霍川便和平光复。次日上午,革命军开进了霍川城。
就在这当口,卫孝衡忽然被抓了。
三
抓捕卫孝衡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爷爷。霍川光复时,我爷爷担任革命军先遣队司令,正带队从庐州出发,一路向霍川开进。到达六安时,费经三便派人前来接洽,表示霍川决定响应光复,恭迎革命军进城接收。
我爷爷接到信后,便加快了前进速度。两天后,抵达五里庙,远远地看到迎接的队伍。这是费经三安排好的。他和我爷爷确定了进城的日期,便组织好欢迎仪式,同时委派副都督兼城防司令卫孝衡前往五里庙迎接,自己则亲率临时军政府一干人员在城门口恭候。
据县志记载,革命军抵达那天天气很好,尽管前天夜里刚降了雨雪,第二天却云开日出,晴空万里。我爷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全副武装的革命军雄赳赳地一路开来。道路两旁老百姓兴高采烈,夹道欢迎。县志上有“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之语,场面极为热烈。但在五里庙,当他看到卫孝衡后脸便垮了下来,当即下令将他抓了起来。
消息传来,费经三吓了一大跳。
“这是咋回事?”
“不清楚。”来人报告说。
“谁抓的?”
“革命军的贺司令。”
及至革命军进了城,费经三才搞清楚,革命军的贺司令就是我爷爷、大贺村的贺文贤,
其父贺继年、其叔贺恺年。
这下麻烦大了!
早知如此,他根本不该派卫孝衡去迎接。
可事到如此,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得好言与我爷爷商量。“抓不得啊,”他把我爷爷请到县衙说,“卫孝衡抓不得啊。”
“为啥啊?”我爷爷说,“他是杀人犯,过去抓不得,现在还抓不得吗?”
“不,不,你听俺说,”费经三笑道,“卫孝衡如今是临时军政府的副都督、城防司令,如何抓得?”我爷爷一听便火不打一处来。“简直是乱弹琴!”他说,“这不是胡搞吗?”他一甩马鞭,抽在皮靴上,发出啪的一声响,“这种坏蛋,双手沾满鲜血,早该杀头治罪,你们咋搞得是非不分?革命政府就得有革命政府的样子,你们这样搞与满清何异?又何以服众?”
费经三连忙解释说:“贺司令,事情是这样的,卫孝衡光复有功,他是众人推举出来的。”他把光复的前后经过简述了一下,接着又说,“军政府名单都公布了,这个时候抓人岂不乱了套?你让俺咋对外边说?”
“有啥不好说的?”我爷爷反驳道,“你就如实说吧,这个恶霸地头蛇早该除了!”
费经三说了半天,毫无效果,顿时一筹莫展。“那你打算咋办?”他指的是如何处置卫孝衡。我爷爷说:“公审!枪决!”
这一下,费经三更着急了。霍川灭门案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其后我太爷爷死于狱中,卫孝衡嫌疑很大,这些均系事实,但问题是桥归桥,路归路,卫孝衡千不是,万不是,但他对光复有功,如在这个节骨眼上杀了他,岂不成了言而无信,诛杀功臣?作为一县之主,他今后如何面对卫家,又如何向各方交代?
费经三急得手足无措,当即派人紧急赶往颍州。据《霍川辛亥史料》记载,霍川光复前,革命军曾派人与费经三联系,策反倒戈。具体负责这事的就是革命党人郑先滔。他时任革命军入皖部队联络员。他在北辰书院时就与费经三相识。在策反费经三时,他向他承诺,只要响应光复,所有人士均可赦免,有功者还可奖赏。当时,郑先滔正在颍州一带指挥作战,费经三无奈只能派人向他求救。郑先滔得知消息后,连夜起草了一封信。在信中,郑先滔要我爷爷立即放人,并说明当前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推翻清帝,建立共和国家。凡是赞成者,皆为盟友。就连袁世凯,我们也要争取,何况卫孝衡呢?他还告诉我爷爷,眼下局势大好,但反革命仍很强大。朝廷已重新起用袁世凯,并派北洋军大举南下,我们更应联合各种力量。如果杀了卫孝衡就会破坏大局,甚至授人以柄。至于灭门案,相信革命胜利了,自有法律做出公正裁判。这封信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然而,就在这封信尚未送达时,卫孝衡已经被释放了。
原来,促成这件事的竟是我太叔爷。
卫孝衡被抓后,费经三在派人给郑先滔送信的同时,又派人去请我太叔爷出面斡旋。那天,贺恺年由于犯病,没有出席欢迎仪式和军政府成立大会。接到费经三的信,他倒没有耽搁,当即抱病前往城里。有笔记称,当时卫孝衡已被押赴刑场,三通鼓响,正要开刀问斩,贺恺年赶到了,大呼:“刀下留人!”这才救下了卫孝衡。
事实上,这些说法并不准确,都是后来有人添油加醋胡乱演绎而已。真实的情况是,我太叔爷赶到时,军政府成立大会刚结束。他把我爷爷单独找到会场边的一个茶馆里,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了一番话。谈话的要点大致有三:一是诛杀卫孝衡不利于光复大业;二是没有证据,难以服人;三是贺、卫两家既有协定在先,就不能随意破坏。他告诉我爷爷,当初接受费经三的调停,便是希望维持和平局面。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他不主张贺、卫两家再敌视下去。“该收手了。”他对我爷爷说,“斗来斗去,两败俱伤,何益之有?”
“那俺爹就白死了?这仇就不报了?”我爷爷似乎接受不了。
贺恺年叹了一口气。“如果你有证据,俺支持你办他,”他说,“如果你凭手中的权力,卫家能服吗?此一时,彼一时,有盛便有衰,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得势。如果这样纠缠下去,将永无宁日。”
我太叔爷说得句句在理,当天晚上,卫孝衡就被释放了。事实上,贺恺年这样做是正确的。据说,卫孝衡也大受感动,发誓不再与贺家为敌,从而维持了卫、贺两家二十多年的和平。直到他死后,两家再起风波,血腥杀戮,这已是后话。
作者简介:季宇,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省政府参事,一级作家。着有《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猎头》《当铺》《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等。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飞天奖、金鹰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和安徽社科文艺奖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