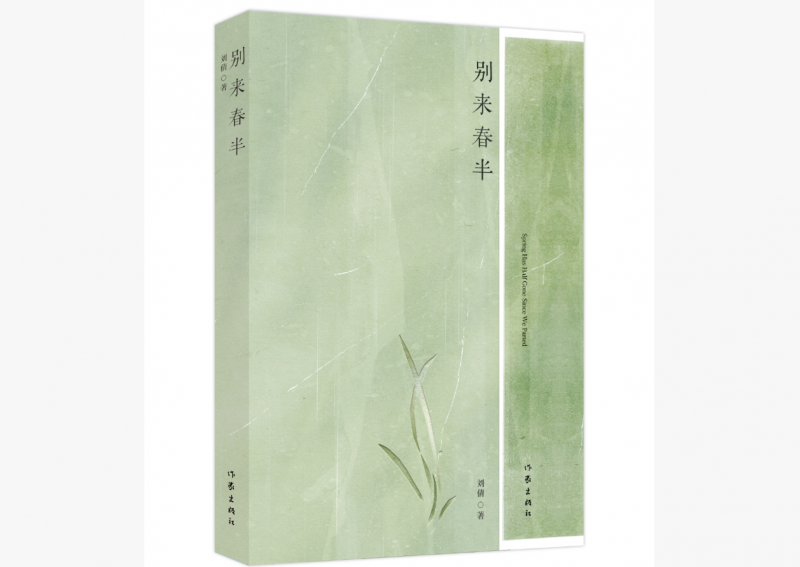之所以用“超越私人化写作”来形容刘倩的散文集《别来春半》,并不是从好与坏的层面上对刘倩的写作或者90年代女性私人化写作做出评判;相反,超出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刘倩的《别来春半》和林白、陈染的写作处于一种并轨又互相交织的状态,同中有异,恰如梅花斜逸枝头,别有一番美感。无论是《别来春半》中以中式美学作为法门书写的第一章“华语是乡愁的魂”,还是在异国他乡游历,充满着小布尔乔亚孤独情调的第二、三章,甚至是以读后小扎作为写作模式的第四章“文学的还魂”其实都是一种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是写他人的故事,但依旧有很深的自我内心的投射之感,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句经典言论来讲,这便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只有90年代女性私人化写作以至今时今日刘倩的写作这种将主体意识完满突出的文字,才是上述这句经典言论的最好注脚。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以少女多米的诡秘心事为引子,牵扯出了她表面平静无波,其实千疮百孔的内心成长历程;陈染的《私人生活》,以一种自卫式的态度来描写幼女倪拗拗的极度敏感多思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潜在对抗。刘倩的《别来春半》其实也是如此,在一篇篇散文化的小说中,她营造了一个个忽而像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世界,忽而又像是20世纪德国现实主义巨匠托马斯·曼《魔山》中像是暗流一般“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世界,但刘倩和上述私人化写作女作家最不同的是,她即使从不直接鞭劈现实生活,但已经以另一种委婉曲折的方式融入了现实,她是真正热爱生活的,用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
《别来春半》这本集子中,除了零星几篇长文,更多的是小札似的像是以归有光《项脊轩志》这样晚明小品文一般的文字,像是啜饮一杯单枞茶,满嘴清香,却也有细细品味才能得到的苦味,但汇总在一起,能看出这种梦幻般的苦与乐、哀与怨终究还是苦中作乐,即使在异国他乡上学,文字背后那个穿着素雅棉布衣裳的乌篷船中的女子依旧跃然纸上,她在缓缓地诉说心事,即使在有些小说中,她易容化妆,连绵曲折,但终究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氤氲之美倾泻而出。
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是《别来春半》第一章中的文字:《钗头凤》叙述了一个小和尚的私语情思,寺院生活气息和灵动的像是意识流般的思绪自然流动,颇得汪曾祺《受戒》遗风;《金陵1947》充满了大陆之外的漂泊美学,像是白先勇笔下《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披着一袭破旧的华服喁喁自语,充满着苍凉之美,就像对着煞白的墙做了一个苍凉的手势;在《夜香港1999》中,又是以黄碧云为代表的香港文学的路数,似乎是《扬眉女子》中的女主人公在刘倩的笔下再次得到了生命的延续,那种不经意的笔触,“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徐志摩《沙扬娜拉》)书写了多少自由的老灵魂。那些在最繁华都市的深夜中迎风起舞的女子,或许,她们不被世俗认可,但却是遗世独立的,她们即使不能进入宏大的历史中,但总有一湾小小的文学文字是容身之地;再如《秦淮八艳》杂忆这一令人潸然泪下的文字,刘倩总是具有一种解构历史的功力,总能在正史冰冷克制的叙述中找到鲜活的东西,找到那飞扬的“人味”。
文学是人学,这是亘古不变的文学理论,秦淮八艳中的每一个女子,一直以来受到诸如红颜祸水之类的污名,但前有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后就有刘倩的这篇锦绣华章,那一个个在历史尘埃中失去了光泽的女子,又一次次地绽放;而在《车站》《非典型差生》中,刘倩开始运用了除了传统中式美学的第二种写法,那是一种类似于阿城《孩子王》一般的写法,《孩子王》中的王胡给了乡村孩子们最大的呵护,希冀着她们能够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而这两篇中的老师和校园生活就像一颗蒙了尘的宝石,在《孩子王》的对立面寄托了刘倩严肃的哲思。
刘倩很钟情少年和青春之时这最美好的岁月,几乎在每一个文本中都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潜文本,《永远的十五岁》对应三毛的《雨季不再来》,《夜宴》对应电影《夜宴》,《时候》对应《牡丹亭》,《垓下歌》在内容上对应郭沫若、张爱玲和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在写法上又有《华胥引》的影子;但这绝对不等于说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刘倩在这些文本中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具有独属于她本人的厚重感。哪一个文本没有它背后的潜文本呢?只不过是代际传承和双生姐妹花的区别,恰似《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的背后是伍尔夫和杜拉斯。
在《跨越国境线的离散》和《孑然流浪在美国》这两章中,刘倩与文本中的“我”几乎重合,她善待世界,但世界并不给予她同样温暖的怀抱,但总是差强人意的。世界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需要不断去呵护,不断去爱抚,最为对抗世俗的私人化女作家陈染在如今也已经与世界和解,那个在年轻时候曾拿玩具手枪指着自己脑门的叛逆女作家也学会了爱这个世界,但她已经到了中年才明白这个道理;而在这一点上,刘倩是早慧的,即使生活有着这样那样烦心的咬啮似的小烦恼。
在《文学的还魂》中,看似是一篇篇观后感和读后感,却并不是这么简单,在游历和阅读纳兰容若、兰波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刘倩其实还是在书写生命。文学作品有着强烈的治愈人心的作用,在她的笔下,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无论生活的年代距离当今的远近,人类都有共同的悲欢;同样的,就像是林白和陈染,她们热爱杜拉斯和尤瑟纳尔等人的文字,今时今日,她们写下的文字绝对不是对于以往大师作品的重复,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篇文字都是属于她们自己的,恰如刘倩在《别来春半》这本书的尾声说道,“我想那些人间的孤独、痛苦与浪漫都是真的。它们困住了我流浪的心,悄声低语就是这里了——我向文学献出了我平庸但善良的灵魂,从此它开出了玫瑰的腹地。”我们有理由看这本具有强烈主体意识和女性意识的文字,在其中,我们会找到与他人和世界的连接点,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出口。
文/尹子仪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