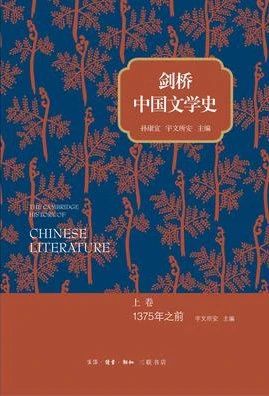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产生的一种文体,自问世以来,对其文体的特征及其认识判断,似乎一直有争议,历来诸家说法不一,难以确认。海内外有相当影响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在对赋这个文体的认识判断上,出现了前后四章之间阐述上的矛盾现象,令读者有些不知所从。
我们试先引述《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涉及赋的几段文字,略作对照比较,而后予以阐发。
该书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在全书中先谈到了赋——
对于秦、汉这两大新政权而言,石刻文与祭祀乐歌都是重要的政治、宗教表达,但汉代盛行的诗歌类型却是“赋”。西汉赋文类,最好是视之为一种“狂想曲”。“赋”这一文学术语,在早期中国共有三层涵义:一,用作动词,意为“诵”“陈”(如《左传》中的诵诗、赋诗);二,“赋比兴”之“赋”,是三种诗歌表现手法之一,最早见于《周礼》《诗大序》,后用于分析《诗经》文本;三,用作专门术语,指称汉赋这一文类。汉时的“赋”字,与很多其他同音字、近音字可以互换,这些字都有“展”“布”之意,将作为诗歌文类的赋与作为诗歌表现形式之一的“赋”联系起来。……所以,“赋”不仅指的是对相关主题的详细铺陈,更指的是其狂想曲式的呈现,后者即《汉书·艺文志》所谓的“不歌而颂谓之赋”。……“赋”这一文类的形式和内容,都没有得到明确界定。事实上,具有一定长度的诗歌文本均可称为“赋”,有时也称为“颂”“辞”。后世文献对“赋”做了进一步分类,如《离骚》传统中的“骚”“吊文”、七段文字组成的“七”、对话体的“设论”(又名“对文”)。这些术语,西汉以后很快便用作文类名,如仅东汉时期就有以“七”为名的赋作十三篇。
……
除了主要与南方文学传统有关的短歌以外,西汉“赋”涵盖了诗歌所有的形式、主题:既有贾谊的四言哲思《鵩鸟赋》,又有董仲舒自伤怀抱的《士不遇赋》;既有司马相如(前179-约前117)夸炫皇家园林的《天子游猎赋》,又有枚皋(约前130-前110)为取悦皇帝而作的即兴篇章;既有王褒(卒于前61年)《洞箫赋》这样的品物赋,又有扬雄等人专主道德训诫的赋作。
西汉赋与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传统确有关联,但其真正源头却是战国末年的修辞炫技与政治说服。汉初推动辞赋创作的不是中央朝廷,而是南方诸藩国。……相应地,当时最杰出的两位文体家是枚乘(枚皋之父,卒于前140年)、司马相如,而他们的语言与想象力也都无疑具有《楚辞》中所体现的那种南方特色。
这并不是说,除了赋与祭祀乐歌之外,西汉无诗。
《剑桥中国文学史》,[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从以上所引可知,《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章认为,赋就是诗——“具有一定长度的诗歌文本均可称为‘诗’”,“西汉‘赋’涵盖了诗歌所有的形式、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引的文字,均在第一章的第十一部分——“早期帝国的诗歌”内容之中,在作者看来,赋显然属于诗歌范畴之内,因而涉及赋的文字,都在标题为“诗歌”的阐述部分。
然而,该书第二章“东汉至西晋(25—317)”中的阐述就不一样了——
……或许是这一时期,班固创作了他的《两都赋》。班固自认此赋相当重要,故而为之撰写了序言;在序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赋史及其功能的看法。《两都赋序》首行,班固断言赋这一文体乃“古诗之流”。班固对于赋的这一界定,或许源于视赋为《诗经》“六义”之一的阐释传统。不过,作为“六义”之一的赋,并不是文学文体的名称,而是指一种诵、作的技巧,与不受比喻或修辞夸饰的羁绊而直接铺陈有关。班固将这种意义上的赋,引申为指称《诗经》中的一种既有文体。其时,班固尚未明确区分作为诗歌手法的赋与作为文学体裁的赋;并且,事实上,赋这一体裁本身的特征,极易使得汉代经学家将赋界定为一种直接铺陈的诗歌手法。……《两都赋序》中有一段文字,简短回顾了赋的文体史,班固认为,赋首先是一种颂美文体,其主要功能是礼赞汉帝国的光荣与强盛。
以上文字的引述,在第二章第一部分“东汉文学(下)班氏家族及其同时代人”的内容中。而该章这一部分,还有专节阐述“东汉的诗歌”,显而易见,撰写此章的作者认为,赋并不在诗歌范围之内。上引文字所探讨的,乃是赋文体的特殊性——它似乎既非诗歌,也非文章。
再看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317—649)”和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中的文字——
相对诗歌而言,文章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除了奏表、檄文或为著名人物写作的铭诔这些公众形式之外,赋这一传统文体继续保持着它的重要性,并在东晋的王朝建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
史书倾向于收录散文类作品,比如诏令、书信(包括奏表)、檄、论,甚至赋,但不倾向收录诗歌。
诗歌是最常见的文学形式,和散文与赋不同的是,诗歌常常要求在群体的语境中创作。
显然,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两位作者都认为,赋不是诗歌。
从以上所引可见,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二、三、四章文字中,凡涉及赋的内容,作者所阐述的赋文体的概念,呈现出互相矛盾、不尽一致的现象。对此,读者应该如何分辨?赋究竟属于何种文体?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和认识赋这一在文学史上出现的特殊文体?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赋在早期中国文学史上,主要有三种含义:其一,赋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最早可见于《周礼·春官》,后由《毛诗序》(诗大序)归纳为诗六义之一:“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赋是六义之一,即如钟嵘《诗品》所谓:“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其二,“不歌而颂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这是指一种摆脱了音乐的诵读方式,即,诗可合乐而歌,而赋则不是歌唱,而是诵读。其三,赋乃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刘熙《释名·释书契》有曰:“敷布其文谓之赋”,陆机《文赋》有曰:“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谓曰:“赋者,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可见,作为一种文体,赋的主要特征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其形式乃介于诗(韵文)与文(散文)之间,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迥异于其他文体的非诗非文、亦诗亦文、半诗半文、韵散相兼的特殊文体。它讲究声韵的和谐与形式的整饬,一定程度上具备诗的特点,却是不歌而诵;句型上长短不拘,没有格律的严格限制,可自由地抒情、状物、叙事、说理,这显然具有散文的特征;但它却又往往协韵,不同于一般的散文;它虽然形成于汉代,但并不固守汉代形成的体制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体制和形式特征不断呈现变化,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赋,如古赋(诗赋、骚赋)、俳赋、骈赋、律赋、俗赋、文赋等。现存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是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
有关赋的体制特征和产生发展的状况,我们再作些展开性阐述,以便更好地认识它。关于赋的产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章学诚《汉志诗赋第十五》也有较明确的说明:“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赋作为一种文体,乃远源于《诗经》,近源于《楚辞》,产生于荀况、宋玉,但它与屈原作品(《楚辞》)有联系,也有区别,楚辞并不属于赋。这样,问题来了,对于中国文学史上早期出现的三种文体——诗(《诗经》)、辞(《楚辞》)、赋三种文体,我们该如何区别其同异呢?对此,有必要做些梳理和辨析。
毫无疑问,诗、辞、赋三种文体,同属韵文大范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讲究声韵,但程度的大小不一;都具有一定的语言节奏;句式上均有各自较为统一、整齐的规范。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诗以四言为主;辞基本无散句,一般六言,加“兮”字为七言,间杂四言或杂言;赋多为四、六言句式;诗、辞基本无散句,极少用联结语,而赋则多联结语和散句;赋比诗、辞少抒情成分,多咏物、说理成分,它乃“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故诗味淡薄,散文气息浓厚。为此,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将辞与赋专门予以分论——有意设“辨骚”与“诠赋”,以区别辞与赋。任昉《文章缘起》将赋、《离骚》《反离骚》分为三种文体:赋——宋玉作,《离骚》——屈原作,《反离骚》——扬雄作。萧统《文选》于赋外,特立骚目(专列楚辞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诗、辞、赋三种文体,在古代文论家眼中,是属于不同类型的不同文体。
骚(辞)和赋,由于汉代人的混称,特别是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合二而一(称屈原作品为屈赋),致使后代发生争议,至今令人难辨二者的区别。对此,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有较清晰的说明:“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清人程廷祚的《骚赋论》,对诗、辞、赋三者的异同,更是作了非常清楚的辨析:“声韵之文,诗最先作,至周而体分六义焉。其二曰赋。战国之季,屈原作《离骚》,传称为贤人失志之赋。班孟坚云:‘赋者,古诗之流也。’然则诗也,骚也,赋也,其名异也,义岂同乎?……故诗者,骚赋之大原也。既知诗与骚之所异。诗之体大而该,其用博而能通,是以兼六义而被管弦。骚则长于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庙。赋能体万物之情状,而比兴之义缺焉。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赋也者,体类于骚而义取乎诗者也。故有谓《离骚》为屈原之赋者,彼非即以赋命之也,明其不得为诗云尔。骚之出于诗,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主幽深,赋宜于浏亮。”可以说,程廷祚将诗、骚、赋三者的异同,比较清楚地辨析明白了,我们由此也得以了解了诗、骚、赋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很明确地说,赋不是诗,也不是骚,它是具有自身特征的文体形式——虽然诗是它的远源,骚是它的近源,它的体貌中还有着散文的因子。
赋自汉代开始,正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体,开始了其独立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赋的文体形式随着时代的更迭和文坛的变迁,呈现出了不同的类别形态,大致上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其一,按篇幅字数分,有大赋、小赋之别,汉代以大赋为主,间杂小赋,魏晋六朝,小赋占了上风,之后,赋在文坛上不成主流,大、小赋之说也就随之淡化;其二,表现形式上,大赋多系设为问答的韵散间出结构,小赋则一般句式灵活多样,以四言句为主,具骈俪化色彩;其三,按文体类式分,赋又可分为诗赋、骚赋、骈赋、俳赋、律赋、俗赋、文赋等多种形式,一般来说,先秦是诗赋,两汉是骚赋(大赋),魏晋是小赋,六朝是骈赋(俳赋),唐代是律赋和俗赋,宋代是文赋,明清是律赋和文赋,当然,这样区分,只是属于不同朝代的倾向性而已,并不涵盖每个朝代文坛的全部状貌。
那么,历代的赋分类及其特征又是怎样的呢?
先看诗赋。作为“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毫无疑问,诗是赋的来源之一,早期赋的作品中,不光有四言的形式,更有以四言为基本句式的诗体赋,如荀子《赋篇》中的《佹诗》(不全为四言诗),以及刘向《屏风赋》等西汉前期的多篇赋作,而其中尤以扬雄的《逐贫赋》为代表,几乎通篇四言,且主客问答形式显然具有赋体的特征。其次是骚赋。由于汉代人骚赋(辞赋)不分,特别是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将辞与赋混而为一(如将屈原作品称为屈赋),造成文学史上对这两种文体的混乱认识,后人为此辩论不止。骚赋,特指赋文体的一种,以骚体的形式出现。从时间上说,骚赋的产生,在西汉早期,其命名乃得之于楚辞——即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离骚》,在文学史上称为骚体诗,由此,模仿楚辞体式的赋作品便被称为骚体赋,其型制与楚辞几无差异,可以说,骚体赋,既是“骚体”,又是赋,是骚、赋二体交叉结合而生的特殊文类,它是骚体形式,属赋的范畴。骚赋的代表作有——贾谊《吊屈原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哀二世赋》、董仲舒《士不遇赋》、汉武帝《悼李夫人赋》、王粲《登楼赋》、王褒《洞箫赋》等。类似骚体赋的,还有“九体”类作品,它们主要是模拟楚辞的“九”类作品,也属于骚体赋的一种特殊形式,如刘向《九叹》、王褒《九怀》、王逸《九思》等。再看大赋、小赋。所谓大赋、小赋,乃是依据篇制和字数而言,大赋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鸿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小赋是咏物或抒情的“小制”,大赋往往“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小赋则“随物赋形”“触兴致情”。大赋盛行于汉代,小赋流行于魏晋六朝。具体来说,大赋,也称散体大赋,篇幅宏大,辞藻繁复,铺排夸饰,其题材内容以描绘山川、京都、宫殿、游猎等对象为主,极尽铺陈之能事,多为呈现宏伟结构的长篇巨制,一般采用主客体问答形式,前为序言,中间正文,后有结尾(乱辞),其代表作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司马迁对大赋的评价是:“虚辞滥说”“靡丽多夸”。大赋体式中有一种所谓的“七体”,缘于西汉枚乘的《七发》,后人仿之,遂成“七体”,它全文以问答为体,凡问必七,以问为主,以答为辅,是大赋的一种特殊体式。小赋,又称短赋,一般体制短小,结构精巧,辞藻明丽,描写真切,语言比较流畅,句式灵活多样,多四言句,且往往押韵,题材内容或直接抒情,或借物咏志,大致分为抒情和咏物两类,代表作有张衡《归田赋》、江淹《恨赋》、陶渊明《闲情赋》、谢庄《月赋》、庾信《枯树赋》等。
综上所述,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看出,赋作为中国早期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具有特殊文学表现特征的文体,既有诗歌的样貌,也有散文的形式,但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诗歌或散文,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与特征,能自立于汉代及其后的文坛。《剑桥中国文学史》前四章(或许之后章中还有述及的文字)所述及赋的文字,应该说都有其符合赋本身特征的部分,或诗,或文,却也都有不完全符合赋特征的地方,故难免片面之失,这是笔者特别需要指出的。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在“中文版序言”中写到的话:“《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此外,本书还有以下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它尽量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地分割为文类(genres)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种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这种叙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汉魏六朝以及唐宋等时期还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现代时期则变得愈益困难起来。为此,需要对文化史(有时候还包括政治史)的总体有一个清晰的框架。当然,文类是绝对需要正确对待的,但是,文类的出现及其演变的历史语境,将成为文化讨论的重点,而这在一般以文类为中心作为传统的文学史中是难以做到的。”笔者特别赞赏主编及其同人们独创的特色(至少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领域)——将“剑桥中国文学史”写成一部文学文化史,这是一个不趋同之前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包括欧美及其他地区,也包括中国)的大胆创新。这种独创性带来的生气和活力,使得这部宏大的文学史巨著,给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同时,笔者也不无遗憾地需要指出,也许正是这种试图突破文类框架的努力,《剑桥中国文学史》难免在具体撰写、全书统稿和整体梳理上,忽略或疏忽了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某些文类概念定义的准确判定与表述,缺乏有意识的统一和规范,令读者略有无所适从之感。当然,从世界文学史高度看,有学者曾指出,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几乎很难发现有像中国赋这样非诗非文、亦诗亦文、半诗半文、韵散兼及的特殊文体,它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坛的一个独创。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