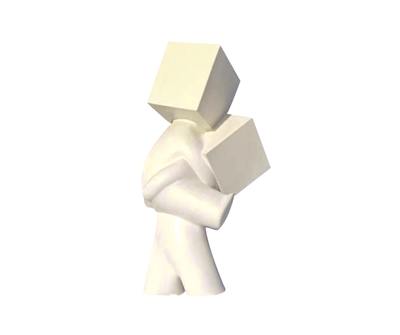都这个时代了,还能有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挺不容易的。
——刘洋
认识刘洋之前,“国际雕塑创作营”是个生词。简而言之就是——“去世界各地做雕塑,把它们留在当地”。
“雕塑创作营是一种国际文化交流方式,由政府或者机构出资,全球挑选雕塑艺术家在1~6周的时间内,在一个公共区域,现场创作雕塑。材料石头居多,此外还有木头、金属焊接、青铜和少量的装置。人数少则三五人,多则达一二百人(北京就有过一次两百人的,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活动结束,为这些雕塑建一个雕塑公园,或者摆在城市重要的地点。创作营会挂参与艺术家国家的国旗(五星红旗因为我已经在30多个国家升起,这是可以骄傲一下的)。组委会除了负责吃住和路费,还会给一部分稿费。相比某些艺术领域在国外的自炒自卖(比如亮相某某大厅之类),其实这才叫真正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刘洋在他的随笔集《斗石头》里这样介绍。
听上去这事咋这么好,好得都有点气人。“都这个时代了,还能有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挺不容易的。”刘洋自己都说。
哈尔滨人刘洋,1972年生于道里棚户区。大学在东北农学院学食品工程。毕业开过一个月面包房,蹬三轮给人送过一年货。
为了登女朋友家门有个说得出口的正经工作,1997年应聘进《黑龙江晨报》,做美编、做新闻部编辑、做体育部主任。
2002年考进中央电视台,任《实话实说》策划、编导。2006年红火了足足250天的央视《我的长征》(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外真人秀)节目,刘洋带着一两个清华大学户外探险队精英,司职探路,被称“先锋官”,拿过中国户外最高奖。
其后拍纪录片、微电影,主持香港健康卫视节目,当新闻评论员、写网易专栏,服装设计拿过国际铜奖,甚至在著名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客串过一个悲催的日本兵“多嘴桥本”。
而雕塑基本算刘洋自学的——大学时在一个雕塑工作室当过学徒。自1999年,他的雕塑便在国内和国际平台获得奖项与展出机会。
2010年他开始参加国际雕塑创作营,游走世界各地,开始自由的雕塑创作生涯。至今他的雕塑创作版图遍及五大洲34个国家和地区,已完成76件大型公共雕塑,他的雕塑作品《柔软的力量》赠予智利圣地亚哥市政府,与米兰足球巨星德阳·萨维切维奇同获黑山城市贡献奖。他的作品也分别装置于意大利特伦托博物馆、瑞士阿尔卑斯山采尔马特、土耳其棉花堡、埃及尼罗河畔及台湾故宫南院等地标位置。
2012年,他创立国际雕塑创作营联盟(ISSA),并担任秘书长,热衷推动雕塑创作,参与各国雕塑研讨会、演讲等。并担任雕塑展览策展人,雕塑创作同时旅行。著有畅销书《刀锋上的行走》。
2021年10月1日,刘洋作品《雪孩子》获选为“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公共雕塑,放大成5米高的巨大版,首个入驻并永久陈列于冬奥公园。
2022年 2月24日,《版图:刘洋雕塑个展》在香港Artspace K空间开展,展期至7月3日。
见刘洋两次,一秋一冬,中间隔了一年多。
他个子不高,笑眯眯的,背个双肩包,一看就很能走路。穿衣风格家常得很,灰突突的,仔细看才看出饱和度低却一般人很难驾驭的配色。“有一种人总能让你感受到轻松,刘洋就是这样,不管在人群里,还是在自然界中,我很少能看到他的局促和焦虑,这在当下人的身上很少见……我很尊敬这样活着的人,不疾不除,真实地面对自己,接纳自己,然后和这个世界自在地相处。”他昔日的同事、主持人和晶这样评价他。
“其实不应该用文字来解读雕塑,而是用人生来解读。当你把整个人想明白,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雕塑了。”刘洋这建议我觉得不错。
困顿的生活会让身体变好
北青报:我看你身体状态保持得挺好,你健身吗?
刘洋:我不健身。我是个体力劳动者,健什么身。我得留点力气干活。
北青报:你平常踢球吗?
刘洋:我踢球也打篮球。但那要组队,现在身边没人了,一年能踢上一场就不错。因为像我这个年龄,这个身材,我碾压你知道吗,我现在过他们跟玩儿似的。有句话说:“过你们就跟过清晨的马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已经胖了,完了笨得呀。我这个状态一直保持着。
跟我生活有关。第一我不会开车,然后像我这种没什么钱也不花钱的人,打车打得也少,我基本都是坐公交。最近我自己又弄了个小滑板车,不是电动的,可以折叠,可以上汽车、地铁,不受限制。最近廊坊借给我们国际雕塑创作营联盟一个地方用5年,我就要去廊坊。最近一有疫情车特别不方便,我有那小滑板车,没车的时候我“倒短儿”就特别方便。这样困顿的生活会让身体变得好,因为每天走路会比别人多很多。
以前我曾经半年多徒步了6000多公里,只是那时候是拍纪录片。某种程度来讲我算是个探险家,我也是中国探险家协会的会员。现代社会人工几乎已经被机械替代,男性也很少会去做体力活,骨子里的荷尔蒙与血性无处释放。而做雕塑是一种释放,尤其到全世界各地做雕塑,让你觉得好像可以仗剑天涯,行走江湖。
早年我不知道人还可以这样活着——可以全世界到处去走,见各种各样的人,可以把雕塑摆在各种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尼罗河边上、撒哈拉沙漠上、喜马拉雅山(道拉吉里)上……而且还可以有收入,我觉得这种生活简直太理想了。我不是一个有特别宏大理想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影响历史的那种伟大的雕塑家。其实我做职业雕塑家不是想选择职业,而是选择一种生活。
做雕塑我可以拥有更高的自由度,创作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作品。从艺术角度讲,国外的艺术家也更偏于实践,他们动手能力更强。中国艺术家动手能力会弱些,不光是中国,比如印度也是,为什么?因为劳动力便宜。我们很多艺术家不亲自做大型雕塑。我经常把雕塑比喻成生孩子,我们在国外做雕塑就像自己生孩子,当妈妈;在国内像爸爸,把自己那点事干完之后,剩下就都是别人的事了。
北青报:你第一次出去是哪年?是个什么机会呢?
刘洋:2010年。我在国内参加活动时认识一个韩国人,发邮件说他做个活动,问我自己做没做过。我说“做过”。其实我以前没有自己做过大型石雕。这个东西在国内不是自己做,有助手。甚至都不做,拿个小稿给人家工厂,加工完了摆那儿。但国外都是自己做。我自己找机会练了练,觉得好像对付得过去,胆儿也大,就去。我一直说人家都是练完了再比赛,我是“以赛代练”,都是在创作过程中练手。
北青报:去的哪儿?
刘洋:韩国。闹了好多笑话,因为以前没干过。连机票都不知道买往返的,买一单程就过去了。那是我第二次出国。去了又不会使机器,当时23厘米一个锯片就很大,我切那锯片就炸了,很危险的。炸完又不敢告诉他们,趁人不注意把它扔了,又去领了一个锯片。后来那韩国人好多年之后问我:“那是不是你第一次在国外参加雕塑营?”
我所有的成功都是运气
北青报:所以从根儿上说,还是喜欢雕塑这个事成就了你,可以这么讲吗?
刘洋:你说我到底有多喜欢雕塑,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不是那么个执着的人。初中喜欢美术,后来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考不了美院,上了工科院校。我爸的一个同事说:“哎呀,小孩喜欢美术,上大学没念成挺可惜。我有个朋友搞美术的,你跟他学习学习。”以前家里的关系就是这样,就去学吧,赶巧人家是个教雕塑的。
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能搞这个。因为家庭一般,你不知道未来什么是一个好的人生。因为爸妈都是学校里的工人,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上大学可能是一条好的出路。按我小时候当地的说法“没准将来能坐小车”,就不用像工人一样那么出大力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1992年农历二月二去那老师的工作室。他也没太想我能跟着学,反正他又没有学生,因为干雕塑是个力气活,他成天自己干也很辛苦,有个助手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跟他学的时候,也不主动学,只是闷头干活。有天他大发慈悲说:“这样,你做个赫拉克勒斯。”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了那么一个,他帮我指点,修,告诉这种事该怎么干。
北青报:等于就是用你给他干活?
刘洋:学徒就是这个样子,他也给我工资啊。但是这没什么,当时有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老师那里有很多书。老师是鲁美毕业,算是好学校出来的。那时候没有网络,专业书也非常少。那个年代,专业书我们非专业的人不允许买,甚至书店都不允许你看,因为里面有人体。我没做过人体。做雕塑不做人体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因为雕塑早年的核心就是把人做得很像。那么你没做过真人体,等于是一个巨大的缺失。那时候天天老琢磨,问我哥:“你认不认识开澡堂子的?我给人搓澡去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见到很多人体。而老师有特别特别多的书,瞬间就打开了一扇门,包括国外的书、讲雕塑技法的书,这都是书店都买不到的。
第二,他出国会带来一些小雕塑,包括他自己做的一些雕塑,能看到这些东西其实也有非常大的价值。我大学时候做得比较多,因为条件比较好,老师那儿有空间、有泥、有石膏。休息日和假期我基本都是在老师的工作室里,有空就去。大学毕业之后就少了。
后来我做了雕塑,我老师很吃惊,他以为我就是跟着混吧混吧就完事了。而且大学一毕业我也就不跟他了。后来我当了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他当理事。他觉得很纳闷,没想到我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后来到北京,也一直在做雕塑。2001年开始参加了两次全国的雕塑活动,也非常不容易,所有人都是专业的,只有我一个是业余的。跟一些机构慢慢就比较熟了,比如说北京城雕办主任对我就很好,他觉得我是个很传奇的人物。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说“北京还不错,过两天我要来北京”。他说“你来北京干吗?”我说“去中央台呗,没别地儿可去呀”。过两天真来了,他就一直在后面说“这人挺厉害,说去中央台就去中央台,中央台是你说去就能去的吗?”然后还有一个雕塑杂志那边比较熟,因为我以前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这两个机构比较宽容。其实各行各业都有门派之分,不是本帮弟子,机会很少。这两个机构就比较开放一些,能容我一个非专业的人进来。所以我觉得所有成功都是运气。
《雪孩子》在北京冬奥公园
全世界都是我的工作室
北青报:那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开始转向成为一名职业雕塑家呢?
刘洋: 2005、2006年左右开始,我在国内参加一些雕塑创作营的活动,结识了很多国外雕塑家,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最早不会外语,也不认识外国人,都跟中国人一拨儿。等到2006年和2009年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那时候年龄也大了,自信心也上来了,就跟外国人接触多了。听他们跟我说“你看我这一年,在你们中国完事之后我就去韩国,去了韩国去美国,从美国再去哪儿……”感觉太牛了,你又能云游世界,又能留下作品。
我就决定去了。当然也不容易,我从2006年就开始往外投稿,投了4年都没有出去。那我也不觉得那件事情是一个挫败。我老举个例子,我说人就像蛇一样,你把这皮脱了之后你才能长大。年轻的时候变动会给你带来一些很新鲜的东西,你得能扛得起变动带来的风险。终于2010年我出去了一趟,要不出去的话,其实这个门槛是很难过的。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们不出去?为什么就我能出去?中国在外面活跃点的也就是四五个人,他们是一档,我做了30个国家独一档。这个东西不是水平的事,就是时间,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和我在外面做的东西的多少。
北青报:你一般做什么作品比较多?
刘洋:我不是很挑材料,但事实上我完成的作品石雕比较多。因为在世界各地的创作营中,石雕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我比较偏好永久材料,因为能够永久地保留下去。
埃及文化部长在请我们去做雕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位诗人,他说埃及有5000年的文明,5000年前的埃及人留下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还有这么多神庙给我们,那么我们现在的人要留给5000年后的埃及什么?所以请雕塑艺术家来做可以留存下去的雕塑。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
我们做的这些雕塑有70%左右不在旅游城市。那个方式有点像一个书法笔会,用一个文化交流的方式留下作品,对于城市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商业雕塑很贵。而用这种方式,它支付你的相当于一个补助,然后也能留下很多作品。他们会带你玩,把你奉若上宾,你会跟当地有很多的交流。
北青报:一般一年去几个国家?你是一站一站的接着来吗?
刘洋:2010年我就去了一个国家,我们4个国外艺术家加上几个韩国艺术家,那4个艺术家都成了我后来很好的朋友。2011年去俄罗斯、埃及。2012年就出去了9次,这在世界上也是很难见的,因为我们做雕塑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得有邀请。人家得准备好石头,人家得有活动,你才能去。那一年我真的全是在出国做雕塑和办签证,几乎没干别的事。中间还抽空去了趟珠峰。那一年之后,就奠定了我在国际上的位置了。完了2017年又去了10个创作营。其他一年大概是六七个。
北青报:如此一来,你现在是一个很爽的生活状态了,干着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情,然后路径也都很通畅。
刘洋:而且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我们这种文化输出是非常良性的,没花国家一分钱,都是对方拿钱请我们出去。我们在国外受到的礼遇也很高,在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整个城市挂的都是我们的海报;在尼泊尔的时候,直升机给我撒花,感觉像巨星似的。
北青报:为什么选择“版图”作为香港个展的主题?
刘洋:别人经常问我工作室在哪儿,我没有工作室。我以前在国内也不接公共雕塑的工程,小雕塑在家里也能做。四川的修行人有一句老话:“一匹马有一匹马的烦恼,两匹马有两匹马的烦恼。”当有工作室的时候就会有工作室的烦恼。所以别人问,我就说全世界都是我的工作室,全世界也都是我的展厅。这逐渐就成为我的“版图”,我用雕塑来开疆拓土。我现在已经在34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作品,以后还要开拓更广阔的雕塑版图。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吴菲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