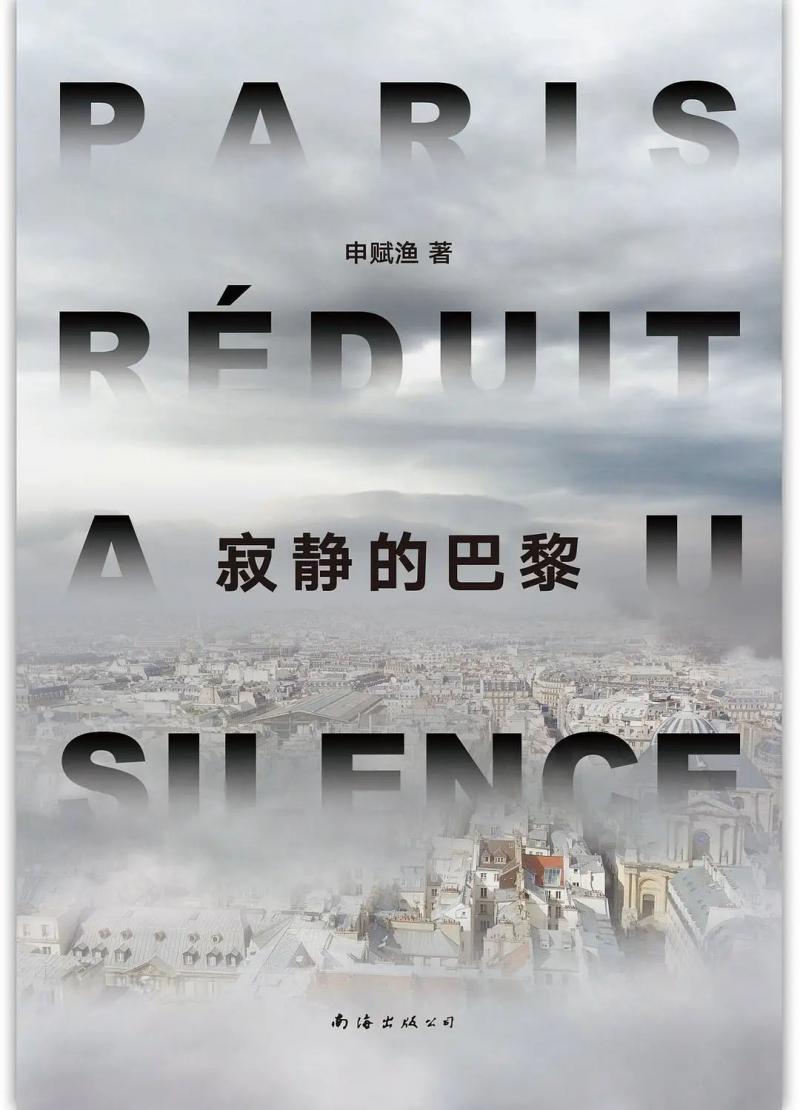作家申赋渔在异乡漫游,5年中采访了许多个普通的生命个体,但如何以文字记录这些人,在普通人的故事中回望历史,在历史里关照细微的现实,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一切都在巴黎因新冠疫情而封城时得到了答案。
巴黎,一部色彩绚丽的电影,突然转成了无声的默片。巨大的寂静中,每个人都听到自己的心跳。申赋渔记录下生命的跳动,如作家梁鸿所说,生命于沉寂中努力绽放,显示出非凡的美。正是这一个个平常人的故事,组成人类精神的基本面貌,也使寂静的巴黎始终充满内在的活力。
在新散文集《巴黎的寂静》中,申赋渔的文字敏锐而有温度,将平凡人对生活的信念和选择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作家徐则臣看来,这才是极具力量和真正的宽慰所在。
塞纳河上的空桥
申赋渔/文
圣心大教堂的左边是圣皮埃尔教堂,圣皮埃尔教堂的左边是小丘广场。因为新冠病毒,百年来从未关闭的圣心大教堂关闭了,最热闹的小丘广场也变得荒凉寂静。拥挤的游客陡然消失, 给游客们画像的画家们也不见了。乔·雷诺阿不知道去了哪里。
乔是一位中国画家,因为疯狂热爱印象派画家雷诺阿,我们就喊他乔·奥古斯特·雷诺阿,他很高兴。不过平常嫌麻烦,我们只喊他乔。乔是画油画的,不过大部分时间不画,在小丘广场上摆一个摊子,给游客画素描。
雷诺阿画作
第一次见乔是在一个画展上。我随一个朋友去看热闹。这是几国在巴黎的画家的一次联展,组织者是一位有钱的公证人,展厅就是他家宽敞的客厅。来的人不多,应该都是主人和参展画家的朋友。大家端着酒杯看画,低声说着话。一圈看下来,也就觉得乔的画有一种亲切感。他画的是人,中国人,他故乡的人。的确有雷诺阿深情温暖的味道。色彩也漂亮,干干净净。
乔站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朋友带我去见他。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很有力,连说了四声“你好”。回头让旁边的一个女孩喊叔叔。她是乔的女儿。我对乔的印象很好,低调、真诚、热情。画展上没法畅谈,约了过一周到小丘广场去看他。
我是从家里走过去的。不远,二十几分钟就到了圣心大教堂的下面。从这里上山有点累,台阶很多,到处是人。同时要提防小偷和试图把带子扎在你手腕上的游荡青年。从圣心大教堂到小丘广场的巷子里人更多,不断有手持纸和笔的画家拦住游客招徕生意。游客不管是拒绝或者接受,双方都显得彬彬有礼。到处洋溢着一种节日的喜庆气氛。
小丘广场中间是露天咖啡座,四周摆着一圈画家的摊位,每个摊位上都撑着一把大伞,挡阳光,也挡雨,巴黎总是在下雨。有画水彩的,有画油画的,有画水粉的,还有人用各种材料在拼贴涂抹着,摊位上满满地摆着他们的代表作。大多数出售的作品画的都是巴黎的风景,实在说不上多好。只有挂着漫画和素描作品的摊位是给游客们画肖像。这样的摊位最多,游客们也愿意凑趣,许多椅子上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摆着美丽姿态的各国模特。
乔一个人坐在伞下面,捧着一本中文书在看,没有顾客。看到我,赶紧站起身来握手。他的摊位跟别人不一样,没有挂许多大大小小的画,只挂了一幅大幅速写。一个年轻女孩穿着碎花的裙子,坐在一座木板桥的长椅上。桥的栏杆上挂着许多锁。女孩眼神亮亮的,像是好奇地打量着眼前来来往往的游客。所有的线条都很简洁,长短粗细都恰到好处,一看就知道是一挥而就,几乎没有任何涂改。这是他女儿的样子,不过看起来要成熟些、外向些。他女儿太腼腆了。
我们也就说说闲话,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朋友才来。乔坚持要请我们到边上的咖啡座坐一坐。我要了一杯卡布奇诺,他们喝的是意大利浓缩咖啡。偶尔会有人在乔的那幅速写前面站着。大概坐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位高个子中年人,很认真地看那幅速写,然后东张西望,喊道:“Hello!”乔站起身走过去。那人问他这幅画多少钱。“No.”乔摆摆手。
我们与乔告别之后,慢慢走下山。朋友跟我说,几年前乔曾经卖过一幅油画。卖了心里又后悔,后来就没卖过。价格高没人要,低了,他自己又觉得不舍。他现在油画画得少,特别想画了才画。好在给人画素描,一个月也能挣不少,生活和女儿的学费都够了。
“那幅速写是他女儿吧,画得真好。”
“是他妻子,出车祸死了。”朋友说。
之后又跟乔见过几次,他一次也没有跟我谈他的油画。巴黎封城后,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手机一直关机。前天突然给我回了电话过来,说这二十天,把自己关在一个朋友的仓库里画一幅画。“我在画一幅大画,一幅巨大的画。”他说。
乔跟我说,他在画塞纳河上空荡荡的桥。他没说是一座桥,还是许多桥。我立即就想到了艺术桥。他给妻子画的那幅速写的背景是艺术桥,挂在桥上的那些锁叫“爱情锁”。据说情侣如果把锁锁在艺术桥上,钥匙扔进塞纳河,就能永远锁住他们的爱情。因为挂锁的人太多,二〇一四年艺术桥的一段不堪重负倒塌了。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于是拆除了所有的爱情锁,并且用玻璃墙挡住栏杆,让人们没办法再“锁”上他们的爱情。可是不屈不挠的爱人们,仍然想方设法,在路灯杆子上锁起了一串串爱情锁。这些锁因为不会对古老的桥构成伤害,已经顽强地存在了好几年。
巴黎封城后,工作人员趁桥上没有行人,突然把最后的这些爱情锁全拆了。
艺术桥是两百年前拿破仑下令建造的,一端连着法兰西学会,另一端连着卢浮宫。最早在这里挂上爱情锁的,是一百年前的一些悲痛欲绝的女孩。她们站在艺术桥上眺望着远去的河水,苦苦思念着再也不能从战场上返回的恋人。一百年后,新冠病毒猛然来袭,病毒已经夺去了一万多个法国人的生命。陡失爱人的悲伤又弥漫在巴黎的上空,如黑压压的乌云,怎样也不能驱散。
节选自《寂静的巴黎》申赋渔/著;南海出版公司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