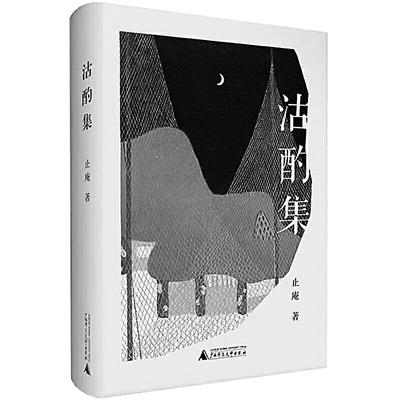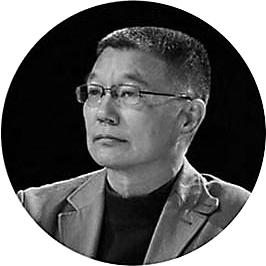主题:阅读使我真正成为我——《沽酌集》新书首发会
时间:2020年12月5日下午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
嘉宾:止庵 传记随笔作家,自由撰稿人
史航 书评人,编剧
主办:广西师大出版社、三联韬奋书店
人得知道得多点,写得少点
就跟我们说话一样
主持人:《沽酌集》是止庵老师20年前的书,不仅我们编辑,读者也有很多读了以后反映说,这个书并不过时,文字也很洗练,书中的观点今天来看也有很多共鸣,就像一本新书一样。我们就从创作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才能写出长远的文章?或者也可以说说一部作品如何才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止庵: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专业写作者。我以前是一个医生,然后我做记者,我到外企打过工。其实都是业余写作,这样写作它有一个好处,你不用指着它生活。我觉得人写文章有一种悠闲态度比较重要。作者不能处于一个饥饿状态,应该处在一个温饱状态,但是又不是吃得太撑,那得睡着了。就是那么一个清醒状态写作。
第二点,我觉得写文章不能写时文——今天出什么事今天写,明天出什么事明天写。这种情况下你写出文章,可能好多报纸约着要,但是登完了就完了。咱们刚才说了一大堆话,其实是关于读书,读书必须得势利眼,做什么事都不能势利眼,读书得势利眼。就是我真是瞧不起一些人,瞧不起人我就是瞧不起他,我瞧得起人我就瞧得起,所以我觉得读书这个事势利眼一点错没有,读书不是一个扶贫项目。
写作也得有点势利,写作势利眼的,不能针对读者,得针对自己。刚才史航说了一句话非常对,得自己化身成为另外一种人来盯着自己。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学法律。大家知道大的律师事务所有一个职业,就专门是唱反调。比方史航犯案了,我给他辩护,我准备好了,旁边人说你这不对。他会盯着你的,哪些地儿你说得不全。我其实特想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人的职业。
你写文章的时候得有一只眼盯着你,把自己这个文章仔仔细细看,把它看周全了,句子、词用得对不对,意思表达得对不对,开头、结尾都想好了。这只眼是谁呢?这只眼是你自己。你应该是你自己最苛刻的一个读者,你不能轻易放过你自己。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是这样,人得知道得多点,写得少点,就跟我们说话一样。你看史航,属于口若悬河的人,但是我特别关注史航,因为我最早不认识他,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关于三毛的活动,把他请上来,我看他说话突突突,我说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快!说明这后边有一个东西,在史航的背后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史航,在后边往这供材料,前面再往外送,得有这么一个人。什么意思呢?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你自己知道的怎么也得比写的多。前两天我做过一个网络的节目,我说你打一口井,能打出一桶水来,但是你得有一井的水,你才能打出一桶水。你不能说是这一个水桶就这么多,哗啦一倒,完了,没有了;或者你根本连一桶水都没有,你非要倒出一桶水来。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在这儿。
写文章不能太讲效率
写作使阅读变得认真有收效
止庵:我觉得现在人特别讲究效率,前两天有人跟我说为什么要用网络语言呢,网络语言效率高,都给节省成仨字儿。
史航:一句话变仨字儿,“我伙呆”。
止庵:我觉得不能这么讲效率,写文章不能太讲效率。你必须得干好多事,你知道好多东西,然后你才能说一点儿。然后你就永远有余绪,人家知道你这人没把话说完,还有话可说,而不是说一下把这话全都说尽。
所以咱们现在经常干一件事,马上想你是不是应该写书,你是不是要写文章?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全不干,就在家吃饭、睡觉、看书,然后看电视、看电影,这是我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又要写作,我得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写作。读书有一个小问题,你读完这书就读完了,你如果不记录一点,过一会儿你就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其实这是个备忘录。
但是你要提供给别人,你还要自己觉得这东西值得一记。因为你要写作,所以你阅读的时候会读得更仔细一些,你不会疏忽太多,而且读完之后你还得把它想周全。比方我们俩人今天说的话,你如果能把这话一句一句都记下来,有好多是半句没说完,自己被自己打断的。但是你写文章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这一句话写周全,得把这一个意思写到底、写完,而且还能自圆其说,还能跟整篇一致,所以这需要翻来覆去想这事儿,我觉得乐趣是在这儿。
因为你要写作,使得你的阅读变得认真,变得有收效,而且使得你最后能够记住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其实读书绝大部分东西都会忘掉,比如我跟史航都是侦探小说迷,侦探小说最要命的(侦探小说、侦探片都是这个问题),就是看的时候特别热闹,看的时候非常高兴,等过去的时候这讲什么来着?完全记不住。所以你通过写作把它记住,我觉得其实写作对于阅读是一个帮助。
大家可能问一个问题,你干吗非要拿着一个书来写一个文章?为什么不直接写这个文章?
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事,比方说这里边有的谈到什么饮食,我还有一篇文章是谈浴室的。因为有一本书叫《欧洲卫浴文化史》,我就从古代到现在,包括我经历的人,就是各种洗澡的故事,我把它写成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若是单独写一个,我真的打不起精神,我觉得没有必要。就好像我的靴鞋观什么之类,就没必要这样谈,但是有一本书跟这儿搁着,就好像是跟这作者有个切磋,有个交流——比方他这儿没有说到的,我就补充说一点;比方他说的有的地儿不是很对,我就给订正一下;或者他有的说得挺好的,我就给赞美几句,其实是一种交谈的方式。
我理想状态的文章
是安静平淡说点真的心得
止庵:我觉得写作其实就是一个交流。像关于书的文章,首先是跟作者交流。我有一个经验,我一直觉得阅读或者是写作,给予、收到这种方式,到底应该打什么比方合适?有一次我突然明白了,我到音乐厅去听一个室内乐的演奏,我坐的位子正好是音乐厅二楼离乐池最近的一个角的位置。那地方不是个好座位,但是它看台上那些人比较清楚。我就看那些做四重奏的人,忽然发现一个事儿,我一辈子都没明白的事我明白了。就是他们之间的交流远远胜于跟底下听众的交流。比方说大提琴的跟那边小提琴的,他们俩之间眼神的往来,和他们之间比方我们这么演,那边那么演,他们这种交流绝对胜于跟你的,你只是一个旁听者。
后来我就读了张爱玲,张爱玲说交响乐是一个阴谋,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交响乐是一大帮人结合对付底下的观众,所以需要把底下观众给调动起来。或者比方说独奏,它其实也接近于这个东西,一个人演,他只面对底下观众,他一定要跟观众交流。只有四重奏这种形式,它是完全跟你没关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胜于跟你的关系。
我觉得后来我就明白了,写作原来根本的意义就跟在这儿一样,实际上你是跟两种人进行交流。假如你写的是谈书的文章,你首先是跟作者的一个交流,他把东西都搁在这儿了,你跟他交流。再就是跟潜在的知音读者交流,比方说你这写的文章总会有一个人看得懂,总会有两个人看得懂,你是跟他来交流,其他人是旁听者。这样你就不会去想着,就像交响乐一样,我得全都给他把情绪调动起来。
我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周作人,他曾经在1945年写过一篇《谈文章》。他说文章有两种,有一种是叫聊天式、交谈式,像咱俩这说话。我们一定是打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开始。所以,这个话题首先它就不会太低,他确实有心得,这心得绝对是大家都不说的,你这有个秘闻,一说就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写文章应该是这个样子,只要是个交谈式的话,你就会设想读者是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你跟他谈的时候一定说最要紧的,最有心得的东西。你的态度也不一样,就像到我们家去,突然手上拿着一个麦克风就站起来说,“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红楼梦》”,肯定不能是这样。他肯定是“大家别吵,安安静静”,甚至比我现在说话的声音应该还低。大家就聊聊天就行,所以声调一下就放低了,态度也变得和缓了,就不那么着急,来我们家踏踏实实你就坐着说说话。你也不用急着非得说服我,不要我们俩争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理想状态的文章就是安安静静的,平平淡淡的,说点真的心得。同时不急不躁地好好把话说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是说给朋友听,是大家在一个已经知道一些事情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交谈,所以没有必要去从头讲起。
读书与其说是兴趣爱好
不如说是一种能力
主持人:很多人认为读书是一种兴趣爱好,希望阅读停留在放松、治愈这样一个层面。止庵老师前些日子发了一条微博,谈到“读书与其说是兴趣爱好,不如说是一种能力”。请二位老师就这个话题展开聊一聊。
止庵:我这话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现在发现特别逗,比方我自己其实活这岁数了,眼睛也不太好,其实看本书不是很容易。朋友圈有时候看谁发一本书,然后有人在书底下留言“这书名我记住了”,或者写一个M,写一个Mark什么之类。我寻思这人得有多忙,您这都忙到什么程度?真的都比我忙,我是最闲的那人。
所以我为什么说读书是种能力,我觉得我周围很多人都是,比方一篇文章你没10分钟看完了,但是有人就说我得搁着,什么时候我有时间了,等我有精力再看,都这样。我有朋友辛辛苦苦买一辈子书,说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读书,退休之后我有时间了,我也有精力。别等你退休之后真的有时间了,但是没精力了,眼神也不行了。
其实阅读是这么一个东西。什么是能力?比方说吃饭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因为我这饭吃不动,或者我这人最大问题是水喝不动,你说是不是这人就是快不行了,是吧?或者咱们说这路走不动了,或者说是风景挺好,我看不了了,太累。我觉得好多人在不阅读的时候,其实是生龙活虎的人,但是一到阅读他就成这么一个人——什么东西他都得等着,等我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其实现在就是时间,而且这时间也没干别的事,坐那儿瞎发呆,你为什么不用这时间呢?读书时间全是挤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阅读是一种能力是这个意思——确实首先他肯定是个兴趣爱好,但是这个兴趣爱好你把它落实了确实是一种能力。
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怎么看书。我在北医上学,周末或者平常有时候回家,就在公交车上看,最挤的时候我把书举到天花板上看。时间可不全都是,哪有专门大块的时间说我等着给您老人家准备好时间,茶叶给您泡好了,然后您老人家看书?没有这个事。
谁不忙,我在公司上班忙得真的跟什么似的,但是坐飞机的路上你可以带本书看,然后你到旅馆,晚上可以看本书。所以我觉得严格说,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其实不是都给你预备好一顿顿饭,而都是你自己去挣。你要真是指你自己一天8小时上班,然后其他的16小时睡觉或者吃饭,如果这么过日子的话也可以,但是确实以后没有一个更好的阅读的时间等着你,没有这事。
还有一个事,好多老师说我现在没有阅读的兴趣,我一定要争取培养阅读兴趣,还有人问怎么培养阅读兴趣。我觉得我自己跟朋友交往了这么多年,我见过原来喜欢读书的,后来不喜欢读书;我还没见过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后来又变成喜欢的了。所以我觉得培养阅读能力这话……
史航:培养阅读能力和培养阅读兴趣这是两句话。
止庵:这句话我觉得不是特别成立。我觉得只能说“保持”——原来你有你把它保持下来,这有可能。要说培养几乎是不可能。什么人能培养呢?小孩他能培养。所以各位在座的如果自己没有阅读能力,无所谓,算了,咱没有就没有了。但是你们家孩子应该让他有。怎么办?从小培养让他念书。各位如果是有当老师的,学生你让他看点书。我觉得只有寄希望于我们的下一代,寄希望于未来,这个是可能的。
不爱干什么事儿最后都能干,就是读书的事儿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事儿不是个好事儿,不是个很容易的事儿。读书是很麻烦的,第一读书得花钱买书,家里还得有地方搁着,还得有专门的时间,不能被打扰,不能别人吵你、别人影响你,这都不行。这么一个情况下你才能读书。另外咱们现在又有网络,又有电视,又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相对都比读书容易得多。所以我觉得假如你不喜欢的话,读书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
读书是一种神秘的生理需要
你只能等待造化之力
史航:在微博上经常有人要求我培养他的阅读兴趣,协助参与培养。这很难的。阅读这个乐趣你怎么让别人插手?你只能等待造化之力。当年那些领导人长征的时候读书,那么艰苦还在读书,而且他读的书可能不都是军事题材的书和地图,不是马上能用上的书。其实读书是一种神秘的生理需要,神秘的,但它又是生理需要,就这个东西。
“这书说得真好,过两年我有空我去看一看”,都是这个心态,拖延。现在我们随便看公众号的文章,“本文章需要你花13分钟”,这都可以!虽然别人觉得我挺爱读书的,我觉得我还是不够,但今年疫情是我相对被动因而导致读书最多的时候,我这辈子读书最密集的时候。因为我真是除了吃饭、喝水、睡觉、上厕所四件事之外,就没有做任何别的事,就是在长春的家里读书,而且是把好的全集就按箱买回,终于敢这样了。《陈布雷日记》十四本,我就从1937年、1938年读到1948年,我就可以这么看了,我有这个时间了。这个心气儿完全不一样了。
昨天我在机场买了本书,叫《我信仰阅读》,是国外的一个出版社的创始人的回忆录。那本书写得特别生动,他就讲书不厚他看着不过瘾,他说他有一段时间,一周就看法语著作,就看《追忆似水年华》。他真的是一天看一本,七天看完。他讲这个乐趣在哪儿等等。
我其实看这本书有点久违的感觉,因为看这本书就很过瘾。他特喜欢亨利·詹姆斯,他甚至决定用这个来试探跟谁交不交朋友——我要说这个人,你一变脸或者没反应,我就跟你不联系了。他大学时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从哥伦比亚大学直接去剑桥上学,就是这么读书的。你发现生活像经历卫国战争一样,还是那么生动,或像个谍战之父,还是很好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过瘾、非常嗨的。
所以这本《沽酌集》)有很多的点我觉得有意思,比如它提醒你要警惕“真诚”这个词,或者它提醒你要警惕“我们”这个词。它可能有时提醒你阅读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再从哪儿出发,或者说什么样的书它金贵,什么样的书不金贵。这里面都有好多的点,或者说如果他是这么说的,你再对照那个事肯定他说得有问题,他自己就打自己脸了。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推理小说集、推理短片、各种命案,一本书就是一个命案,有的是无头案,有的是几个连环案,我觉得这些是有趣的。
我们可能快到了跟大家提问的时间,我不是主持人,我就预先说一句,特别希望大家提问的时候,也像止庵读书一样,就脑子过滤一遍,这个问题本身的乐趣和价值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特别认真地和详尽地来回答。
读者:我看书的时候发现谷崎润一郎经营的那种美学观,在周作人的文章中体现得特别突出。周作人是崇尚简俗、爱好天然的人,他的文章在那种晦涩的措辞当中也有自己的情绪。我查了一下,谷崎润一郎和周作人只差了一岁。我想问他们俩有见面或者说书信上的交流吗?或者说周作人先生有受过谷崎润一郎先生文艺美学观的影响吗?
止庵:周作人比谷崎润一郎大一岁,他们有交集,也是很好的朋友。
先说受没受影响。谷崎润一郎的美学观在日本叫恶魔主义,唯美派的。周作人离开日本实际上是在1912年,大正初年,明治末年。谷崎1909、1910年已经登上文坛的时候,周作人还什么都不是。他比周作人要出名早。但周作人是不是直接受他影响,我觉得不是。
周作人很喜欢谷崎的文章,在一九三几年也写过介绍谷崎文章的文章。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谷崎去世。其中有一件好玩的事。周作人1949年以后,特别想吃日本一些很稀奇古怪的点心,他就托香港的鲍耀明。鲍耀明跟谷崎认识,就去托谷崎买这个点心。谷崎买了之后先寄香港再寄到北京来,这就需要是那种保质期比较长一点的点心。周作人的太太也是日本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她临死之前就吃了这点心了。
谷崎是日本的大文豪,1886—1965年在世,比周作人晚生一年,比周作人早死两年。当时周作人想送给他一个图章,他也想要一个中国图章。周作人就找张樾丞刻图章,但是刻图章没有料。那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找不着材料,周作人就把自己的一个铜章给磨了,然后让张樾丞刻了一个图章。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铜不许出口。所以就找到作协,作协还专门给出证明,最后把这章寄给谷崎了。现在在日本的文学馆里面还有这个章。
整理/雨驿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