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醒龙,1956年元月生于古城黄州。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三卷)、《蟠虺》,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出版有小说集《刘醒龙文集》、散文集《寂寞如重金属》等,共五十余种。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
近日,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刘醒龙新作《如果来日方长》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刘醒龙用亲身经历和处于一线的在场感受,写出这本长篇纪实散文,书中以理性客观的视角,详细描述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或熟悉或陌生的同城中人,与疫情决一死战的具体细节,用大量事实和实际行动表现了武汉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拼命”精神,使人理解为何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为何是“英雄的人民”。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武汉封城76天,身处武汉的作家刘醒龙的胡子也留了这么多天。最初蓄须是因为封闭在家里不用出门,因此不修边幅,但没想到事态发展到后来的情境,刘醒龙说自己就有些与新冠病毒赌气:“想看到底是新冠病毒害人的时间长,还是自己的胡须长得长。”
想不到,刘醒龙的胡须竟然蓄了两个半月,76天,在武汉解封的那一天——2020年4月8日零点,刘醒龙毫不吝惜地剃掉了。刘醒龙开玩笑地称自己当不了“美髯公”:“我的爷爷长着一把山羊胡,我自己如何能逃得脱爷孙之间的遗传?”
回望2020年,刘醒龙说:“疫情是一面很特殊的镜子,照出来的人间百态,没有一样是特殊的。对人的痴迷,不是生,也不是死,是从生到死的过程中,人道的苦行,人性的裸奔。”
2020年的水仙花不开
疫情之下,花且有灵,何况是人
散文集定名为《如果来日方长》,是因为刘醒龙之前曾为战“疫”歌曲《如果来日方长》作词,“被谱成曲后,反响还不错,自己索性将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重新构思写成一部18万字的长篇散文,篇名也叫《如果来日方长》。从老母亲在疫情高峰时患重病起,到二叔因为疫情次生灾害病故,尽可能从细微处入手,表现‘封城’之下一个武汉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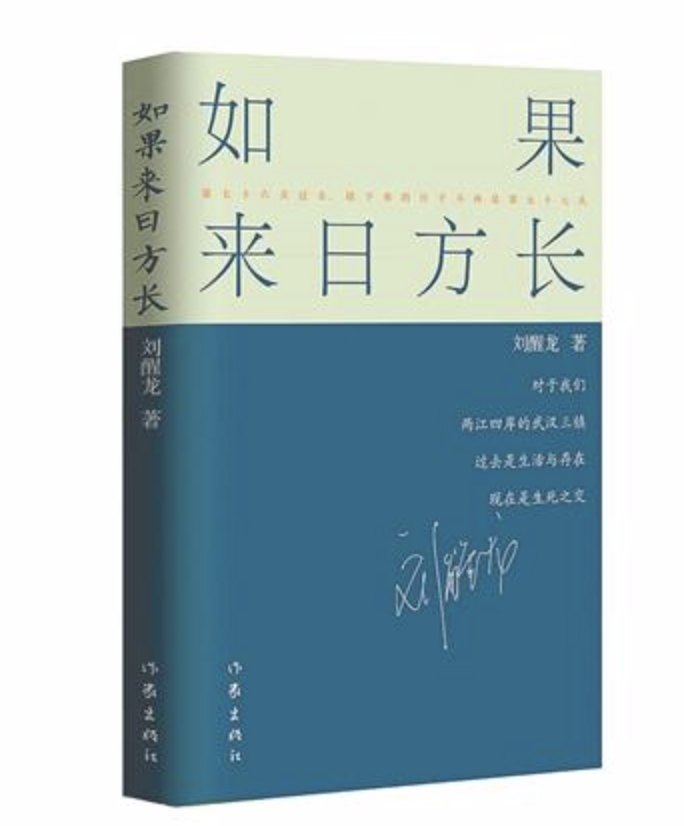
在歌曲《如果来日方长》中,刘醒龙写到了2020年的水仙花不开,写到了母亲的梦惊窗扉,父亲的酒才半杯。刘醒龙说困守孤城,2020年水仙花不开,是疫情后的那段日子里他最早写的句子。他透露,夫人的一位朋友年年春节都会提前寄来水仙,正好在过年时节开花,可是2020年春节收到水仙后,养了多时也不见开花。“《如果来日方长》谱成曲唱开后,有几个朋友说,原以为只是自己家里的水仙不开花,没想到你家的水仙也不开花。”
歌词中的“父亲的酒才半杯”,是有感于一位朋友。那位朋友的女儿是医生,要上一线了,朋友拿着酒杯,说是给女儿壮行,只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背过身去,落下的眼泪,反而比喝下去的酒还要多。刘醒龙说:“疫情之下,花且有灵,何况是人。朋友一家后来全都安好,对于这两句歌词,我们从不触及。人心之敏感,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有很多。”
刘醒龙还讲道,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将这首歌与战“疫”期间亲手拍下的各种图像一起做了一个短片,用于自己医疗团队的一个活动。“她在微信里只说,同事们都觉得这歌真好听!我当然晓得这话是不能说第二句的,便只回复谢谢二字。因为再说下去,必然是泪如雨下。疫情期间,我们家直系亲属中总体情况还算不错,就是老母亲病重,没法上医院,让人揪心。疫情刚过,老母亲一连三次报病危,特别是第三次,连ICU室都放弃抢救了,让转回普通病房,好让家人们在一起陪伴。熬了四十多天后,最终还是挺过来了。老母亲出院时,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朝她鼓掌,连连声称是奇迹。望着老母亲脸上重新出现的慈祥笑容,真的觉得母亲身上从头到脚全是奇迹。”
战“役”拼的是人间烟火,守的是市井街巷
在《如果来日方长》的“代后记”部分,记录了刘醒龙对于《文艺报》《中国新闻周刊》《楚天都市报》《南方周末》的“答记者问”。刘醒龙讲述说,“封城”之前,他患了眼疾,“封城”后没法医治变得日益严重,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以前睡眠很好的刘醒龙在疫情期间经常失眠,而为了补充能够增强免疫力的蛋白质,刘醒龙说自己在那段时间毫无忌口,吃下去的脂肪也比平时都多,结果熬到后来,体重居然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三公斤,由69变为66公斤。那段时间他还曾因为一次食物中毒折腾了十几个小时,“那种状态极像是中了新冠病毒的招,人几乎要崩溃了。”而他一位年轻朋友是预备役军官,奉命带领预备役军人支援火神山医院。“从火神山医院开建,到火神山医院封闭,整个过程用不着他出力干粗活,只需要在那里值守。从火神山撤下来后,从头到尾没病没痛的朋友整整掉了20公斤体重,“唯一原因是高度紧张”。
武汉“封城”期间,刘醒龙称自己家是“家大口阔”,一家三代六口人,第一次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这么久。“特别是头三个星期,方方面面都没做好准备,日常起居的不适应,生活物资相较缺少,心理状态的不到位,这么多人在一起,有时候几个小时没有一点动静,甚至该吃饭了,连喊几声也没人答应。那样的沉默让人深感不安。“好在身边有8岁的小孙女,总有机会将家里弄得像是开心乐园。加上家里人人都有活要干,有主持网站工作的,有替国外一所大学翻译急需资料的,有冒着疫情天天到单位上班的,还有上大学网课和小学网课的。正月十五以后,大家各忙各的,才真正缓过劲来。”
在刘醒龙看来,武汉历史上历经多次劫难都挺了过来。但从出人、出力、出物来讲,从来没有像这样,无论你是什么角色,处在何种位置,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同从未见过的病毒、从未有过的疫情抗争。面对新冠肺炎,不需要敢死队式的冲锋,但绝对人人都是上甘岭一样的死守。一千多万武汉人,留守家中,用生命的每一个细胞进行拼搏。有些事做了也就做了,没必要多唠叨。千家万户全都在一线抗“疫”。
刘醒龙的家人也在做志愿者,患了眼疾的刘醒龙自感“累赘”,也只有“在家庭防线上还能起点作用”。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他将自己从头到脚穿戴好,拎上一家六口的生活垃圾“慷慨”出门,“孩子们不让我干这事,但我自己仍一次不落地坚持做到‘封城’的最后一天,也算是为战‘疫’出了绵薄之力。一个人的健康无恙,就是封城战‘疫’的强大战斗力。每次放完垃圾,用一分钟时间,仰望夜空,深深吸一口气。隔着口罩,仍然感觉到星云之下,清新无比,如同那天夜里,一千多万人对着窗外同喊一声‘武汉加油’。”
刘醒龙表示,武汉在过去,对他来说是两江四岸的武汉三镇,是生活与存在,在经历疫情之后,则是生死之交:“2020年元月中旬,为了治疗眼疾,连续多天,没戴口罩,光着嘴泡在医院,不知多少次与新冠病毒擦肩而过,当时的那种后怕,真的是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心惊胆战,好在终究还是平安无事,这些记忆加经历,使人对这座越来越时尚的城市多了一些沧桑之感。”
最让刘醒龙感觉到刻骨铭心的是大年三十,一架紧急运送抗“疫”物资的大型国产运输机降落在天河机场。刘醒龙和孩子都是军迷,看到电视画面时,齐声叫道:“运20”来了!一声叫毕,禁不住热泪盈眶。刘醒龙说:“从‘封城’的那一刻起,全国人民就齐心协力,倾尽家底,给予支援。后来得知作为大国重器的‘运20’,全部都在飞往武汉,那种震撼感不是军迷很难完全体会。疫情期间,自己因为眼疾当不了志愿者,但也做了些事情。武汉降为低风险地区后,有新冠肺炎患者家人给我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我借故没有见面,就放在省文联办公室里,至今也不好意思打开看。有人建议送给抗‘疫’博物馆,我也不想那样做,那会更加不好意思。”
刘醒龙认为,武汉战“疫”拼的是人间烟火,守的是市井街巷,凡尘世态,点点滴滴,不似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也不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些不经意的由衷表达,显示出这座城市的细胞还很鲜活,人人都还是那么热爱生活、善于生活,压力再大也不会丧失对生活乐趣的追求和享受。一千万人都喊武汉加油,其实是在为自己加油。一千万人都宠爱热干面,其实是在集万千宠爱于自己一身。”
那天夜里,去江汉关送别“老对手”
2020年4月8日,武汉封城结束,刘醒龙回忆说:“零点一到,家里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夫人和孩子们有没有落泪,我顾不上看,松开手臂后,赶紧去卫生间,一边擦干净眼眶,一边剃去胡须。剃完胡须,家里人仍旧待在客厅里,一点睡意也没有。大约零点30分时,才突然起了去江汉关看看的念头。我们到江汉关时,已是零点50分,临江的街道旁有不少年轻人,在那里一次次腾空跳将起来,让同伴用手机抓拍。那一刻,自己突然想起,1948年春节前,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的抓捕,在汉口一家布厂当工人的父亲正是从江汉关码头上了小火轮,逃回黄冈乡下。江汉关一带是经常要来的,以往从来不曾如此联想过。常说细思极恐,自己这样子,大概是恐极细思了。我还想到1990年春节过后,自己在江汉关前与一位作家兄长握别,没过多久,那位兄长就病逝了。从古至今,江汉关一带由于是大码头,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别离。这么联系起来一想,2020年4月8日凌晨,大家都去江汉关,怎么就不是送别那个时常跳出来对人类进行一场全方位大考的老对手?”
疫情结束大家欢呼,问及是否在抗疫期间充满信心,刘醒龙说:“至于信心,也不是什么充满与充不满,人生本当如此。前些时,央视一个摄制组到我年轻时曾经待了十年的工厂采访,得知我在车间当车工时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感到很惊讶。他们先前采访过一些当过工人的文化人,称得上是好工人、合格工人的极少。所以,我理解的信心,无非是真诚面对眼前的生活,尊重努力劳作的自己与他人,不浮肿,不虚脱,为自己能够完成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而开心。我生性好孤单,武汉‘封城’后,仍有那么多人主动问候支援。有时候,深受感动也是一种信心。”
刘醒龙感谢很多朋友在疫情期间为他寄送防护物资,他说在“封城”之初,连医护人员都缺少防护用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帮他们一把。他将手机里全部联系人,从头到尾重新阅读一遍。只要觉得对方可能与医疗机构有关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短信或者微信发过去。“手指刷屏的那一刻,根本没有去想,自己这么做,合适不合适。武汉全城危情稍有缓解,心情踏实了一些,再想此前一系列冒昧唐突之举,竟然得到那么些作家同行的支持,想来只有一句话才能解释:同舟共济,相互信任!文坛很小,其间三六九个人,大都耳熟能详。文学很大,大到高山仰止,海阔无边。”
乱发肝火,乱用蛮力,太粗鲁了就不是文学
疫情结束后最想做什么,刘醒龙的答案是:“当然是先治好眼疾,目前为止,做了两次手术,扎了几十回针灸,服了一百多服中药,虽然眼科专家表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治愈概率,自己还是挺乐观的。我也不允许自己不乐观,因为一直想动手的青铜三部曲之二正等着我去写。”
疫情,显然让刘醒龙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他表示,人世与人生,其实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只不过疫情将这种变化放大了,让人人都能清楚看出过去与现在的不同。人类中的个体,孰优孰劣,标准就在于是进化、退化还是固化了。人的智慧是病毒比不了的,怕只怕有人将愚蠢当成智慧,所干下的蠢事,连病毒都会笑掉大牙。
而对于文学的使命,刘醒龙也有了更深的认知:“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现。越是遇上不同寻常的时刻,越是不能因情志不遂,乱发肝火,乱用蛮力,太粗鲁了就不是文学。”
刘醒龙认为,记录这个世界的种种罪恶不是文学的使命,文学的使命是描写罪恶发生之时,人所展现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爱;记录这个世界的种种荣光不是文学的任务,文学的任务是表现荣光来临之前,人所经历的疼痛、呻吟、羞耻与挣扎。文学做不到朗月,也做不到骄阳时,能做到星光满天也好。宁可眼下像星光般苍白无力,也绝对不要乱放邪火。
刘醒龙坦承,“封城”之下的文学是自己的一种探索,他找不到先贤留下来的现成经验,更不知能给后人提供哪些风范。在《如果来日方长》中,他虽然写了几位在火线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担起巨大职责的医护朋友,但他依然觉得,这不过是身陷火线的我们,用相对一手的文学元素,给未来的某个文学天才做些预备。“所以,我尽可能完整地写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比如,我熟悉的一位护士长,55天没有与幼小的孩子见上一面,每天在电话里互诉相思。好不容易从隔离病区出来,走到家门口,孩子却躲在门后,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奶声奶气地不要妈妈进屋,说妈妈身上有病毒。母亲也不让她进家门,隔着老远递上几样她最爱的美食,她就在门外的楼梯间里蹲着吃完后,转身重回医院。这样的人性该怎么审美,这样的亲情该如何抒发?不要说一部《鼠疫》,就是再用十部《鼠疫》也说不透武汉‘封城’的平常与特殊。”
而对于如何疗愈疫情带来的心理伤痛,刘醒龙回答说:“科学上的难题一般人解决不了,经济上的问题一般人解决不起,心理与精神上的伤痛,所需要的总是最简单的办法最有效:陪伴!我写这部《如果来日方长》,最重要的体会也是这两个字。”
供图/晓艺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