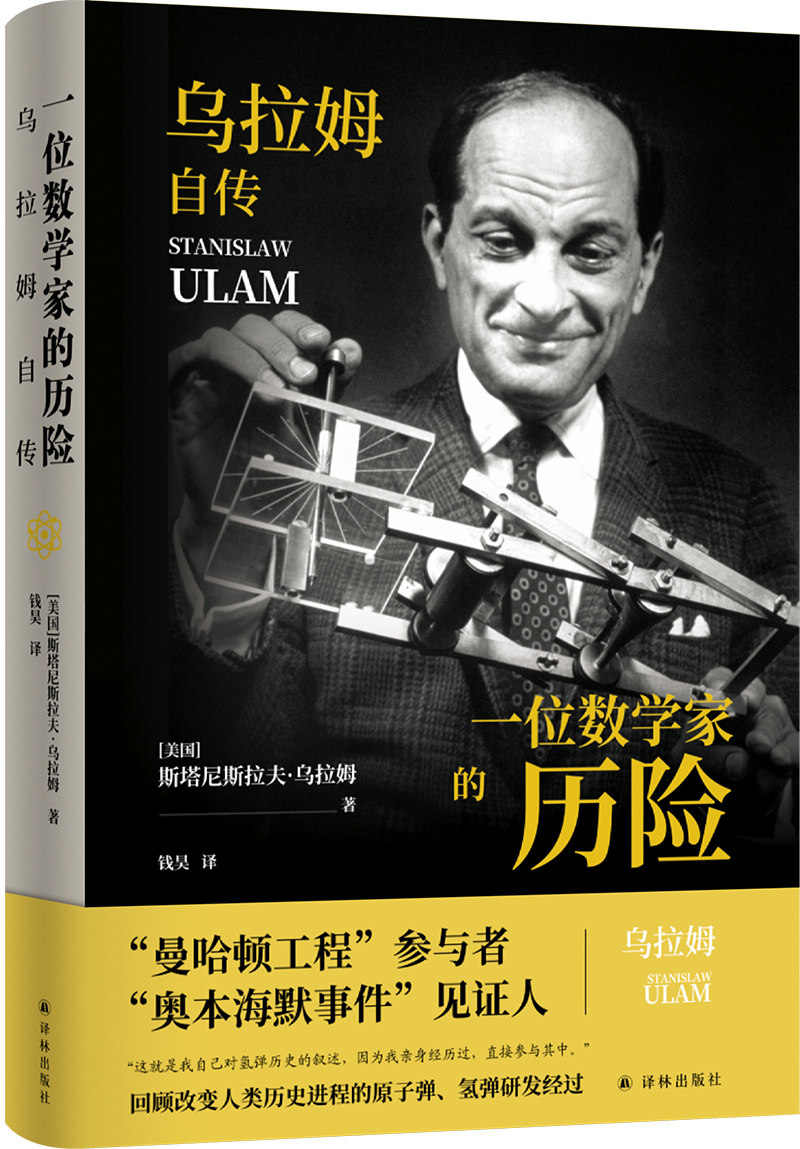1943年暮春,我写信给冯·诺伊曼,谈到了投身战时工作的可能性。我知道他已经参与其中了,因为他的信经常是从华盛顿而非普林斯顿寄来的。我做教学并不是很快乐,尽管我做了很多数学研究,也撰写论文、组织研讨会,并教授和战争有关的课程。我仍感觉时间浪费掉了,我觉得我能为战争做更多事情。
一天,约翰尼在回信中暗示说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正在进行,他不能告诉我是在哪里。他说他要从普林斯顿途经芝加哥到西部去,并提议说我可以到联合车站去和他面谈,因为火车换乘有两小时的间隙。这是1943年初秋时的事。
我如约前往,而约翰尼当然也按约定出现了。护送他的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就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他们显然是警卫员,这让我印象深刻,我想约翰尼一定成了重要人物,才会有这样的待遇。其中一名警卫员去办理车票手续了,我和约翰尼谈了起来。
约翰尼说现在有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工作,而我很可能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他依然不能告诉我是在什么地方,但他很频繁地在普林斯顿和那地方之间往返。
不知为什么,也许纯属偶然或是不可思议的巧合,又或是有先见之明,我开玩笑似的回答:“嗯,你知道,我对工程学或者实验物理学了解不多,我甚至不清楚厕所冲洗装置是如何工作的,只知道它涉及某种自催化效应。”听到这里,我看见他的脸抽搐了一下,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后来,我才了解到“自催化”这个词的确会在原子弹制造工程中用到。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个巧合。我说:“最近我一直在研究分支过程。”比如有一篇瑞典数学家发表的论文,是关于类似细菌繁殖一样的粒子倍增过程的。这个工作是战前完成的,是一个关于概率过程的巧妙理论。它同样与中子倍增的数学理论有关系。约翰尼又一次用近似怀疑和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惨笑了一下。
我偶然遇见了威斯康星的天文学家乔尔·斯特宾斯,他告诉我有一些和铀有关的工作正在进行,还谈到了从重元素中释放能量的情形。我怀疑是这个消息促使我下意识地发表了上述言论。
在这次于车站的会面中,约翰尼和我还谈到科学界在规划对战争有用的工作时,似乎普遍缺乏想象力,特别是在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计算方面。我指出,我对部分主要参与者的年龄有疑虑(那时,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在我看来就算老了)。约翰尼也认同其中明显有高龄因素。像往常一样,我们试图用诙谐的评论来冲淡忧伤,说应该有人出面组织一个“老年”协会,成员是那些对为战争出力感兴趣,但深受早衰或速衰之苦的人。
由于约翰尼除了说去西南部外,不能或不愿透露他具体要去哪里,我便想起了一则古老的犹太故事,讲的是两个犹太人在俄国搭乘一列火车。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你要去哪儿?”另一个人回答:“去基辅。”第一个人随之说道:“你这个骗子,你告诉我你要去基辅,好让我以为你要去敖德萨,但我知道你要去基辅,所以你为什么要撒谎?”于是我对约翰尼说:“我知道你不能告诉我,但你说你要去西南部,好让我觉得你要去东北部,但我知道你要去西南部,所以你为什么要撒谎?”他大笑起来。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战争形势、政治和世界局势;然后他的两个同伴都回来了,他就走了。
我和他又见过一次面,我想是在芝加哥,那是在我受到官方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名称不详的工程之前,这个工程很重要,研究与恒星内部有关的物理学。邀请信由著名物理学家汉斯·贝特签署。一起寄来的还有人事部门的一封信,详细说明了职位、薪水、审批程序,以及到达目的地的方式等。我怀着激动和热切的心情立即接受了邀请。
薪酬略高于我在大学里的收入,而且是以十二个月为基准支付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有五千美元。在那里,像贝特这样的专业物理学家的工资已经比大学的高不少了。我后来得知,来自哈佛的化学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拿到了据称天文数字般的九千或者一万美元。
我把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战争工程的情况告知了我的学校,并获得了在此期间休假的许可。
我的学生琼·辛顿在几周前已经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地方去了。琼上过我开的经典力学课,有一天她来到我位于北大楼的办公室,询问我能否在学期结束前三四周给她举办一次考试,以便她能参加某些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她出示了一封系主任英格拉哈姆教授的信,信里授权我可以这样做。她是一个好学生,一个相当古怪的女孩,金发、健壮、漂亮。她舅舅是英国物理学家G.I.泰勒,她还是19世纪著名的逻辑学家乔治·布尔的曾外孙女。我就在信封背后写了几个问题;琼拿了几张纸,带着笔记本席地而坐,写完了她的答卷,通过了考试,随后从麦迪逊消失了。
很快,我熟识的其他一些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没有说去哪里就消失了。这些人中有在咖啡馆认识的人、年轻的物理学教授以及研究生,包括戴维·弗里施及其妻子罗丝——她是我微积分课上的一名研究生、约瑟夫·麦吉本、迪克·塔舍克等人。
最终,我得知我们要去新墨西哥州,去一个离圣达菲不远的地方。由于从未听说过新墨西哥州,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联邦作家项目的《新墨西哥州导游指南》。书封底的借阅卡上有借阅者们的签名,我看到了琼·辛顿、戴维·弗里施、约瑟夫·麦吉本和所有其他因机密的战争工作、没说去哪儿就神秘消失者的名字。我就以这样一种简单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在战争时期要保证绝对机密和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和斯特宾斯很熟,在到达洛斯阿拉莫斯大约一个月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没有说我在哪儿,但提到了时值一二月份,我在地平线附近看到了老人星。事后我想到,作为一位天文学家,他能够很容易地推断出我所处的纬度,因为老人星是南天的恒星,在北纬38度以北是看不到的。
我们订车票时遇到的问题这里就略去不谈了。即使我拥有优先权,我们还是被拖延了将近一个月才出发。在火车上,为了给已经怀有两个月身孕的弗朗索瓦丝弄到一个卧铺位,我不得不给售票员一笔小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我想也是最后一次“贿赂”别人。
我们到达了一个遥远的、人迹罕至的、毫不引人注目的小站,新墨西哥州的拉米镇。令我无比惊讶的是,在那儿迎接我们的是杰克·卡尔金,一位我很熟识的数学家。几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遇见了他,之后又见过很多次面。卡尔金曾是约翰尼的助手,并和他一起去伦敦讨论空中投弹模式与方法中的概率问题。就在几周前,他加入了“曼哈顿工程”。他是个高个子、外表帅气的男子,比多数数学家更会为人处世。听说我要来,他从军队的车辆调配场借了一辆汽车,开车到火车站来接我们。
阳光很明媚,空气清爽而令人陶醉,虽然地上有很多积雪,但仍然挺暖和,与麦迪逊的严冬形成了可喜的对比。卡尔金开车带我们进入圣达菲,我们在拉方达酒店停下来,坐在酒吧间低矮的西班牙式桌子边吃午饭。吃完一顿有趣的新墨西哥州风味的午餐后,我们走到了中央广场附近一条小街上一栋一层建筑的门口。在一套简朴的房间里,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妇女请我填写了一些表格,然后在一台老式台式机器上转动曲柄,制作出了我们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工程”的通行文件。这间不起眼的小办公室就是通向庞大的洛斯阿拉莫斯复合体的入口。此情此景很像英国那种“斗篷与匕首”式的涉及秘密行动的悬疑故事,勾起了我小时候为这类故事着迷的回忆。
开展工程的地点在圣达菲西北大约四十英里处。旅途有些让人提心吊胆,杰克特意想让我们领略一下乡村景色,于是带我们抄了一条近路,这是一条泥泞的小道,周围稀稀拉拉地分布着一些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的村落,走完这条路,我们通过了格兰德河上一座狭窄的木桥。
周围的环境富有浪漫色彩。我们向上走啊走,进入了一片由平顶山、峭壁、矮松和灌木丛组成的奇特而神秘的景观。随着海拔的升高,眼前出现了一片松树林。在铁丝网围住的一道军队大门前,我们出示了通行文件,而后车开进了一片坐落在泥泞而未铺砌的狭窄街道边的杂乱的一层或二层木质建筑之中。
我们分到的是池塘边的一间小木屋(他们承诺等更大的宿舍盖好后就给我们更换)。之后我就跟着杰克初次参观了技术区域。
我们进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我惊讶地发现约翰尼正在全心地和一个中等身材、浓眉、表情严肃的人谈话。他在一张黑板前面踱来踱去,稍微有点儿跛脚。这人就是爱德华·泰勒,约翰尼把我介绍给他。
他们交谈的内容我只能懂个大概。黑板上有一些极长的公式,把我给吓住了。看到这些复杂的分析,我目瞪口呆,担心自己永远无法为之做出任何贡献。但日复一日,那些方程式一直留在上面,而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几个小时就会变化一次,这让我重拾了信心,有了能为这些理论工作添砖加瓦的希望。
我能听懂他们对话的一些片段,一个小时后,约翰尼把我拉到一边,正式而清楚地向我解释了这项工程的本质与现阶段的状况。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是两三个月前才认真开展起来的。冯·诺伊曼似乎非常确信工程的重要性,而且流露出了对这项事业最终能获得成功的信心,它的目标是制造出一颗原子弹。他给我讲了考虑过的关于提炼可裂变材料的问题,关于钚的问题(虽然当时洛斯阿拉莫斯还连一丁点儿真实存在的钚都没有)的各种可能性。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几个月之后我看见罗伯特·奥本海默兴奋地从一条走廊上冲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紧跟在他后面。他把瓶子底部几滴神秘的物质展示给大家看。一扇扇房门打开了,人们聚拢过来,进而窃窃私语,大家兴奋异常。这是实验室第一次拿到了钚。
不用说,我很快就遇到了大部分先于我从麦迪逊神秘消失的威斯康星的熟人。我第一天就碰见了汉斯·贝特,我对他的了解要比对泰勒的多些。我逐渐认识了整个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团队。我之前已经认识了许多欧洲和美国的数学家,但还不认识那么多物理学家。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