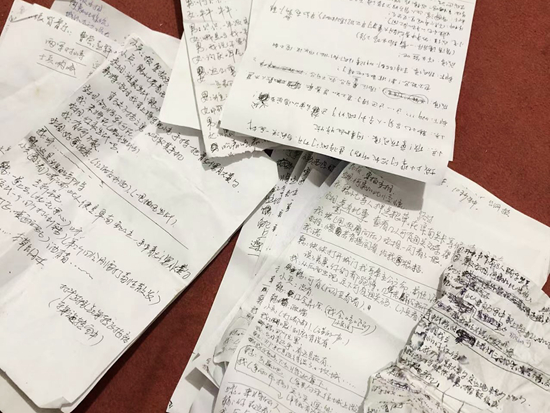“报——”
一名“士兵”推门而入,惊飞了院里的鸡群。
披着被单的“丞相”拍桌站起,一口安徽方言道:“何事如此惊慌?”说话间,用手空捋着胡须,胡子只在上唇,是用墨水画上去的。
“禀报丞相!”“士兵” 神情肃穆,挂着凉席铠甲,戴一顶塑料油壶头盔,带回前线的消息:“西凉大军前来攻我城池,正在城外叫喊!”
这批大军,是一众以锅盖、木叉、锄头迎战的老妇人。
事实上,没有哪个将军会任用一群年过六旬的老妇做战士。但这就是32岁的“导演”鲍小光拥有的全部资源:老人、残疾人、割完的稻草、用尽的油壶、父亲放弃练字后剩下的墨水和女人们灶台上的锅盖。
他的片场是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村庄。从去年开始,鲍小光自编自导了一系列以“三国”为背景的短剧,在社交平台上获赞不少。
剧组
一个专业的剧组,包含制片、导演、演员、摄像、服化道、美术、动作指导等各类人员,但鲍小光想得简单。
他的剧本只有一张A4纸,写着简单的剧情和台词。
三国古装剧要靠扮相,但也能就地取材。揪一把草,团一团系在头顶上,就是古人的发髻。一个5升的空油壶,刚好装下一个脑袋,于是剪出一块脸的空缺,其他部分用墨汁涂成黑色,倒扣在头上,像样的头盔就有了。再把蛇皮袋撕成条絮状,绑在瓶口,头盔上的红缨流苏也有了。衣袍是旧床单,战甲是凉席,观战的望远镜是两个绑在一起的矿泉水瓶,鲍小光还给加了根绳子,方便挂在脖子上。
他要做出一个纯“草根”的作品,道具既要像,也要不那么像,“它是一种创造”。因此不愿网购道具:一是“太贵”,二是“太真”,反而失了乡土特色。
一切准备就绪,最大的难题只剩下人。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小孩。鲍小光甚至觉得,村里90%的年轻人似乎都“消失”了。
选择演员的标准只有一个:有时间。
住在对门的李东华因此成了主演的最佳人选。他是鲍小光的远房舅舅,64岁,中年丧妻,晚年丧母,3个女儿都嫁出去在外打工。他常年独居,白天总是关着门生活。虽然住对门,鲍小光也不怎么见他。
一个人生活,饭是随便对付的,有时一天一顿,有时一天两顿,但酒是准时要喝的,离不了。李东华高兴了喝,觉得生活“一言难尽”了也喝,喝醉了就抱着母亲的遗照哭。以前这时候,母亲总一边批评着,一边把茶水送到嘴边来。如今“没人管了”,他“爱喝就喝”,人才90斤,血压就到190,一斤白酒配一天的生活,直到鲍小光来敲门。
一个简易的剧组慢慢搭建了起来。摄像师是鲍小光在村里临时找的朋友,他因疫情原因暂时留在家里,没出去打工。他们在李东华家的院子里“安营扎寨”,情节简单,只有“禀报丞相”的戏份,以两人对话为主。李东华知道自己演的是“丞相”,却不清楚“丞相”是什么意思:“没打过交道,不认识。”
在片场,鲍小光要一边酝酿着情绪当演员,一边当导演,给不识字的“丞相”说戏。李东华总是记不住台词,眼神和动作要导演一一讲明。“先看书,再看前面啊。”李东华神色紧张地拿着竹简答应着,鲍小光又纠正:“要低头看。”于是他像个听话的孩子,认认真真把头再低下去一点。台词有时说着说着就愣了神,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看向导演:“又忘了……”鲍小光就会再给他提醒一遍。
后期制作也是现学。鲍小光找到一款好上手的剪辑软件,大概琢磨了一周,就“出师”了。
视频发布后,他的粉丝从百十个变成几千,又涨到两三万。一位老同学看到后,还给鲍小光捐赠了10套服装,一些假发。
导演
在成为“导演”之前,鲍小光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厂工、一个失意的歌手和一个有着创作想法的装修工。
2006年的鲍小光只想去打工,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16岁初中毕业,他如愿以偿,跟堂哥进了江苏的帽子厂。
厂里有联欢活动,鲍小光喜欢上了唱歌。他每月挣七八百元,索性花一百多元买了架电子琴,下班琢磨编曲,不大懂乐理知识,只靠感觉写了两三首情歌。
1年后,他厌倦了工厂生活,在网上看到北京有唱片公司招人的消息,决定成为一名“歌手”,辞职北上。
来京后,数次应聘被拒,他的艺术之路中断,钱也几乎花光。为了“吃饭”,鲍小光在中关村附近的湖北菜馆干起了服务员,那里食宿全包,下了班可以回宿舍继续琢磨写歌。但最后一桌客人吃完饭总是将近凌晨,“太熬人”。
写好歌,鲍小光要找录音棚录歌。一首歌的制作费用是三四百元,交付的作品是一张碟片,鲍小光回去放给室友听一下,“感觉挺不错”。他当时月薪只有1500元。
为了多挣点,鲍小光又辞职去了装修工地当“小工”,每月能得四五千元。一开始搬材料,运东西,后来又随朋友去郑州,做室内墙艺。
那时他不再写歌,把兴趣转移到了墙面,用硅藻泥涂料在墙上作画。这是他中学时的兴趣,受父亲影响,他爱好画画和书法。但也和父亲一样,没坚持下去。
在外漂了10多年,鲍小光没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一个身份。“一会到这儿,一会到那儿,钱也没挣到。”因为“买不起房”,谈了多年的女朋友跟他分了手。鲍小光决定回家。
回乡后的一年,他开了一家装修公司,但客源不多,倒闭时又赔了些钱。之后几年,就零零散散跟着装修队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干完活回家睡觉。挣不到钱,找不到对象,一无所成。”
现下家里只剩他一人。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时回来。弟弟在浙江工作,结婚生子后,母亲便过去帮他带孩子。“农村就是这样。”鲍小光说。
2020年,鲍小光接触了短视频社交平台,当时已经有几位当地的网友拍乡村短剧,还因此有了些收入,这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初到北京时,他曾找中介应聘过群众演员,但最终不了了之。
2021年春节过后,在做装修吊顶的间隙,鲍小光就开始谋划,决定成为一名“导演”。
演员
鲍小光剧组里的人,要么是从外面回来的,要么是出不去的。
因为疫情,邻村邻镇很多人赋闲在家,有感兴趣的,就主动找上门来客串。鲍小光的父亲回来割麦子,也饰演过站在门口的卫兵。
34岁的韩小七看到了鲍小光的视频,立马来了兴趣。他2016年结束北漂返乡结婚,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就在镇子里住了下来,从事电商生意,在网上卖牙膏一类的日用品。疫情后,快递物流时常停摆,生意停滞,多了许多闲暇时间。于是给鲍小光发了私信,骑上电瓶车就去找他。
韩小七加入剧组后,扩充了剧本的“对敌”情节。他常常饰演刺杀“丞相”的反派角色,与鲍小光饰演的“将军”正面对峙。两位主将以自行车为“马”、电动车为“赤兔马”,挥舞着挑稻草的木叉和浇菜园的粪勺对打,最终往往是反派倒地而死,或者撒一把面粉“隐身”而逃。
鲍小光不会写分镜和脚本,镜头切换和动作衔接都是临场发挥,边拍边想,一场十几秒的武打戏要拍一天,“非常难”。因为只有一个机位,同一个动作要做三四遍,换不同的角度拍。
直到今年7月,韩小七为了孩子上学,把家从镇上搬到了县上,渐渐退出了剧组。同月,鲍小光的同村表姐卢帝回乡。
她今年40岁,在外打了25年工。她1996年就去了深圳,进过雨伞厂、玩具厂、服装厂,摆过地摊,卖过麻辣串,后来辗转到上海,开了一家卖牛肉汤和黄焖鸡的小饭馆。疫情期间,生意“不太好做”,她把店转让出去,回到老家,担任起鲍小光剧组的摄像、演员和场务。
卢帝的贡献,还在于以女性带动女性,让鲍小光的剧组第一次有了大规模群演:一群五六十岁的女人。
这对她来说并不难。她平时就在村里与人交好,只需联系好一两个,阿姨们呼朋引伴就来了,甚至包括75岁的老太太。
当卢帝第一次找到61岁的段金兰时,段金兰不知所措:“俺不知道弄啥,俺不敢去。”后来卢帝讲“不要紧,就跟玩一样的”。段金兰半信半疑地去了,许多人和她一样,戴着帽子口罩,怕被人认出来说闲话。
到了现场,“人家说咋弄就咋弄”。她们通常饰演卢帝的“小兵”,站在她身后,举着木叉铁锨一类的“武器”示威助阵,没有台词,只设计一些简单的动作,唯一的要求是整齐。
对于老妇人而言,这也并不简单。不说“万箭齐发”,光是单膝跪地准备射箭,也是跪下难,起身也难。“年纪大了,只能耐心慢慢教。”几个小时下来,鲍小光喊干了嗓子。作为报酬,他会给每个群演30元补贴。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鲍小光翻拍了空城计、草船借箭、三英对吕布、败走华容道等经典桥段,有时还根据社会时事热点自创情节。制作周期也稳定下来:通常花三四天写剧本,两天拍摄,两天剪辑,最终的视频时长要控制在1分30秒以内,这是他验证过播放量最好的时长。
为了让观众有新鲜感,鲍小光不断想着新方法。他把手机绑在竹竿上高高举起,增加俯拍画面,又不断更换拍摄场景。今年3月,他在湖边用茅草搭建了草棚,拍了几条视频后,下雨草棚被风吹倒了。10月,他又重新用稻草做了城墙,旁边拉着钢丝固定。
如今鲍小光有42万粉丝,短视频每月能给他带来几千元的稳定收益。播放最多的一条视频,为他增加了15万粉丝。有朋友建议他接拍具体的广告,一条能再挣几千元,但鲍小光拒绝了,“我希望我的账号里,全是好看的视频”。
村里出了“名人”,村支书希望能借助这个机会,把村里的牛羊肉等农产品推广出去。这也是鲍小光的初衷之一,他在初期就发布过一条视频:“丞相”行军路过中岗镇,特命属下驻留3日,品尝当地牛羊肉。
村庄
乡村剧组特殊之处还在于:群演的优先级比主演更高。
鲍小光总会把群演的戏份安排在前,下午一点钟开始,四五点前就要结束,因为她们多数要去接孙子放学——这是日常中最重要的任务。
段金兰1人带了3个孙子。这3个孙子分别在3所学校上学,老大在镇上读初中,老二和老三分别在镇上和村里读小学。段金兰每天骑着三轮车跑4趟,早上6点送两个大的,8点回来送小的。下午3点多接完小的,4点半又去接两个大的。
她这辈子带大了6个孩子,两儿一女成家后在外打工,她又开始带孙子。从前的孩子倒是好带,大人做事时,就任由小孩在地上爬,“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这样”。但现在,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不挨着土”,必须干干净净地带大。小孙子缠得顾不过来时,她上厕所的空儿都没有。孩子一离人就哭,她常常是听着哭声做饭。
段金兰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3顿饭,吃3顿药——降血压的药,降血脂的药,治手指风湿的药,和缓解脑供血不足的药。现在入了冬,又要腌萝卜干咸菜,孩子们过年回来爱吃。但她没功夫种那么多萝卜,于是到镇上买了四五十斤,回来全部切成条,切了20分钟,胳膊就“疼得不行了”。
老伴4年前过世后,她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也很少在村里走动。拍视频几乎是她唯一的公共活动,也是唯一的娱乐。但乐什么,好像也不知道——她没看过三国,压根不懂“群演”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好玩”。 一把年纪了,做着这些奇奇怪怪的扮相,一人出了差错,大家都捧腹大笑。回来还能“上电视”,在手机里看见自己。
段金兰的小孙子也“高兴得不得了”,指着视频里的“小兵”奶奶们挨个儿认。
平日里左右邻居聚在一起,“都是叙这个事儿”,一边看,一边笑。
以防万一,段金兰总在拍戏前提前招呼邻居一声:要是“拍电视回来晚了”,就劳他费心把孩子捎回来。这一个月来,3个孙子总有几天回家见不到奶奶。进了厨房,不仅没有热粥吃,灶台上的锅盖也不见了。
到后来,女人们“越去胆子越大”,基本找谁谁都去。拍完了还说:“下次再拍叫我啊!”
卢帝爱美。在村里生活,她照样涂着美甲,戴着戒指。雨天在家闲着没事,又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后来穿古装上镜,有网友在评论区提意见:“不太好看”。她就上网花100多元买了假发,七零八落地贴在头上,配上舞刀弄枪时凶狠的表情,更显得滑稽了些。但她不怎么在意。
放在以前,如果没有“美颜”,她从不上镜。自从在村里拍戏,她的想法变了些:“拍这个就是要真实。都是老家这些人,出门人家都认识你是谁,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美丑不论,“玩得开心就好!”
“丞相”李东华也不再感到害羞。他去商店买东西,有人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上来就喊:“丞相!”。李东华非常诧异:“你怎么知道我是‘丞相’?”那人掏出手机,李东华也掏出手机,一部一百来元的老年机和一部几千元的智能手机对在一起,那人说,“你这不行,我这儿能看到!”
鲍小光去坐公交车,连司机也会问:“‘丞相’怎么没来?”后来上街吃油条,小摊的老板也冲李东华笑,叫他“网红”。
李东华没想当“网红”,只是感到镇上多了许多认识他的人,人们都来跟他说话。他只觉得热闹,并喜欢这场热闹。
文/杜佳冰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