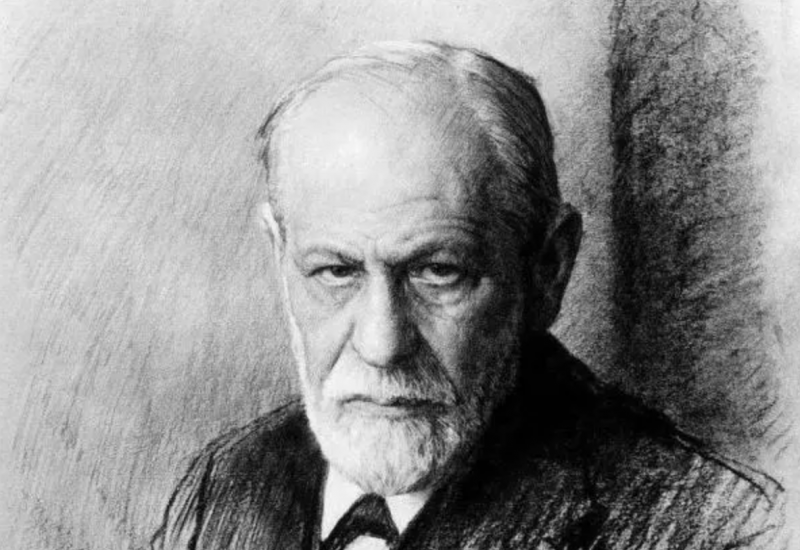梦境世界给了我们太多启示,因为梦境无意间流露了人的自然天性,暴露了人的生命本相,这也是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的价值所在,以及意趣所在。解读梦境便是等于打开了人世的黑箱子,生命的黑匣子。
而且梦境与文学有关,这太有意思了。以至于弗洛伊德在解梦的时候,一方面是拿他所经历过的那些病例来演示,更重要的则是经常拿文学作品来说事。他的最经典的概念中,有很多都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分析来提出的。
弗洛伊德
这次,我们看看弗洛伊德以及博尔赫斯是如何解读莎士比亚笔下的著名人物克劳狄乌斯的伪善之梦。
本文选自张清华所著《春梦六解》。
他恐惧地破解着镜子里面恶魔般的形象,
他的没落和他命运的反影。
我们就是俄狄浦斯……
—— 博尔赫斯:《俄狄浦斯和谜语》
一、表面上最讲究道德的人,没准儿就是伪君子
思路不知为何,忽然又跳回了故乡,想起了关于故乡的人和事。笔者的老家是在山东博兴,汉代以前,这里属“千乘”地界。千乘者,自然是从“千乘之国”得名。博兴紧挨着齐都临淄,兴许是因为有重兵屯驻,战车千辆,故称作千乘。处都城旁侧嘛,自然有拱卫之责,拱卫都城,当须要有重兵。这个不算考证,只能算是瞎猜。我只是想说一个故事,《搜神记》中所记的作为“千乘人”的“孝子董永”的故事。该故事现被乡人恣意夸大为信史,还造出了“董府佳酿”之类的名酒。这都罢了,我故乡的人捕风捉影编故事,不过图点利益,为文史乡俗添点儿材料,为地方文化和旅游多添个噱头罢。然现代以来不惮以恶意编故事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非要捏造出一个苦大仇深的董永来。
《搜神记》中的原话说,这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说的是,董永家贫,为了葬父,宁愿将自己卖为家奴长工,但买了他的人却认为他是个孝子,给了他一万钱就叫他走人。兴许是董永运气好,但归根结底还是笔者的乡风自来淳厚,并未有吃定他当牛做马的恶人。而董永也确乎格外讲究信义,为父守丧三年后,定要报答主人,回到买主那里去做工。
永其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
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年轻人的好品行感动了上天,天帝定要帮助他,于是路上出现了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愿做你的老婆。就随董永一起到主人家去。而主人全然没有霸占董永的意思,反倒有点不解说,已把钱奉送阁下了呀。董永答曰,蒙主厚恩,小人没有理由不来报答。主人无法,便问他的女人能干什么,董永说:“善纺织。”主人便说:“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来报答我的话,就让你太太给我织一百匹双丝细绢吧。”一百匹,自然不是个小数目,想来织工差不多也刚好值那一万钱,要么就是这主人有点卖乖的意思了——你这么固执地要报答我,那我姑且就给你个难完成的活儿。设想,即便如此,如果一年半载织不完,主人也必不会为难于他。
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纺织,十天即织完了。
该处省略了大量的故事细节:比如董永卖力干活,永妻日夜兼程,但绝无主人欺压,小夫妻备受煎熬之事,也未见天帝专横,非要拆散人间夫妻的凶恶面目。
然小女子出门后即对董永说,妾乃天上的织女。只是因郎君为孝子,感动上天,天帝才命令我来帮你偿还欠债的。说完腾空而去,一溜烟不见了。
这董永和仙女似乎也属于涸辙之鲋的那种情分,苦难时相濡以沫,大水一来则相忘于江湖。分别时,也并无生生死死的悲悲切切。而戏里所编造的财主的凶恶,便纯粹是道德的谎言了。想来世上还是好人多,你尊我一尺,我还你一丈。董永和财主都属于这样的人。这才是正经八百的淳朴古风,也是我爱的厚土故地。
因此,某种程度上“教化”在文学中,经常会变成一个虚伪的命题。表面上最讲究道德的人,没准儿就是伪君子,过度执念于道德的命题,于真正淳厚古朴的民风来说,不啻一种败坏,它无意识地将人性中的恶夸大并唤醒了。人与人之间变成了欺压的关系,背信弃义的关系,横加干涉的关系,损人不利己的关系……你说这戏码儿,到底是教化人呢,还是误导人?想来《搜神记》之所以没有写到那诸般人性之丑和恶,大约不是这干宝刻意要“麻痹人民”,掩盖阶级斗争,而是那时确乎较少背信弃义之人与薄情寡义之事罢。社会风气没有那么坏,讲故事的人自然也就想不到那么多。
无独有偶,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一节,是开篇处的故事,叫作《狐语》,说的是沧州有个叫刘士玉的读书人,家里有间书房被狐狸精所占据。这家伙通人语,白天还可以同人对话,甚至胆大妄为到可以揭墙上的瓦块打人。彼时,这里的州官叫作董思任,是个好官,也是个好事儿之人,便亲自前来要驱这狐精。他到了之后,即“盛陈人妖异路之理”,换成今人的话说,就是“大讲科学道理”,但就在此时,那家伙说话了。
忽檐际朗言曰:“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咄咄不怡者数日。
这妖孽也颇有一套,它不像人,喜欢冠冕堂皇从高处谈,而是用了“底线思维”,说你这州官虽然廉洁爱民,但也不过是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你爱民不过是希图个好名声,不贪不捞也是怕以后有麻烦罢了,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鸟么。所以在下我也就不回避你,但你也不要自作聪明,唠叨个没完,说多了倒叫自己尴尬也。
哈哈看官,你道这畜物是好惹的么?讲起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用高尚和科学的大道理都对付不了它。州官狼狈而归,很没面子也很不高兴。最后咋办?还是底线思维,用粗蛮之人对付这等妖魅之货。“刘一仆妇甚粗蠢,独不畏狐。狐亦不击之。或于对语时,举以问狐。狐曰:彼虽下役,乃真孝妇也。鬼神见之犹敛避,况我曹乎!刘乃令仆妇居此室。狐是日即去。”州官前番折了一次面子,这一招则扳回了一局,着一粗使丫头来书房里住下,该女佣不畏妖物,狐精自然也奈何她不得,反而说,她虽属下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孝妇,对这样的人,便是鬼神也要畏惧三分,何况我辈呢。说罢溜之大吉。
这故事依在下看来,也是同样道理,凡事别把道德看成是一高出人间之物,常用底线思维有好处。动辄以高不可及的道德要求人,到底不是有效的办法。想来吾族人之所以常飙高大口号,却常有置倒于路边的翁妪于不顾的奇闻,大约也是因了这般缘由罢。
二、真正的要害在于,扮演者会“由梦境延续至现实”之中
笔者以前总疑惑,为什么人在童年时的梦总是非常清晰,早上起来,可以和自己的祖母或姨妈,毫不含糊地讲出梦中的情景,且讲述时并无编造,哪怕是本能的编造。而到渐渐成年之后,梦却变得愈来愈模糊,最终竟然无法讲述。有时明明在梦中记得很清楚,甚至在梦中就开始整理记忆了,告诉自己,希望可以清晰地记下来,但眼睛睁开时,那个原本似乎清晰的梦突然飞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先我总认为,这是因为人的记忆力衰退的缘故。因为人渐渐长大时,脑子里储存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像一台存了太多东西的旧电脑,渐渐运转不灵了。但现在我想,问题可能还不仅仅在此,而是在于“梦境检查制度”的渐渐严苛。随着人的长大,逐渐的世俗化和社会化,“自我”这东西渐渐变得皮糙肉厚,他以理性的面目自居,就像个愈老愈刻板严厉的门卫,将这尴尬的“本我”看管得愈发紧了,而“本我”呢,那原本活跃的肌体也渐渐丧失了率性,而不得不更加学会伪装,在复杂的乔装改扮之后才得以出笼。如此,梦境中的形象,便变得越来越暧昧模糊,难以记得起来了。
而且在梦醒时又多了一层检查,这同样是无意识的。所以醒来的刹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梦是不合伦理或规制的,或是比较无趣,对自己不利的,便在“开机”时即出现了一个“删除”动作,或者叫“刻意遗忘”,变成了乱码,所以梦也便记不起来了。
这和人性中“只记得过五关斩六将,不记得走麦城”,是不是同一个道理?谁都愿意记得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不愿记起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特别是坏事情。所以,不止记忆是选择性的,连梦境的保留与否,也变成了选择性的。
而这便是在下的发现了,也是他——我们的主人公,“黄昏的君主,做梦的国王”,克劳狄乌斯的逻辑。这十恶不赦的家伙,在达到了目的之后,最想做的就是“洗白”自己。如何洗白?那便是演戏,演一个至为宽厚与睿智的仁君,演得越像越好。于是,他在王子哈姆莱特和王后——从前的嫂嫂、而今的妻子面前,努力扮演了一个仁慈的父亲和丈夫;在其他的大臣面前,则努力扮演着一个明君圣主的角色,他演得很像,完全入了戏,以至于自己也都相信了自己。每当年轻的王子向他恶语相向出言不逊时,他几乎毫不介意,绝无愠怒,话里话外都透着善解人意的体恤和宽容。以至于连我们这些观众都有点晕了,觉得年轻人是有些过分了,如此气量狭小而目无尊长,怎么能行?
克劳狄乌斯
其实哈姆莱特之所以装疯,除了猝然失去父亲的悲伤与惶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来自此人之伪善的压力。如果不疯掉,他便无法面对这伪君子,也无法对众人揭破他的把戏。因为当他从德国威登堡大学急切回到丹麦奔丧之时,奸王已然坐定了王位,变更了朝纲,甚至还娶了王子的母亲,变成了哈姆莱特“新任的父亲”,满朝文武都已臣服于他,母后已然与他同床共枕,连昔日那些交好的同窗兄弟也都早已投靠。你让这年轻人如何能够淡定,如何能够单靠过人的理性和头脑来应对呢?
所以他只好不惜败坏自己完美的形象而“佯疯”,以缓解痛苦、无助和焦虑。五百年后的博尔赫斯洞悉了这一切,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镜子》,其中专门分析了“伪善”的秘密机制。回想近三十年前,当我初次读到它时,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几句的厉害;后来许多次重读,也依然没有真正领会个中深意;直到十年前我在精神病院里遇到那“道德伪善狂”的一刻,在与医生的对话中,似乎猛然间受到了什么刺激,一下子醒悟过来了。
这是篇幅很不短的一首诗,它在反复展开地分析了“各种形态的镜子”之后,忽然冒出了这几句:
克劳狄乌斯,黄昏的君主,做梦的国王,
他并不觉得自己在梦中,直至那一天,
一个演员用哑剧在舞台上
把他的罪孽向世界献演。
我从未感到有如此突兀、令人警醒的震撼。我意识到,老博尔赫斯之所以说他是“做梦的国王”“在梦中”,是说他在扮演,他彻底进入了角色,而并没有觉得,或者早已忘记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镜像。他毒杀了兄长,骗娶了嫂嫂之后,便一直立志和励志要做一个好的君王。所以无论哈姆莱特如何用恶毒和不堪的话语来攻击他,他都不曾生气。他甚至连自己也相信了“他编织的童话”——一如舒婷当年送给顾城的诗中所说,“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什么时候他的梦碎了?那就是哈姆莱特导演了那一幕哑剧,将他的罪孽“向世界献演”。那一刻他真的好像是被剥光了衣服,赤裸裸地现形在了众人面前,他大叫着从现场逃掉了。
然而在梦醒来之前,他扮演得分毫不差。即使是王兄尸骨未寒,他就已急不可待地迎娶王后之时,他也能够将这无法说通的鬼话,说得听起来无比得体,如天花乱坠。
虽然我们亲爱的王兄哈姆莱特新丧未久,我们的心里应当充满了悲痛,我们全国都应当表示一致的哀悼,可是我们凛于后死者责任的重大,不能不违情逆性,一方面固然要用适度的悲哀纪念他,一方面也要为自身的利害着想;所以,在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之下,让幸福和忧郁分据了我的两眼,殡葬的挽歌和结婚的笙乐同时并奏,用盛大的喜乐抵销沉重的不幸,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当今的王后,这一个多事之国的共同的统治者,结为夫妇;这一次婚姻事先曾经征求各位的意见,多承你们诚意的赞助,这是我必须向大家致谢的。
好个“让幸福和忧郁分据了我的双眼”,“用盛大的喜乐抵销沉重的不幸”,他厚颜地将无耻装扮成了坚忍,将贪欲的图谋偷换成了责任,甚至还将这小人的僭越演成了君子风度,将卑鄙的谋杀犯说成了悲情的“后死者”。
这是世界上最具绅士气质的不要脸了吧。自我的道德化,是骗子的拿手好戏,他演得真可谓滴水不漏,完美。中国的夫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而这家伙是把好色硬说成了好德。这提醒我们,如果世界上有人将欲望当德行说,或是以德行的名义来实现其贪欲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还有一点,语言也是如此地可疑,想想这完美的效果,不是首先来自他奇妙的“话语转换”么,是过剩而漂亮的修辞,将这悖谬和无耻成功地转换为了合法与合道德。
而完成这一话语转换的语言大师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老莎士比亚。
当然,除了道德,最好还要再加上理性。克劳狄乌斯深知“理性”可以战胜仇恨,“理智”可以战胜正义。哈姆莱特的仇恨和正义,正是在他的“理性”面前变得一无所能,变得那样苍白、弱小和不成熟。
哈姆莱特,你这样孝思不匮,原是你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他的孝道,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然而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经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既然我们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无论谁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经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把它介介于怀呢?
嘿!那是对上天的罪戾,对死者的罪戾,也是违反人情的罪戾;在理智上它是完全荒谬的,因为从第一个死了的父亲起,直到今天死去的最后一个父亲为止,理智永远在呼喊,“这是无可避免的。”我请你抛弃了这种无益的悲伤,把我当作你的父亲;因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王位的直接的继承者,我要给你的尊荣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至于你要回到威登堡去继续求学的意思,那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愿望的;请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离开这里,在朝廷上领袖群臣,做我们最亲近的国亲和王子,使我们因为每天能看见你而感到欢欣。
嘿,瞧瞧,还有什么话说,有了这番道理,任何一个未“丧失理性”的人,都只能心安理得接受现状,若要再固执己见,那便铁定是“逆天悖理”,而非“堂堂男子”所为了。面对这样出色的演员,你让年轻的王子不疯,又如之奈何?
三、博尔赫斯真正读懂了莎士比亚
在朱生豪的译本中,奸王是译作“克劳狄斯”(King Claudius),而在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的《镜子》一诗中,则译作“克劳狄乌斯”。窃以为后者的翻译也许更准确些。因为这个名字有可能是来自于一位名声不彰的罗马皇帝,长相不佳,且又有残疾的克劳狄一世,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尼禄·日耳曼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Drusus Nero Germanicus,前10—54年),这个名字很冗长,也容易被混同于他之后名字同样啰嗦的第五位皇帝——著名的暴君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Drusus Germanicus,公元54—68)。他是罗马帝国朱里安·克劳狄王朝的第四任皇帝,是在宫廷内斗中偶然坐上皇位的。鉴于他并非正统的身世,以及有缺陷的长相和德行,窃以为莎翁在写此剧时,大概有意用了这一掌故,以暗示和强调“克劳狄乌斯”之作为“奸王”,沐猴而冠的僭越之身。
博尔赫斯
剧中关于奸王的长相,是不断通过哈姆莱特之口,还有他与父王鬼魂之间的对话,来侧面描述的。第一幕的第二场中,哈姆莱特以“天神和丑怪”之别,来形容其父王与叔父之间的差异;父王的鬼魂在叙述事情真相时,则如此来形容他恶毒的内心,“过人的诡诈,天赋的奸恶……阴险的手段”;第三幕中,哈姆莱特在怒斥母后时,又将其叔父形容为“一只蛤蟆、一只蝙蝠、一只老雄猫”。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两个“克劳狄乌斯”之间的内在联系。
好了,这些或许都没那么重要。我之所以费功夫来证明克劳狄乌斯的长相,是想探究莎翁在写作该剧时,有可能潜藏的某些深意。这些深意被老弗洛伊德忽略了,他一直过分关注了哈姆莱特,而忽视了克劳狄乌斯这个角色的意义。而敏锐的博尔赫斯意识到了,他在诗歌中将我们引向一个认知的黑暗地带,当然,也是一个有着无比明亮的真理启示的境地。如果我们尝试来分析一下,很可能,在莎翁的构思与想定中,克劳狄乌斯是一个丑陋的家伙,外观的丑陋与内心的怯懦,还有德行上的卑鄙当然是对称的。如此,在克劳狄乌斯内心中,便有着一种深刻的自卑与妒忌。这或许是他在弑兄篡位之后,还要娶原先的王后作为妻子的真正动机,因为他原本也可以娶一个更为年轻和“纯洁”的女性来做王后。当然,你可以将这解释为是他的政治考虑,娶原先的王后,可以有助于他稳固政权,迷惑或钳制对手,尤其是有着合法继承权的王子哈姆莱特。但是,在笔者看来,他之所以努力扮演自己的正面形象,确与先前的自卑所驱动的一种内力有关。
这是很有意思的,“做梦的国王”,“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梦中”,我觉得博尔赫斯是真正读懂了莎士比亚。克劳狄乌斯背负了现实中作为罪人的巨大压力,他宁愿希望一直生活在梦中。在梦里,他是一位慈父和仁君,受人尊敬,且不受支配地行使权力,与一切既成的秩序和平共处……如果这样的状况能够一直延续,他就会一直维护下去。这是一个“反向的梦境”,常人是希望噩梦会醒来,他则是希望春梦勿受惊扰,将现实固执地当作了白日梦来做。然而在第三幕,哈姆莱特的哑剧如一面闪亮的镜子,照出了他丑陋的真容,如一声断喝将他从梦中惊醒,他便无法再继续装扮下去了。
请注意克劳狄乌斯的反应——他先是大惊失色,尔后则是要尽快将这面让他从梦中醒来的“照人的镜子”予以移除,将王子遣送至英国,并密信让英方将他处死。这样既能够除灭政敌,又可以免受内部的压力。他急忙调动人事安排,一切停当之后,无人之时,他的自言自语披露了他内心的惊悚:
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我不能祈祷,虽然我的愿望像决心一样强烈;我的更坚强的罪恶击败了我的坚强的意愿。像一个人同时要做两件事情,我因为不知道应该先从什么地方下手而徘徊歧途,结果反弄得一事无成。要是这一只可咒诅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血,难道天上所有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洁白吗?
若是读者还没被这华美的辞藻弄晕,便能够体察奸王此时的内心痛苦。他也是人,内心的魔鬼和人的良知在进行着斗争,这才是伟大的莎士比亚!他揭示的不是人间正义的必然胜利,而是人性中全部的黑暗与秘密,包括了我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不曾意识到的那些秘密。看,他在祈求上帝的宽恕:“慈悲的使命,不就是宽宥罪恶吗?祈祷的目的,不是一方面预防我们的堕落,一方面救拔我们于已堕落之后吗?那么我要仰望上天;我的过失已经犯下了。可是唉!哪一种祈祷才是我所适用的呢?‘求上帝赦免我的杀人重罪’吗?那不能,因为我现在还占有着那些引起我的犯罪动机的目的物,我的王冠、我的野心和我的王后……”老莎士比亚给我们活画了一个正在分裂的灵魂,他在怯懦而孱弱的“超我”与泛滥而失控的“本我”之间的挣扎,以及魔鬼在这一过程中的胜出,以及胜出之后真实的惧怕。
啊,不幸的处境!啊,像死亡一样黑暗的心胸!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地胶住了的灵魂!救救我,天使们!试一试吧:屈下来,顽强的膝盖;钢丝一样的心弦,变得像新生之婴的筋肉一样柔嫩吧!但愿一切转祸为福!
进入魔鬼的灵魂吧,假如能够。我们看到了,他正在用人间的种种罪恶,人性的诸般弱点,来为自己宽释,用了世界上所有的不堪来为自己垫背。但最终,他所害怕的仍是上天的审判,他认为在那里“一切都无可遁避”,都会露出真容,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忏悔,而他又是无法忏悔的,因为他不能交出他的所得,更不可能向天下坦承自己的罪行。这样的现实不是噩梦是什么呢?所以他的梦是双重的——既是不愿醒来的春梦,又是希望不曾发生的噩梦。
显然,王子的哑剧已然当众扒光了他的衣服,这是最致命的,他之前所精心维护的梦境已被撕碎。老莎士比亚实在是太厉害了,他将这一过程展示得淋漓尽致。哈姆莱特在排练之时,便自言自语道:“听人家说,犯罪的人在看戏的时候,因为台上表演的巧妙,有时会激动天良,当场供认他们的罪恶;因为暗杀的事情无论干得怎样秘密,总会借着神奇的喉舌泄露出来。我要叫这班伶人在我的叔父面前表演一本跟我的父亲的惨死情节相仿的戏剧,我就在一旁窥察他的神色;我要探视到他的灵魂的深处,要是他稍露惊骇不安之态,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凭着这本戏,我可以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随后,他还再三叮嘱他的好友,同样知晓秘密的霍拉旭,让他集中全副精神注视他的叔父。“要是他在听到了那一段戏词以后,他的隐藏的罪恶还是不露出一丝痕迹来,那么我们所看见的那个鬼魂一定是个恶魔,我的幻想也就像铁匠的砧石那样黑漆一团了。”他坚信这出戏就是一面照妖镜,只要对手还有人的弱点,就一定会暴露出来。
这就是莎士比亚,他窥测人的灵魂如探囊取物,分析魔鬼的内心如同解牛的庖丁。他没有将奸王脸谱化,而是彻头彻尾地还原了他的处境,设身处地设想了他内心的窘困。并让这“黄昏的君主”无法挣脱他命运的魔咒,最终湮灭在渐渐升起的黑暗之中。
选自张清华 《春梦六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