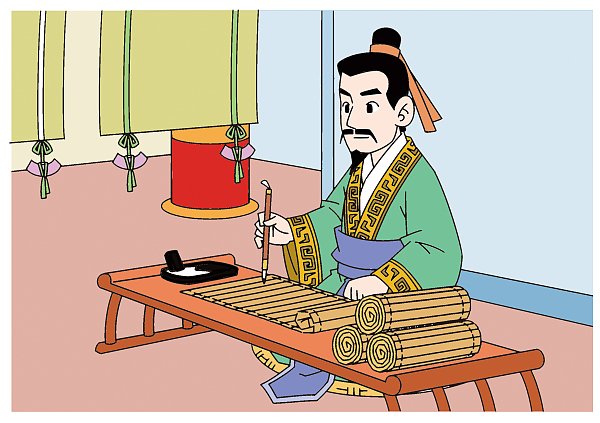今天在说到“写作”一词时,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会想到是真正在稿纸上“写”这个动作了,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在电脑上码字,因此,纸墨笔砚这些“文房四宝”,似乎只剩下了怀旧的意义和收藏价值。如果我们用“键盘侠”来指称当代的文字工作者,大致上也不能算错,写小说、写论文、写报告、写材料,甚至连法庭上书记员做“笔录”,都是把文字通过键盘敲进去而已,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键盘写作时代”。
“键盘时代”的写作其实也很辛苦,长时间盯着电脑,眼睛会变得干涩疲劳;由于在键盘上不停地敲击,看上去似乎不是什么体力活儿,日久天长,十个手指也会变得僵硬起来;伏案久了,颈椎也会出现问题,这些都与长时间面对电脑工作有关。与键盘时代以前的写作相比,到底哪个更辛苦,也只能是冷暖自知了。
西方人在打字机发明之前,写作时用的应该是羽毛笔。伊拉斯谟是欧洲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集诗人、古典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神学家、教育家于一身,著述卷帙浩繁,用斯蒂芬·茨威格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剧》中的评价:“他是西方所有从事著述和创作的人当中第一个有欧洲意识的欧洲人、第一个因为爱好和平而备受争议的人。他是人文主义者的理念——一种善待世人和善待思想界的理念——的一个十分能言善辩的辩护人。”这位知识渊博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酷爱书籍,因为“在一个通常毫无权利可言的时代,读书是有教养者的唯一特权”。
伊拉斯谟还是一位勤奋的写作者,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写一部新书比他看一部旧书的校样还省事”。他虽然身体孱弱,但却每天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在其余的二十个小时中,他会不停地工作,著书、阅读、辩论、校勘和修改文稿,只要他醒着就意味着他是在著书。“他手中的羽毛笔简直就是他的第六个手指。”茨威格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描写伊拉斯谟的阅读和写作生活的,其时的情形都需要我们这些读者们去进行“脑补”。
而键盘时代以前的中国现代作家们写作时,身体或精神上遭遇的“苦状”,则是他们自己告诉我们的。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特别迷恋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还将图书馆里的《沈从文文集》悉数借回家阅读。在书籍的内页上有沈先生蝇头小楷的手稿,字体清秀漂亮到可以拿来作字帖。然而,沈先生在其清新隽永的文字背后,掩藏的是生活的困厄与艰辛,他之所以成为高产作家,目的只是为了卖文为生。他在1929年10月下旬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道,“本来已说不写文章的,谁知又成了不在本月底写成一书就无法支持的情形,眼前还一字不曾着手,然一到月底无论如何也非有三万字不能解决,所以这几天若写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就是上课也恐怕不到一月连来吴淞的钱也筹不出了。”
除了为生计着想,不知道写什么却又“不得不写”之外,那些“为爱好兴趣和热情”而写作的人,也会遭受写作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之苦。在胡悦晗的《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中,讲到多金的邵洵美说他“平时读书写文章,都在夜间”,不过“夜里写文章,一忽便会天亮;一天不睡,三天都不能使精神恢复,我于是时常头痛”。
编撰《中国药学大辞典》的陈存仁讲到脑力劳动者的工作状态,“白天常觉疲劳过度,遇到有些写作上的困难问题,夜间不能成眠,有时睡到半夜入梦之时,拟好了一段文稿,或是想出了一个字,忽然清醒坐了起来,急急开了灯动笔记下。最初记好之后,也就入睡了。后来记了之后,觉得提起了虚火,自己按捺不下,就继续做上两三小时工作。从前年轻,少睡两三个钟头无所谓,但是积了半年时间,究竟人不是铁打的,就病起来了。”熬夜这种打破作息规律的生活方式,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人尽皆知,然而,对于作家、学者等文字工作者来说,熬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思维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深夜很活跃,只是这些精神产品的产出,不得不以生产者的健康为代价。
无论是“键盘时代”以前的写作者,还是当下的“写手”,书写的工具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脑力劳动的实质却是一样的:它需要作者的构思、才情和坚实的文字功底,需要作者案牍劳形的毅力,那凝聚着作者的思想、情怀与使命感的文字,是滋养社会精神生活的食粮。当我们怀着莫大的兴趣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时候,应该感谢他们在每一个冷寂的夜里的付出,这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所应想起的。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