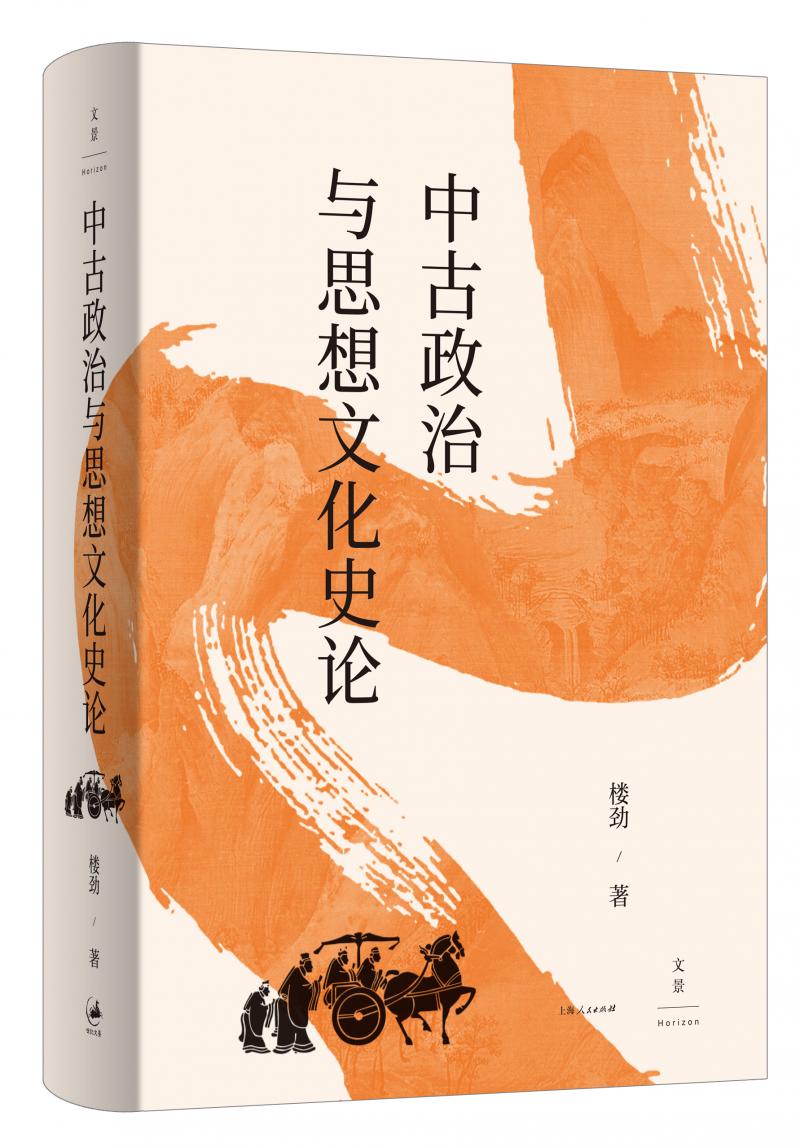女医“取官户、婢”以下的另外几项规定:“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为自古公认女性身心成熟的盛年 ,按当时习俗和婚龄,该年龄段的应多已婚女子 ,对自身性别特点的体会要更全面,更便于教习妇科之术。“性识慧了”既是对生徒的常见要求,也与世间公认医者特须“巧慧智思”有关 ,“五十人”之额与同署男医员额相比也不算少 ,不过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值得注意的,是“无夫及无男女”的规定。
“无夫及无男女”,从字面解释即未婚女子及无子女之寡妇,这项要求在入宫服事的官婢中也可看到。《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郎中 员外郎”条原注述配没官奴婢赐人者不得拆散其夫妻男女,其下有云:
若应简进内者,取无夫无男女也。
“简进内者”,即其前文所述配没而“入于掖庭”的妇人工巧之类,“无夫无男女”则是针对其中多有已婚女子的规定。这大概是要取其较少俗间是非和牵绊,对于服事内廷者来说是不难理解的。 非但如此,当时还确认女性天然易受外界干扰,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妇人方上 · 求子》论“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有曰:
女人嗜欲多于丈夫,感病倍于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妒忧恚,染著坚牢,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难瘥。
女人“感病倍于男子”或然,却绝非因其“嗜欲多于丈夫”,故此论虽体现了传统医学兼重心理的长处,但也更多当时流行的社会性别观成分。即世人公认女性本易陷入各种是非牵绊,困于情绪而难自拔,并已将之上升为合乎天道的医理。这一点似可表明,规定“无夫无男女”的出发点,不仅是要一般地减少其社会关系的外在干扰,而且也是在尽可能排除女性特多“慈恋爱憎、嫉妒忧恚”的外因,从内在心理上有助于其专志服事。
当然在此背后,可能还存在着女性从业本不如男,若多牵绊又困于情则尤不可为之类的成见,同时也不排除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别观念在起作用。相传为西汉刘向所撰、后人续有所补的《列女传》卷四《贞顺传 · 齐杞梁妻传》载杞梁妻葬夫恸哭,城为之崩:
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
杞梁妻投水赴死,固属非常之举,堪值注意的是其申说的“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见吾节”。 此语表明,在“三从”成为女子的最高道德律后,“无夫无男女”洵为出嫁女子自明“诚节”和世间认其贞静可靠的要件。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对入宫官婢做“无夫无男女”的限制,除取其少所牵绊、职志易固外,还有更高一层的“女德”观念为其标的,故其又可与汉魏以来《列女传》和《女诫》类作品的流行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
看来,唐代女医之所以须“无夫无男女”,实际上是比照服事于内廷的官婢,以诚节贞静、较少是非牵绊和易于专心致志为其选取条件的。由此不难推想太医署培养女医的目的,主要也是为内廷的大批嫔妃宫女兼为宫外贵妇提供医疗服务。与之相应,“女医”条下文的“别所安置”等规定,一方面继续体现了当时社会性别观对女医习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似亦有类服事于内廷的女伎安置教习之法。
“别所安置”即太医署选取的女医,不与其他医、针等生一体习业,而是另有专门院舍供其起居教习。如此安排,一种考虑是因为官府需要培养女医,名教又甚重男女之防,遂不得与男性生徒混同教学。可与参证的,如道经《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上《讲习品》所述女道士外出就师受道的规范 :
凡是道学,当知听习回向,须得明师……若女冠众,性理怯懦,本位无人可习者,当三人、五人乃至多人,清净三业,赍其道具,听受法本。亲近大师,一日二至,退著本位。若近本师住处法门,无女冠住处法门,应近本师住处左右,投精专奉道之家居止。
道法授受既须明师,但教门仪轨亦重男女之防 ,故若女道士别就他观听受法本,不仅须结伴就师,其居所亦有限制。从中可见道观若有常居女冠,也要为之设立专舍。有意思的是上引文提到女冠“性理怯懦”,则其结伴出行专舍聚居,也是针对世所公认的女性特点采取的保护措施,这对出身贱户易受欺凌的女医来说显然尤为必要。
女医别所设立“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除与女道士外出就师相类的防范、保护寓意外,所透露的是另一层更为重要的信息。“给事”而称“内”,在唐一般是指宦官之职,女医起居教习的别所竟由宦官监门守当,可见其性质当与教授和供奉内廷乐舞的内教坊尤其是太常别教院入宫女妓所居的宜春院相类。《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乐署载内教坊故事:
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
是唐初以来设内教坊于禁中,教习供奉内廷的伎乐,武后以来以中官为使统之。至玄宗时扩充外教坊,分为左右,与内教坊并由宦官教坊使统领。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一》又载玄宗故事:
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
玄宗教梨园弟子的别院,或即上引新《志》所载置于蓬莱宫侧的内教坊 ,可见此院由宦官监门守当实属理所当然。而所谓“太常别教院”,则因乐舞之事本属太常寺太乐、鼓吹二署,但供奉内廷新曲者性质特殊,故须立院别教,其在体制上当属外教坊,规模常有千人,其中入宫供奉的女伎则居于宜春院服事教习。
以上所以要费辞说明内教坊及别教院之制,不仅因其别在宫中教习,且由宦官掌之,事与女医“别所安置”并以“内给事”监门守当性质相近;更是因为安置女医的“别所”,很可能就像宜春院那样位于宫中。日本《令义解》卷八《医疾令》所引《养老令》“女医”条亦有“别所安置”之文,其注解曰:“谓内药司侧,造别院安置也。” 可见日本仿唐所定之制,是将女医安置在宫中“内药司”侧的别院。王昶《金石萃编》卷六二收录的《梁师亮墓志铭》载志主为安定乌氏人:
大父殊,隋任右监门录事;显考金柱,唐奉义郎;并行高州壤,道蔑王侯。杨雄非圣之书,我家时习;方朔易农之仕,吾人所尚。君……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别教医生,抠衣鹤禁,函丈龙楼,究农皇之草经,研葛洪之药录。术兼元化,可以涤疲疴;学该仲景,因而升上第。
梁氏所任“左春坊别教医生”不见于史载,王昶引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有曰:“考《百官志》左春坊药藏局有郎、丞、侍医、典药、药童,无云别教医生者。唯太医署有医博士及助教,掌教授诸生。然则师亮殆以医助教入侍宫坊者欤?”认为梁氏是在左春坊受教医术,“业成而升上第”。今案左春坊药藏局既设侍医、典药,此类除从医外自可教习药童,梁氏为太医署助教充宫坊教习是讲不通的 ,即便其有可能临时入侍宫坊,显亦不得称“起家”。但王昶以为梁氏受教左春坊也有问题,若其本为药藏局药童之类,则不得称“别教”;若其为太医署生徒,则断无就学左春坊之理。今案志铭述其家非儒生,又慕尚东方朔以所学博杂登进 ,梁氏或系医家子弟选入太医署为医生者,盖因其由此跻身流外官而夸称“起家”,被遣至左春坊充任教习故称“别教”,又因唐制教职考课皆以生徒课试成绩及业成的多少迟速分等而“升上第”。 这就不能不引人联想梁氏赴左春坊所教,很可能就是由太医署教习而须“别所安置”的女医。
据唐长安宫城布局,女伎入宫所居的宜春院,当在东宫北部中轴线东的宜春宫附近,宫南即为典膳厨,隶属于左春坊的典膳、药藏局应在典膳厨附近。 以太常别教院女伎入宫安置于宜春院之例推想,太常寺太医署别教女医于东宫药藏局所辟院舍确有可能,因其既便于利用药藏局的医药资源,又有就近服务于内廷嫔妃、宫女之便,且宫禁本严,尤合“别所安置”之义,还因其地不免仍有东宫官吏往来,正须有“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由此推想梁氏所任的“左春坊别教医生”,或者就是辅助博士“别教”安置于左春坊管内院舍的女医 。不过退一步讲,无论梁氏所任何职,所教何生,唐《医疾令》“女医”条既规定其与入宫官婢同须“无夫无男女”,又“别所安置”并特设“内给事”四人监门守当,则其安置之所当位于宫中,起居教习有类太常别教院入居宜春院的女伎,比照入宫服事的女婢来管理,业成常以内廷嫔妃宫女为服务对象,这恐怕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选自楼劲《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世纪文景2023年1月出版。文题原作《“无夫无男女”及“别所安置”》,注释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