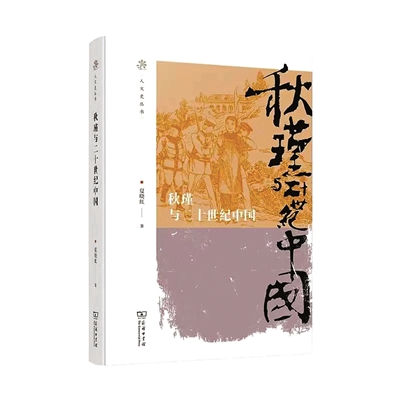服部繁子画的秋瑾像
◎杨早(文化学者)
1908年2月25日,生前的弟子、好友在杭州凤林寺为秋瑾开追悼大会。这次追悼会距秋瑾在绍兴就义,只有七个月。亲友们将她的坟迁到西湖之畔西泠桥侧,再开追悼会以表纪念。在秋瑾墓长达70多年的十次迁移中,这是第二次迁墓。十个月后,朝廷便下令平墓。
当天追悼大会,主调自然是对鉴湖女侠的缅怀,对朝廷的愤恨。然而,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了。说话的是一位旗人,而且是杭州驻防营协领,叫贵林。目击者说,贵林在追悼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明亡于李闯,而非大清,大清是从李闯那里得的天下,秋瑾搞种族革命,未免不大对头。这话引起了全场公愤,当面痛斥这位旗人将领。于是贵林“怏怏而去”,衔恨于心,向朝廷密报,后来清廷下令平毁秋瑾墓,贵林便是主谋之一。
故事讲到这里,是不是很流畅?什么人啊,竟敢在烈士灵前批评逝者生前行为不当?事后又含怨告密,真是太坏了!
事情真的这么流畅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林。贵林有两个身份,一是杭州驻防营协领,一是杭州惠兴女学校总办。如果你不了解惠兴,我打个比方,她就是清末的张桂梅,为了兴办女学不力,惠兴于1905年12月愤而服毒自尽。现在杭州仍然有惠兴中学,纪念这位女教育家。而在惠兴逝后,勉力维持女学堂的,正是总办贵林。
而且贵林跟浙江的许多革命党人,关系着实不错。放弃翰林之位闹革命的蔡元培,1902年元旦举行婚礼,贵林赫然在座,而且发表了演说。还有记载说,贵林在当时杭州驻防营中,被称为“清朝孔子”。这样一个人,他会失心疯地为了清朝统治去灵前骂秋瑾吗?但是大家都这么说。于是到了辛亥革命,贵林作为顽冥不化的旧朝官僚,就被处决了。
那到底贵林那天在秋瑾追悼会上,说了些什么?好在他自己有记录,而且发表在《惠兴女学报》上,后人才能知道他真实的观点。
作为与众多维新人士交好的满族军官,贵林的主张是要消弭满汉之见。他与徐锡麟有过交往,不相信官方文告里说的,徐锡麟竟会刺杀巡抚恩铭、起兵反满。他真心认为徐是被冤枉的,自然,他更不相信被徐锡麟案牵累的秋瑾有什么造反的行为。
贵林没见过秋瑾,他对秋瑾的批评,主要来自所闻,说秋女士“志大行粗,语言不谨,文字蛊祸,而家庭革命之说实有以尸之”。秋瑾在当时,远不是如今大众记忆中的光辉印象,她喜男装,喜骑马,爱刀剑,连革命同志也啧有微词。而秋瑾被祸,实因提倡家庭革命而非政治革命,这是当时舆论的共识。但是,贵林在追悼会上讲这样的话,当然是不合时宜的。
那贵林为何要在追悼会上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逝者发难?其实贵林有一番大道理要发挥。他认为徐锡麟案也好,秋瑾案也罢,“兄弟姑不论其是否冤诬,然可断定其为国事公罪之案”。贵林的意思,在现代宪政制度下,“国事公罪”是不会受到死刑这种对待的。他举的例子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西乡隆盛。贵林认为西乡隆盛谋叛,是主张宪政而不能达成,但西乡认可“天皇神圣不可犯”,因此被诛之后,很快天皇就“赦其罪且旌其行”。贵林的潜台词很明白,如果中国的维新人士都坚持“尊君爱国”,那么等到宪政功成,像徐锡麟、秋瑾这样的政治犯就不会被杀头,这就是满人贵林被在座众人称为“愚拙”的见解。
这一桩公案,经《秋瑾与贵林》作者夏晓虹于2007年像破案一样抽丝剥笋,条分缕析,才得以大白于世间。贵林的苦心,也不致埋没于历史的尘灰之中,正如作者在文末所言:“这部分人的努力与声音,在迅速的革命风暴中被无情地席卷而去,可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不应该追随时事变化,漠视其存在,对其活动与心事一笔抹杀。”当年读到这一段,极为击节,对于如何规避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刻板印象,似有所悟。
2023年,将此篇再放置在多年研究汇编而成的《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之中再看,犹如镜头往空中拉起,看到一座城市在大地上的位置,对于“秋瑾”这样一位表征性人物,正宜结合史料的考辨,时人的舆论,以及整个二十世纪对秋瑾的书写与接受,才能让秋瑾的所言所为,焕发出迥异于记忆的新义。晚清的舆论以“家庭革命”为辞,为秋瑾死于政治罪名鸣冤,而到了1930年代,则是以“政治革命”收编“家庭革命”,再到1950年代的“革命传统教育”,秋瑾等人呼吁男女平权的呼声被压抑了,方向虽异,结局类似,都是将秋瑾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纳入近代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中,至少是抹杀了她很重要一部分的“活动与心事”。
《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夏晓虹著商务印书馆
我在好书评奖的推荐视频里讲,阅读《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宜采用“倒读”,先读“剩义篇”,无论是媒体约稿的《英雌秋瑾》,还是为《中华文明之光》所作《我欲只手援祖国——说秋瑾的女杰情怀》,都是正面立论,可以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秋瑾的人生全貌;而作者用力最勤的“延展篇”,则是多角度全方位地扫描“晚清的秋瑾”与“二十世纪的秋瑾”,足以让人明了作为叙事主角的秋瑾所处地域环境、舆论氛围,乃至时代幻变给她脸庞抹上的不同油彩。最后来到“本事篇”,仔细探讨秋瑾本人的趣味爱好、情感取向、政治论述与女性意识,才算完成了对秋瑾这位“熟悉的陌生人”的重塑。此时再回看课本、词条中的秋瑾,不免有一种洗尽铅华、入眼入心的恍然。
“秋瑾”很小,“二十世纪中国”很大。但大总是由无数小组合、激荡而成,大的叙事,也不能吞化小的复杂。不能识小者,不足言其大。供图/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