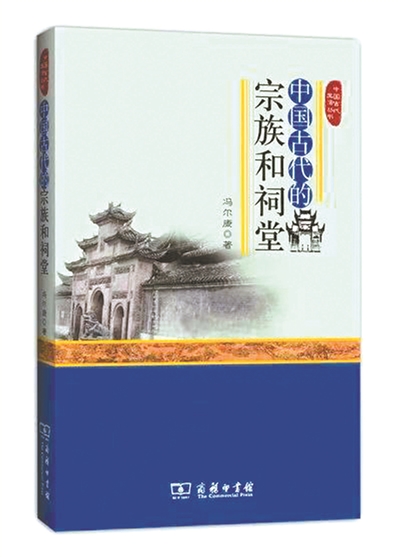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后,曾师从历史学家郑天挺攻读明清史专业。他是国际知名的清史专家,代表作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等。他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今年夏末,冯尔康教授回国,回到他热爱了一辈子的南开大学校园。虽已90岁高龄,他仍以治学为乐。和他漫步在校园曲径,听他回顾南开历史,讲述平生治学心得,偶尔一缕夕阳落在他斑白的鬓发,让人愈觉其智者的沉着和安详。我们从青年读者的角度多有请益,老先生一一耐心回答,最后不忘提醒年轻人要多运动,说自己还常去游泳馆游上几个来回呢。
年轻人应珍惜批评
被恩师郑天挺“和颜悦色”了两次
冯尔康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留校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当助教,半年后成为著名史学家郑天挺的研究生。
冯尔康感念师恩深重,曾专门撰文回忆郑天挺先生授课时的情形:毅生师(郑天挺字毅生)讲授明清史基础课,开设《明史专题》《史料学》选修课。老师讲课,缓缓而谈,时有口语——“那个,那个”,此外没有多余的话。他上课没有讲稿,手上拿着若干张卡片,比我们通常用的64k要稍大一些。后来听傅同钦教授说,毅生师在讲课之前,反复看他的卡片,有时似作默述状,可见他的认真和下功夫。冯先生近日敬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获知,老师在30年代授课前,总是“读摘讲授札记”“备讲述之用”,老师是精益求精,非将功夫下到家不可,所以讲授的内容非常清晰,我们接受起来很快。
冯尔康还谈道,郑天挺讲授史料学,令他开阔了眼界,知道历史学有那么多辅助学科,诸如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印章学、目录学、钱币学等等,获知史料学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一些史料的搜集、考订方法。他在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上,以相当大的热忱和精力投注于史料学,写出《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两部专著。冯尔康说,追本溯源,这些研究受启发于毅生师的史料学课程。
1959年明清史研究班开业的第一课,郑天挺讲授《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开宗明义,要求学生们精读一本书,即张廷玉主修的《明史》。为什么精读一本书?何以选择《明史》为读本?怎样才是精读?先生对这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冯尔康体会“精读一本书”的方法,不仅是指导史学初学者的入门良方,也是史学工作者终身受益的方法,带有普遍的意义。他也是这一方法的践行者,“我做研究,不论是哪一朝一代、哪一个专题的历史,都精读一部史书,如我系同仁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我写东汉史、三国史,主要精读《后汉书》《三国志》。我把毅生师的方法还用到教学上。如在讲授中国古代史基础课时,对于多种通史教材和专著,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其中的一种,其他只作泛览性参考。”
在冯尔康印象中,郑天挺先生“总是那样慈祥地面带笑容,从不对人疾言厉色”,可是有两次和颜悦色地含蓄地教导了他。“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召开中美两国学者经济史研讨会,我原本要出席可是却没有去,毅生师说你应当去;一次是毅生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在天津召开工作会议,我在上课之后才到会,毅生师问我怎么才来?他希望我出席国际学术会,是让我有被学界认识的机会,也是表示南开大学历史系有人从事相关研究;要我早点到会,为辞书编辑做点工作。”
谈及此,冯尔康的感念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毕业时想报考研究生,未被批准,学校要我留校做助教。留校不久,历史系为培养青年教师,郑先生就将我收做了他的明清史研究生,所以我说他是我的恩师。”后来,冯尔康辗转得知,当年能够留校和成为研究生,郑先生应该都是帮了忙的。当然,这也因为冯尔康的优秀。冯尔康入学时,恰逢南开大学实行优等生制度,他第二年就被评为优等生,还是学生论文竞赛的获奖者。
年轻人不要轻信“文物”
一枚“雍正”印章送到郑天挺手中,他为何转身就拿出了煤油灯
回忆起和老师郑天挺的过往,冯尔康印象最深的是和老师的课后答疑。“那时老师给我们上课,课后有答疑时间,这是他自己规定的,一般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大家随意,不强求参加。”冯尔康说,这种课后答疑,经常只有我和老师在教室里问和答。
冯尔康一直在老师的关注下成长,遇到问题就向老师请教。郑天挺先生上世纪50年代末起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因为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所以他为了工作,很多时候居住在书局。冯尔康到北京常到书局为老师安排的住处拜望。
“文革”结束后,风气开放,冯尔康为写作《雍正传》常到北京查找资料,也常到老师家中拜访并请教问题。他记得一次聊天时谈起,自己在河南调研时听当地一位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一个在监狱服刑的犯人报告自己有一枚曹雪芹印章,冯尔康当时就觉得可疑,判断犯人有为立功获减刑而做假的可能,但也不好多问。
待回津后见到郑天挺,便向老师请教这件事的可能性。郑先生遂举了一个例子,“老师说解放前曾有一位文物商人带着一方雍正‘为君难’的印章找到他,想卖给他。他请商人把印章留下,过两天再来取。等人走后,郑老师拿出煤油灯,用煤油洗掉了印章上的印泥。老师见多识广,洗掉印泥后从刀工一眼就看出是新刻的。”冯尔康说:“老师举这个例子是告诉我,对文物千万不要轻信,也包括不要轻信其他的史料,一定要认真鉴定真伪,用郑老先生的话说叫‘史料批判’。”
1980年夏天,由教育部同意、郑天挺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明清史国际研讨会”。那场会议有100多位国内外学者参加,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历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冯尔康作为论文组成员为会议做学术服务,同时提交了关于雍正的论文。在那次会议上,他结识了不少人,也为很多学者熟识。当时国内环境还相对闭塞,学者们难以听到国外的研究声音。郑天挺具有国际声望,视野开阔,冯尔康能从老师处获得一些信息,他记得郑先生曾告诉他,美国人已经不研究大题目,而是研究具体的小题目。
年轻人应有创见
清朝得以立足于中国,重点在北不在南
冯尔康教授写作《雍正传》,是一段关于学术追求佳话。回溯写作动机,冯尔康说:“本科阶段,郑先生给我们上明清史课时,就曾提到雍正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值得注意。后来我做清史研究时,觉得雍正的政治改革措施非常有意义,比如摊丁入亩等政策都值得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雍正帝的形象在学术界和民间逐渐正面化。此前,由于皇位继承问题的争议,雍正帝常被描绘为篡位者、暴君等负面形象。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雍正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冯尔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撰写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述雍正帝生平政绩的传记。他认为,做历史的人应该把在历史发展中起作用的人实事求是地写出来。
冯尔康在为雍正立传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将雍正的个性写出来,“因为我开始写《雍正传》时历史写作还是很公式化的,给一个人定义阶级性,那雍正当然是地主阶级最大的头子,我坚持的是按实际情况来分析历史人物。”冯尔康尤其侧重剖析雍正的人品,试图将其性格的复杂性揭示出来。
冯尔康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他写雍正,不是研究雍正个人,而是研究那个时代。他将清朝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一样。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清前期为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达到国家一统。冯尔康说这一观点没有抓住时代特点。他认为清前期的问题不在于三藩和台湾,而在于北部边疆,“解决了北部边疆问题,清朝才得以真正稳定。”冯尔康说:“我们从康熙三次亲征蒙古噶尔丹可以看出他对满蒙关系的重视程度,因为这是清朝能否立足中国的关键所在。”乾隆中期平定新疆北部,设立伊犁将军,最终巩固北方、西北、西南边疆,这一段是清朝前期,这是冯尔康在《雍正传》中提出的观点,他也自信清朝历史的分期应当以此分析为准。
1981年底,冯尔康的《雍正传》完稿。作为国内首部雍正评传,这部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至今畅销40年,是豆瓣评分最高的雍正帝历史传记。网友评论它不仅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雍正帝的生平政绩,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见解,为雍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学界也认为,《雍正传》的出版不仅推动了雍正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也促进了学术界对清代历史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同时,该书还通过生动的笔触和丰富的史料,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立体的雍正帝形象,增强了读者对清代历史的理解和认识。
年轻人应下足功夫
八阿哥的笔记、十四阿哥的奏疏统统不放过
冯尔康在撰写《雍正传》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史料搜集和研究。冯尔康最常去的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的清史资料特别多,我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关系也非常好,我要什么书他们都愿意提出来给我。”
冯尔康把能在南开大学找到的资料看了一遍,觉得还是不够,于是又想去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想去,但那时候它归属于中央档案馆,需要批准才能进去。70年代末第一历史档案馆移到故宫,对我们开放了,所以我每次到北京都要找机会去。”
冯尔康到第一档案馆主要目标之一是看清朝皇室玉牒。他说:“清史界有位老先生曾提出,雍正的继位之谜可能在玉牒里,这对我有启发。我还想在其中找到能够帮助分析雍正为人的材料,当时格外注意的一是雍正的朱谕,另一个就是遗诏。”
玉牒存放在皇史宬,冯尔康找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接待工作的朋友鞠德源,他为冯尔康到一档查资料提供了不少帮助。“记得皇史宬里都是又高又大的书架,有清代历朝所纂修的各种类型玉牒。那些档案没有装盒,按朝代一摞一摞地摆放着,根本没有人能够去看。进去之后灯光昏暗,工作人员帮我把布满灰尘的档案从架子上搬下来,我带着纸笔,就在库房里边看边抄。”
皇十四子胤禵的奏疏也不能不看,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冯尔康跑到北大图书馆,直接找馆长。实际上冯尔康不认识馆长,但他一向注意相关信息,所以在报纸上知道了馆长的名字。他记得:“馆长二话不说,告诉我你就看吧!”
除此之外,冯尔康还查阅了大量相关大臣的奏折,写了很多人物传记。
该看的看了,该写的也写了,冯尔康认为还不够,因为他得知康熙皇八子之子写有一部笔记,而当年皇八子颇有被立为皇太子的呼声,所以他判断这本书与继位之谜关系密切,如果不看,写《雍正传》必然缺一角。书在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这一次可没有那么顺利,几经周折才得以借阅。
写书期间,为了查找相关资料,冯尔康住在北京,几个星期才回天津一趟,白天看资料,晚上整理资料,一刻不停。“那一阶段想看到的材料——各种类型的档案、文集、地方志,基本都看了,遗憾的是年羹尧档案因为不在内地没看到。”
冯尔康在写作时也注重可读性。他说:“我写作不完全是给专业人士看的,我上小学时就爱读历史演义,比如《隋唐演义》《说唐》等等,大众化的文风对我是有影响的。”
年轻人应认清使命
当社长、所长的机会,为什么都推掉
曾经南开大学校方要冯尔康出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他谢绝了;一个研究所的老所长将退职,副所长找到冯尔康,表示想让老所长建议他接替所长职务,他也推辞了,对此他说:“我觉得别的事我做不了,做不了就耽误事,所以都没有做,我就想安心做学问。”但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冯尔康为南开历史学院做了不少好事,他曾基于好友、台湾大学荣休教授陈捷先的介绍,主持台湾学者彭炳进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设立学术讲座基金会,他连续三年约请天津、北京学者演讲,然后汇集成学术论文集三种并出版。还是陈捷先的美意,令冯尔康与曾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负责人姚为民结识,姚先生遂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设立奖学金,奖励勤学的学子。冯尔康负责此事,直到2002年退休,而此项奖学金也就结束了。
另外,冯尔康先生是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创办中国社会史学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他在南开大学最早主持推动社会史研讨会,并作为研究者第一个发表文章,即《开展社会史的研究》。
请他给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们一些寄语,他想了想后,语调恳切地说:“如今时代的经济条件较之过去强得多,就做学问来讲,有这个条件,更可以走向世界,开阔眼界,吸收中外的文化来取长补短。但由于我们处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也需要静下来,尤其是做学问,必须要静。静下来,才能踏踏实实地做出有价值的传世之作,而不是应急之作,才能对社会和人类有益,这是我们的目标。”
90岁高龄的冯尔康教授给我的印象是为人谦逊、治学严谨,他与弟子们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也始终关心着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在采访中得知,冯教授坚持锻炼身体,最爱游泳,回到南开校园,也没忘记去游泳馆游上几个来回。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