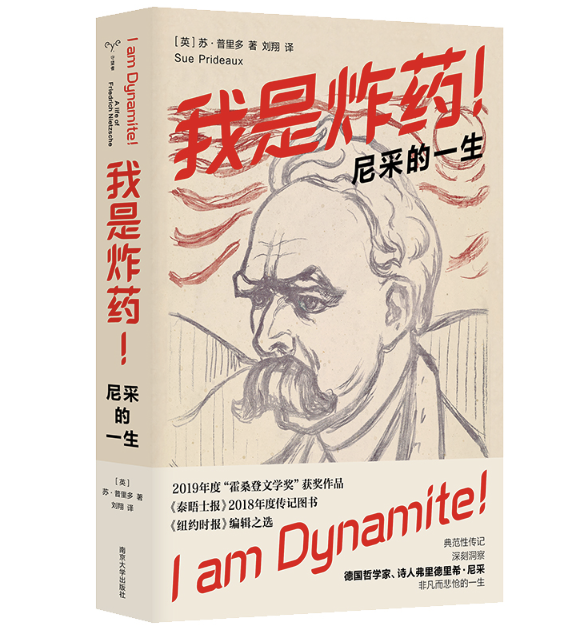1897年4月,母女间的暴风骤雨终于止息。疲惫不堪、郁郁寡欢的弗兰齐斯卡去世了,终年71岁,可能是死于子宫癌。伊丽莎白终于获得了对尼采这个人及其作品的完全控制权。
首先要做的是把他和档案馆迁往一个更合适的处所。瑙姆堡是一潭死水。在她看来,魏玛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那里,他可以在德国文化的万神殿中占据一席之地。
随着歌德在1775年的驾临,魏玛早已成为德国的缪斯之城。黄金时代的文化巨擘们已然完成了朝向“我们德国的雅典”的改造:费希特、赫德、洪堡、谢林、席勒和威兰。1848年,李斯特承袭文化衣钵,成立了文化社团——“新魏玛协会”,并在宫廷剧院执导了瓦格纳的早期歌剧作品,从而开创了白银时代。
歌德和席勒的档案都被保存在魏玛,而伊丽莎白盘算着,分享这份荣耀将进一步增加尼采档案馆与瓦格纳档案馆平起平坐的机会,伊丽莎白对科西玛在拜罗伊特的那个档案馆充满了愤愤然的艳羡之情。
卖掉瑙姆堡的小房子,买下魏玛的大宅第,这需要资金。梅塔·冯·萨利斯马施林斯乐于解囊相助。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回报那些与尼采在锡尔斯玛利亚共度的夏日吗?梅塔教会他的仅仅是泛舟于席尔瓦普拉纳湖上,而作为交换,他教会了她,一个女人同样可以成为超人。
梅塔找到了新落成的“银景别墅”,一座相当丑陋的四方形砖石结构宅邸,位于魏玛南郊。它的规模比瓦恩福里德要小,但由于无须容纳一个音乐厅,也就足够大了。银景别墅以其位置著称,因其银色的景观而得名。它过去和现在都坐落于徐徐上行的洪堡大街顶端,俯瞰着这座城市最美的景致,因此也是欧洲伟大的新古典主义风景之最,这是歌德结束其意大利之旅归国后的手笔。像尼采一样,歌德爱上了罗马周遭的平原和乡间,也爱上了它们在画家克洛德·洛兰画布上的呈现。归来后,歌德着手将魏玛平原起伏的轮廓重塑为世外桃源的缩影。牧场变为乐土。蜿蜒的伊尔姆河的曲折处建起了庙宇和石窟。从银景别墅的窗口望去,景致绵延至少十英里,这是对尼采心爱风景的再现,正是那片风景赋予了尼采灵感,在对露的苦恋中,创作了《夜之歌》。
银景别墅的双层玻璃阳台是尼采余生的三年中日日落座之处。如果他的双眼能够看见这片景色——但这是完全无法确定的——那么他将会记起与露一道登上萨克罗山的那次改变命运的远足,彼时的原野和风景,平展地铺陈上图林根平原,而其边缘则被埃特斯堡森林汹涌的黑色林涛所吞没。
在梅塔看来,这似乎是最适合她亲爱的朋友的所在。她以39万马克的价格买下了这座别墅及其土地。在没有知会梅塔的情况下,伊丽莎白开始了一项穷奢极欲的建筑工程,这里砸掉一个浴室,那里打掉一个阳台,然后把账单寄给梅塔,这些毫无必要的装修改造费用令梅塔愤慨。但她发现,更糟的是伊丽莎白对于公众的狂热。梅塔读到一篇记者文章,描述尼采是如何为了获利而被展览示众:先是睡觉,接着醒来,然后蜷在一张椅子上,被喂了几块蛋糕。对梅塔而言,这太过分了。她切断了联系。
1897年7月,随着改建工程的竣工,伊丽莎白组织了一次广而告之的秘密夜间旅行。哲学家坐在轮椅上由火车从瑙姆堡运抵魏玛,到达车站专门开辟的私人入口。这里通常是为萨克森魏玛大公保留的专用通道。从抵埠那一刻起,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伊丽莎白靠自己的双脚在城中走动过。她只乘坐马车出行,随行的还有坐在车厢上的一名车夫和一名男仆。
最早的到访者之一是哈里·凯斯勒伯爵。8月他抵达时,惊讶地发现一个身着制服的仆人正在车站迎候他,那仆人的镀金纽扣上夸耀性地装饰着贵族的五角形冠冕。凯斯勒是来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同名音乐作品已于去年首演,引起了轰动。凯斯勒提议让先锋艺术新锐设计师亨利·范德费尔德来为《查拉图斯特拉》设计一个豪华藏书版。凯斯勒还意欲敦促晚期诗作,以及尚未出版的《看哪这人》的出版。伊丽莎白对此无动于衷。除了想要压制《看哪这人》中对她本人不利的段落,她更倾向于在她关于其兄长的传记文章中吝啬地释出该书中的小片段。此举维护了她作为看守者、作为唯一有权接触这本宝贵自传的人的特权地位: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武器,能够用来让任何可能质疑档案馆发布内容的真实性的人(柯林拜尔的阴影)噤声。她牢牢把持着《看哪这人》,直到11年后才准其出版。即使那时,她也只允许凯斯勒以所谓“银行董事版”的形式出版,这是由范德费尔德设计的150册豪华限量版,以黑色和金色墨水印制,让她赚了29500马克。
哈里·凯斯勒初次到访银景别墅之时,伊丽莎白更乐于讨论与尼采相衬的丧葬安排,尽管他还在楼上活得好好的。她已决意要把兄长安葬在银景别墅的土地上,就像瓦格纳被安葬在瓦恩福里德一样,但这令市政当局十分为难。哈里·凯斯勒认为,锡尔斯玛利亚的贞洁半岛兴许是更为适宜的地方,但伊丽莎白对此不感兴趣。不过,她仍提议由他来担任档案馆编辑之职。尽管时年61岁的伊丽莎白施展万种风情向29岁的凯斯勒抛出了这个提议,他还是没有接受。
伊丽莎白有着维也纳人的习气,热衷于跟年龄只有自己一半大的美男子调情。档案馆的第一任编辑弗里茨·克格尔爱上了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并与之订婚,因此被解雇了。随后,伊丽莎白雇用了年轻的鲁道夫·施泰纳,此人后来加入了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宗教通神学教团,其后又根据他青年时期所经验到的幻象,创立了自己大杂烩式的“精神科学”,名曰“人智唯灵论”。鲁道夫·施泰纳除了在尼采档案馆的编辑工作外,伊丽莎白还聘请他指导自己学习其兄长的哲学,此事以失败告终——坏脾气的幻视者无法指导顽固的大羊驼。施泰纳放弃时声称,她既不能接受指导,也无法理解其兄长的哲学。这两点恐怕都是对的。
由于凯斯勒的拒绝,档案馆的编辑职位出缺了。新近从锡尔斯玛利亚运来了大量文件。尼采最后一次离开锡尔斯时,在杜里施家中他的房间里留下了各种笔记和便条。他告诉杜里施说那是垃圾,应该烧掉。杜里施只来得及把它们放进橱柜,还没顾得上点火,朝圣者就来了,他们要走遍查拉图斯特拉的山,触摸他的石头。他们紧紧攫住一切神圣的遗泽,不管上面写的是“我忘带伞了”,抑或是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被撕成碎片的狄俄尼索斯之间不同含义的推测。伊丽莎白风闻此事,马上要求把所有东西都送去魏玛,它们在那里加入了那笔文学遗产越垒越高的故纸堆中。
最终,伊丽莎白不得不纡尊降贵,把彼得·加斯特请回来担任编辑。他的确是唯一能够读懂那些晚期笔迹的人,此事对伊丽莎白的野心而言至关重要,她要把那笔混乱的文学遗产塑造为她自己的书,并以尼采的名义出版。她打算将其命名为《权力意志》,并推它为尼采的代表作,他对所有价值的重估。她丝毫不怀疑,她可以从文学遗产的残章断句中创造出这部作品,在理智之光照临的最后一年里,尼采偶尔会提到这本他正在考虑写出的书,或者说他已经写出,又或者说在完成了《敌基督者》后不再需要写出的书。
尼采从来都不富裕。他有穷人那种悭吝的习惯,翻来覆去地使用同一个笔记本,直到本子上再无余地。除非笔迹中出现明确的退化,否则往往没有表明时间或思考顺序的线索。他有时从前往后写,有时又从后往前写。有的页面和段落被划掉或覆盖。同一页上既有深奥的内容,又有潦草的购物清单。
正当加斯特埋首于文学遗产之际,银景别墅已然成为一处朝圣之地,在其中,尼采的文本、照片、旧版书和镶着花边的面纱,巴拉圭民间工艺品,以及先驱者弗尔斯特博士的半身像陈列在一起。弗尔斯特博士是崇高的雅利安主义和反犹主义殖民事业的英雄。伊丽莎白在周六举办沙龙,周中举行许多聚会。到访者兴奋地意识到,如某人所说,就在他们上方“只隔一层横梁”的地方,躺着尼采查拉图斯特拉的偶像。有来头的访客被允许远远眺望一眼楼上的身影,他现在总是穿着从圣像图录中借鉴过来的白色长袖亚麻及地长袍。
多愁善感的来访者很容易将尼采神化,出版物中开始出现半宗教性的描述。它们往往着力描述他的双眼。这位崇高的智慧之王拥有一双具备神秘能力的眼睛,超越一切在世之人,能凝视人心之深渊,能企望冰峰之层巅。尼采那双可怜的半盲的眼睛被比作双星、天体,乃至星系。“那时,任何一位见过尼采的人,”鲁道夫·施泰纳写道,“看到他蜷在打褶的白色长袍中,看到他那张高深莫测、充满疑问的高贵的脸,看到他那狮子般雄伟的思想者的头颅,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个人不会死,但他的双眼将会生生世世安息于人类与整个世界的表象之上,在无边无涯的狂喜中睡去。”伊丽莎白请来为其兄长设计纪念碑的建筑师弗里茨·舒马赫说:“看到(他)的人都不会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是一具精神已然逃逸的肉体。人们不得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一位超越了日常琐事的人。”
伊丽莎白乐于在晚餐后展示他。她常常把他布置在半透明窗帘的后面,若隐若现,像降神会上的幽灵。很少有人能像哈里·凯斯勒那样真真切切地看到他。凯斯勒恐怕是最常看见尼采的人,当他有业务要与伊丽莎白讨论时,常常在银景别墅过夜。他会被吵醒,听到尼采发出“长而嘶哑的声音,用尽全力向着夜空尖叫;之后,一切重又归于平静”。
凯斯勒从尼采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病人,或先知,甚至也不是疯子,他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信封,一具行尸走肉。裸露在外的双手,其上的静脉血管青紫相间,如同死尸的手一般蜡黄而肿胀。蓄得过长的胡须,覆盖了整张嘴和下巴,是为了刻意掩饰陷入茫然的白痴状态,遮住不受控制的嘴。与朝圣者们不同,凯斯勒从尼采的眼里什么也没看到——没有疯狂,没有恐惧,没有灵魂。“我倒宁可把他的目光描述为某种忠诚,但同时又欠缺理解,一种徒劳的智力探索,就像你在一只高贵的大狗身上常常会看到的那样。”
1898年夏天,尼采第一次中风。第二年又发生了一次。1900年8月,他患上感冒,并出现呼吸困难。一个也许是担心遭到伊丽莎白长期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证人,报告了尼采的死亡。其描述听起来像是一位照顾该病人多年的护士所做。
他,也许是她,注意到,在被转移至魏玛后,尼采丧失了阅读、理解乃至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尽管这位不幸的患者从来不乏访谈。但这些访谈极少当面进行。所有接触都通过伊丽莎白来推动,所有报告都得经她的手,而尼采则瘫在一旁,无助地躺在那位证人所说的“床垫墓穴”里,被推起的家具包围着,以防止他逃跑。他无法自如行动,尤其是因为,他一看到闪亮的物件就会试图把它塞进嘴里。除此之外,他总体上是一个听话的好病人。他境况凄凉,毫无希望,但他很少有身体上的痛苦。
哈里·凯斯勒证实了以上描述,不过伊丽莎白的新闻简报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尼采从他最喜爱的作家——显然是莫泊桑——那里,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据她说,尼采“直到最后一刻都还保留着他的语言能力。他是多么经常地赞美着我所做的一切。当我看起来悲伤的时候,他又是如何安慰着我。他的感激之情令人动容。‘你为什么哭呢,莉丝贝?’他会说,‘我们多幸福啊。’”。
关于他的死亡,也有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他的濒死状态是痛苦的,但持续得并不长,匿名证人写道,此人显然有临终观察的经验,他(她)接着评价说,鉴于尼采予人深刻印象的体格——“即使在棺材里也威风凛凛”,如果他有足够的求生意志,也许会挣扎得更久。
伊丽莎白对这次死亡的叙述有所不同。将近午夜,她坐在他的对面,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在酝酿。中风令他神色大变,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伊丽莎白喜欢中风这种事。)“看来,这个伟大的心灵就要在电闪雷鸣中毁灭了,然而,他又醒了过来,并试图说话……即将凌晨两点,我给了他一杯提神的饮料,他推开灯罩,以便能看到我……睁开他那双非凡的眼睛,他最后一次凝视着(我的)双眼,高兴地喊道:‘伊丽莎白!’然后,他猛地摇了摇头,心甘情愿地闭上眼睛,死了……查拉图斯特拉就这样死了。”
他逝世于1900年8月25日。
来源:守望者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