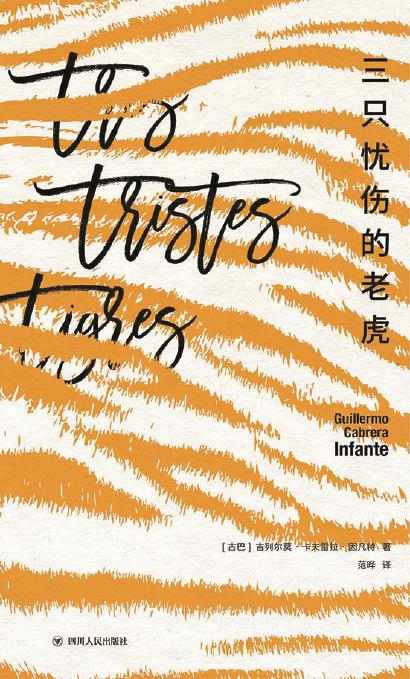“Everything happens in threes”:凡事皆三。
一九六七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出版。同年,古巴作家卡夫雷拉·因凡特的长篇小说《三只忧伤的老虎》出版。同年,一只暹罗猫出生。因凡特收养了她(反之亦然)。因为她常于深夜引吭高歌,其歌声实在难以恭维,足以构成对巴赫(Bach)的冒犯(offense),故由此得名:奥芬巴赫(Offenbach)。
虎,虎,虎
因凡特的写作就好像某种猫科动物命名术:给猫科动物命名,也用猫科动物命名其他。“死亡是看不见的老虎”,他在一部小说里如是说,然后把这部小说命名为“三只忧伤的老虎”——其实这已经是该书的第三个名字,他之前分别命名为“没有边缘的洞”和“热带黎明景观”,直到老虎出山。果然凡事皆三。
作家自承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革命前夜的哈瓦那,而原书名Tres tristes tigres是一个著名绕口令的开头,直译过来就是:“三只忧伤的老虎……”老虎象征着蛮荒之地和异国情调,忧伤可说是最文学化的情绪,至于“三”则是神秘的数字,在作者眼中代表着“可怖的不对称”,“头脑丛林中幽暗的闪光”。在两希文化以降的源流中可以找到太多与“三”相关的文化符码,最常见的便是犹太基督宗教传统中三位一体的上帝。直译成“三只忧伤的老虎”,不失为有趣的书名,但损失也不可免:首先绕口令的味道荡然无存,中文里“三只忧伤的老虎”完全不绕口,作家这方面的意图就落了空。我遍寻各种绕口令大全,终究没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为了凸显语言游戏色彩,选取不相干的中文绕口令做题目,在语义上、联想轴上的指涉又会丧失。曾想出个差强人意的方案:《苦虎图》。首先“苦ku-虎hu-图tu”韵母重复,凸显音韵上的疏异感;语义上“苦”勉强能和“triste”产生一点关联,“虎”也幸存下来。至于“图”,这部小说确实是一幅一九五八年份的哈瓦那夜游图。可是“三”哪里去了?——题目这不是三个字么。
其他语种的译者前贤又是如何处理的?法语译本并无悬念地翻译成Trois tristes tigres,毫不费力,罗曼语族同气连枝,羡慕不得。德语按字面译成Drei traurige Tiger。而英语译家经过漫长的寻索(three sad tigers,three tired tigers,three flat tigers,three triped tigers,three-tongued tigers,three triggered triggers),最后译成Three Trapped Tigers,可以看到字义上有所牺牲:“triste(忧伤)”变成了“trapped(被困)”,但藉着同为西方拼音文字的优势,成功保留了TTT的“类头韵”形式。因凡特表示这已经是众多选项中最不坏的一个,或者索性不译,直接用西语原书名。作家还不无戏谑地加上一句:“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出版人的意见,他们是最好的裁判官。”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漫长的上下求索之后,中文版还是老老实实地照字面翻译,纵虎归“名”。
《三只忧伤的老虎》里没有老虎,有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哈瓦那,出没于酒吧、夜总会和滨海大道之间的夜行动物:作家、摄影师、演员、歌手和鼓手,及其他城市浪游者。据说在哈瓦那夜生活黑话里他们都可称为“老虎”,这样说来可远不止三只。因凡特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些老虎在新的时代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绝。作为纸上的濒危动物保护者,他能做的就是用超载的文字圈出一片记忆的保护区。
斑纹学入门
《三只忧伤的老虎》自身就是一只斑斓虎。书中曾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繁人物比作老虎的斑纹:“……对老虎来说多一条斑纹算什么?”动物学家告诉我们,每只老虎的斑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乍看上去只是随机线条的混沌迷宫。斑纹是一种反秩序的秩序,就像富恩特斯在《西语美洲新小说》里说的:“我们的作品必须是无秩序的作品,也就是说,作品中如果有一种可能的秩序,就是跟现今的秩序相反的秩序。”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简称“红学”,研究《文心雕龙》的学问据说简称“龙学”(毕竟不能简称为“文学”),谈论《三只忧伤的老虎》不好称“虎学”,索性称之为“斑纹学”。斑纹学方便法门有三:曰对称,曰离合,曰隐显。
先说对称。全书“序幕”从一个男人(夜店主持人)的独白开始,“尾声”以一个女人(公园里的疯女人)的独白结束。开场时宾客如云,散场时无人理会。如此这般对称的斑纹不止一组,紧接“序幕”的“首秀”第一场,是小女孩用第一人称讲述童年轶事,而“尾声”之前的“第十一次”,求诊的女人也讲了一个小女孩的忧伤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她童年时代的小朋友,但讲到最后她忽然说:“有时候我想我的小朋友就是我。”
再看离合。可以从炫人眼目的斑纹中挑出离散的一束,比如“星星丽雅”的故事被分成八部分,都冠名为“她唱波丽露”,合在一起就成了这位传奇黑人女歌手的小传。而另一位女性角色的独白却是按数字命名:“第一次”“第二次”……讲述劳拉·迪亚斯去看精神科医生的十一次经历。“星星丽雅”与劳拉(有人在她的名字Laura里读出了aura“黎明”),一黑一白,一夜一昼,她们的故事错落贯穿全书,神光离合,俨然一条条连缀呼应的斑纹。
三看隐显。在斑纹丛中寻出若隐若现的幽眇纹路。比如“游客”的故事讲了四遍,说的是美国游客坎贝尔夫妇的哈瓦那周末游,坎贝尔先生讲述在前,坎贝尔太太的勘误在后,这算两遍;紧接其后同样的叙述者同样的故事夫妇俩又各讲了一遍,这就是四遍。到了后文才有交代,原来是某位美国作家坎贝尔的短篇小说被译为西班牙语准备在杂志上刊发,却因译者里内·莱阿尔(“Leal”这个姓氏在西班牙语里恰好是“忠实”的意思,绝妙的讽刺)太过直译,生硬蹩脚,总编无奈之下只得找人重译:“西尔维斯特雷,里内的翻译很糟糕——这么说是避免使用其他形容词,那将是一句脏话。我恳求你在里内稿子的基础上另写一稿。我也发给你英文原稿让你看看里内是怎么完成……”此处总编的落款只有GCI三个字母,正是本书作者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的姓名缩写,在现实中他的确曾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两版译文风格迥然不同,里内那一版时序上本应在前,但书中却在西尔维斯特雷的版本后出现,是最糟糕意义上的翻译腔——作为中译者我又遇上了翻译生涯中的新挑战,以前总要努力翻好,这里却要努力翻得糟,还得是让人能一眼看出的糟糕——一味直译硬译死译,还出现了不少望文生义的错误,比如“第一根手指”明显是英文“first finger”的误译。但无论是里内版本还是更流畅好读的西尔维斯特雷版中,坎贝尔先生的讲述都洋溢着浓浓的大男子主义腔,坎贝尔太太都在致力于揭露丈夫的虚伪和自负,夫妇二人的共同之处则是新帝国公民莅临老殖民地,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我看不懂的即无意义,与我不同者即缺陷——啊,这迷人又危险的他者!另外我们且不要忘了,坎贝尔先生在(小说的)现实中是位单身的小说家,坎贝尔太太其实是他的虚构。书中提到的“英文原稿”我们无从看到,因为本不存在,那是小说家因凡特的虚构。虚虚实实,是耶非耶,两版没有原文的译文交织起文内文外的现实,俨然彼此对立又彼此映衬的斑纹,让人初见时费解,再看时晕眩,三看时忧伤莫名。翻译与原作,自我与他者,虚构与现实,种种有形的斑纹夹杂着层层隐蔽的纹路。
在全书的核心位置,把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的事件讲了七遍,题为:“不同古巴作家笔下的托洛茨基之死,事发后或事发前”。从古巴革命的先驱何塞·马蒂到杰出的女人类学家卡夫雷拉·莉迪亚(洛尔迦著名的《吉普赛谣曲》中就有一首题献给她),从美洲巴洛克的集大成者莱萨马·利马、“神奇现实”的施洗者卡彭铁尔到深受非洲文化影响的诗人尼古拉斯·纪廉,追摹七位经典作家的文风笔法,或华丽,或玄奥,或煞有介事,或繁复夸饰,以戏仿的方式浓缩了一部二十世纪古巴文学史,风格各异,焕然有章。看似炫技式的“风格练习”背后隐藏的是个人风格的消解:当一个人有七种腔调,七套笔墨,那么到底哪个才是自己的声音?当一桩事实可以用七种方式讲述,那么哪一种才是历史的真实版本?或者说,本就不存在唯一的真实,历史与记忆注定在讲述中遭遇背叛?
背叛之书与命名术
《三只忧伤的老虎》里没有常规意义上的反派人物。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反派的话,因凡特说,那就是背叛。有人背叛了家庭,有人背叛了爱情,有人背叛了友情,有人背叛了老师,有人背叛了革命(或反之亦然),有人背叛了自己,“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当激动人心的伟业背离初心,乌托邦就成了敌托邦。《三只忧伤的老虎》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背叛:“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任何雷同,均属巧合”,本书开篇便作如是说。这就像波丽露舞曲中的海誓山盟,谁相信谁是傻瓜。随后又号称“本书用古巴语写作。也就是说,用古巴的各样西班牙语方言来写,而写作不过是捕捉人声飞舞的尝试。”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尝试,写作或文字终究要背叛人声。书里不止一次出现“当时那情景真值得听听”“你真该听听”“不过还是得听他自己说才更有味儿”以及类似的说明,而我们作为异时空中的读者,当然不可能听到。作者在暗示自身书写的局限,以及背叛的宿命。想想全书卷首所引刘易斯·卡罗尔的话:“她试着想象蜡烛熄灭后会发出怎样的光”,烛火熄灭后的光彩只能在回忆中焕发,而追忆逝水年华就等于背叛失去的时间,就像书中库埃突然问“我”能不能回忆起一个爱过的女人,在“我”做出肯定回答并详加描述之后,库埃却悍然断言“我”根本没爱过,“那个女人不存在,是你刚刚编出来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爱,如果你真的爱过你什么也不会记得,你根本记不住嘴唇是薄是厚。或者你能记住嘴但你不会记住眼睛如果你记住颜色你就记不住形状,你永远,永远,永远不可能做到记住头发额头眼睛嘴唇下巴和腿和穿鞋的脚还有个公园。永远不可能。……你只会看见那双看着你的瞳孔,至于其他,相信我,都是文学创作。”都是文学创作,都是追“译”逝水年华:往昔之于记忆,一如原文之于译文,而“翻译,即背叛”。
作者的另一自我,“老虎”们的精神导师牾斯忒罗斐冬语出惊人,他说真正的文学应该写在空中,自己也是如此实践: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遇刺记演义七种都是他的口头创作,经弟子们录音又违背老师的意愿保留誊写出来,造成双重背叛:“被背叛的遗嘱”与被背叛的空中文学。最讽刺的是,极力反对书写的人却以这样一个绰号留名于世:牾斯忒罗斐冬(Bustrófedon,Boustrophedon)本义是书写的方法,“牛耕式转行书写法(一种古代书写法,由右至左,再由左至右互错成行,古埃及语、古希腊语等曾用过这种书写方法)”。前缀bous-即古希腊语中的“牛”,所以我在发音近似的前提下特意选择了牛字旁的“牾”,取“背逆”之义(“牾,逆也”),因为他总是逆潮流而动,与常规背道而驰。连牾斯忒罗斐冬也“背叛”过自己:作为狂热的词典读者,语言游戏的重度沉迷者,谐音的情人,回文的猎人,他不会不知道像回文这样的游戏只能存在于文字中,因为顾名思义,回文读起来正反都是一样,“是对听觉的欺骗”,所以必须写出来。写出来的回文是不得已的背叛(文字背叛声音),被翻译的回文是不可免的背叛(译文背叛原文)。比如在书中牾斯忒罗斐冬引用的“Dábale arroz a la zorra el abad”,字面意思就是“修道院院长给雌狐狸米吃”,我绞尽脑汁勉强翻译为:“糊米烹米糊,胡寺僧饲狐”,虽说是拆句自行降低了难度,但好歹把回文译成了回文,可称背叛之背叛……
全书最后也是最长的部分Bachata,原文是“欢闹,舞会,派对”的意思,所以我音译为“巴恰塔”的时候选定了恰恰舞的恰,同时考虑到Bachata里包含了巴赫的名字Bach,我毅然决然将全书里出现的“巴赫”都换成另一通用的译名“巴哈”,以中文的字形相近(恰-哈)对应原文中的字母重合,也为了处理下文的语言游戏:“我现在听着巴哈在库埃评点的间隙想象着如果牾斯忒罗斐冬活着会编出怎样的语言游戏:巴哈,巴哈士奇,巴士拉,巴士底坑(分布在水泥地上,打断了滨海大道的空间连续),芭哈娃娃,巴哈瓦那,巴恰塔,巴恰恰恰——听他用一个词编出一部辞典。”这里描写的是两位主人公,两只老虎跑得快,库埃载着西尔维斯特雷驱车夤夜飞驰在哈瓦那的滨海大道上,广播里在放古典音乐,“库埃一边开车一边哼着音乐摇头晃脑,时而握拳向前表示forte(有力地),时而张手向下表示pianissimo(极弱),走下一级级无形的,想象的音乐阶梯,好像手语专家在翻译演说。……
——你难道听不出老巴哈是怎样摆弄D调吗,怎么设立他的模仿,怎么让变化出人意料地出现,但总是在主旋律允许和提示的情况下,从不提前,从不滞后,但仍能让人惊奇?你不觉得他是个完全自由的奴隶?哈,老伙计,他比奥芬巴哈更好,我发誓,因为他在here,hier,ici,这里,在这哈瓦那的忧伤里,而不在什么巴黎的欢乐里。”
就在他大放厥词的时候一曲终了,电台主持人开口:“女士们先生们,您刚才听到的是D大调大协奏曲,作品第11号第3首,作曲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据说这就是古巴文化中著名的Choteo,《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词典》简洁地解释为“戏弄,开玩笑”,而古巴学者如Jorge Ma觡ach却从中提炼出民族性的特质,即嘲弄自封的权威,不接受按部就班的现实,报之以微笑讪笑哈哈大笑。按书中人的说法:“这很古巴。在这里必须把真话当俏皮话说才会被接受。”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全书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俏皮话,谐音梗,以及明引暗藏的音乐、电影、文学典故“秀”……所有的饶舌与离题,东拉西扯旁敲侧击,都因为无法轻易说出最重要的名字。
一九七二年,因凡特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在伦敦的一家医院中接受了22次电击治疗。他还主动要求医生增大服药量,因为感觉耳边总回响着老虎的咆哮。医生苦笑着回答:因凡特先生,我们医院旁边就是海德公园啊。
这位伦敦医生没能真正理解他的古巴同行(因凡特早年曾学医,后来弃明投暗从文),就像书中给牾斯忒罗斐冬开颅的医生,只知道把患者的“语言呕吐症”归结为脑损伤。这只在耳边咆哮的看不见的老虎是死亡,是遭背叛的理想,回不去的往昔和故乡,同时也是流亡中呓语和失语的自己。科幻电影爱好者因凡特常说,唯一的时间机器是打字机。他的写作是猫科动物命名术&驱魔术,因为降服心魔之虎的最佳方式就是给它起个名字。
有一次摄影师内斯托尔·阿尔门德罗斯在老友因凡特家里留宿,半夜梦见自己被老虎吞噬,惊醒时发现一只十二磅重的暹罗猫正卧在自己胸前无声凝视。它的名字是奥芬巴赫。
文/范晔
来源/文汇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