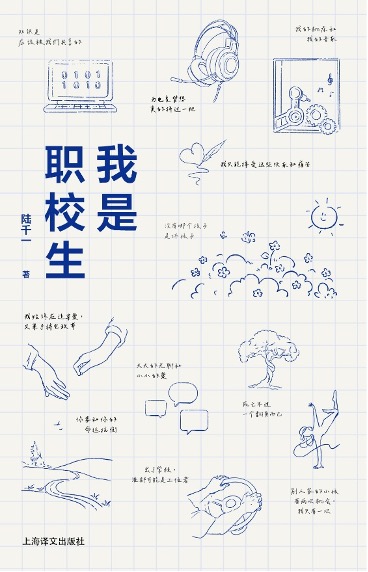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人称书系”第二部作品《我是职校生》首发上线。作为国内首部师生共创的00后职校生自述文集,该书通过12位职校生的原生叙事与师生共创的独特视角,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理解职业教育与职校青年的窗口。分享会上,作者陆千一结合自身在西北职校的执教经历,讲述了这本书的创作初衷与过程,引发了关于“职业教育该走向何方”的深度讨论。
“局内人”讲述职校师生的真实处境
《我是职校生》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题材书籍,更是一部扎根现实的“生命自述录”。作品由1篇作者自序、12篇受访学生自述、1位专业课老师自述构成正文,呈现了我国西北地区一所大专职业院校师生多样的人生故事:错失的电竞理想、模糊在记忆中的恋爱、对自由生活的期许……背景和个性迥异的学生细述来路、剖陈愿景,经老师陆千一转写后,文字饱含原生力量。
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人称书系”旨在以亲历者视角呈现当代中国的时代议题,涵盖农村/城乡、打工人/新工人、行业故事等领域,而《我是职校生》则精准切入“职业教育”这一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赛道——中国40%左右的同阶段在校生为职校生,他们常被贴上“不努力”“没出息”的标签,却鲜有机会在公共话语中主动表达。经由这部作品,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叙事空间,以“局内人”的视角讲述职校师生的真实处境。
从“记录者”到“共创者”
分享会上,陆千一回溯了《我是职校生》的创作历程。2022年,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陆千一进入西北一所职业院校执教两年,任语文教师。习惯写作的她开始在社交平台记录与学生的日常,不想意外引发媒体关注,也有编辑开始邀约她创作职校主题作品。
“起初我很开心,觉得是文学创作的机会,但很快发现不对劲。”陆千一在分享会上坦言,彼时多数关注的目光将“职校生”视为一个“社会议题”,而非“具体的人”——“他们想知道‘职校生群体有什么问题’,却不想听‘这个职校生有什么梦想’。”这种视角让她陷入犹豫,最终她推掉所有媒体邀约,用半年时间推翻初稿,决定“把叙事权还给学生”。
此后一年多,陆千一以“访谈+转写”的方式,与200余名学生深度交流,最终筛选出12位受访者。他们中有想“在奶奶家院子里修零件、弹吉他”的陈楷夫,有希望“把计算机教给更多同学”的计算机生小舞,也有懵懂探索爱情理想状态的杨铁……“学生的语言里有原生的力量,比如他们说‘打螺丝’(代指流水线工作),说‘死亡不过一个翻身而已’,这些不是我能写出来的。”
“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都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面镜子。我希望呈现出不同个体尽可能丰富的侧面,至于如何为群体画像,则是留给读者的议题。”陆千一表示,受访的学生们或许并不熟悉访谈、创作和出版,但他们喜欢自己的故事,认可记录的意义,有学生在受访后告诉陆千一,“把家乡和成长讲出来,像和自己和解了”,这让她更加确定“自述体”的价值——不是“我写他们”,而是“我们一起完成故事”。
看见职校生的理想与困境
分享会现场,陆千一通过书中片段,还原了职校生被忽视的多面人生:他们并非“放弃努力”的群体,而是在教育筛选中被边缘化的“追光者”——有人为电竞梦想休学一年,即便最终进入职校也不后悔;有人利用课余时间教同学计算机知识,想打破“职校生只会打游戏”的偏见;有人悄悄兼职攒钱报街舞班,因为“喜欢的事不能放弃”。
这些故事背后,也折射出职业教育的现实困境: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查课、收手机成为日常,却难以保障实践教学质量;部分老师照本宣科,与学生刻意保持距离,甚至将学生视为“待输送的底层劳动力”;家长或外出打工或无力管束,学校成了“安全托管所”……陆千一提到,有学生自嘲“在学校玩够了,假期出去打螺丝才有力气”,这句话的背后,是职校生在“教育期待”与“生存现实”间的无奈平衡。
“这本书的价值,不止于记录,更在于‘破界’。”长期以来,职校生被简化为“中考/高考的失败者”,但书中12位少年的故事证明,他们有理想、有尊严、有对抗命运的勇气。《我是职校生》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机床与音乐”“爱与遗憾”的故事,填补了主流叙事对这一群体的空白。
陆千一提到,有学生收到书后给她发消息:“原来我的故事也能被印成书,原来有人真的想听我说话。”这句话或许正是《我是职校生》最动人的意义——它不仅是一部纪实作品,更是一面镜子,照见40%职校生的真实人生,也照见社会对“成功”与“价值”的多元可能。正如该书推荐序作者、《县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所言:“这部书让‘山重水复’的职校生人生,显露出‘总有路’的可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