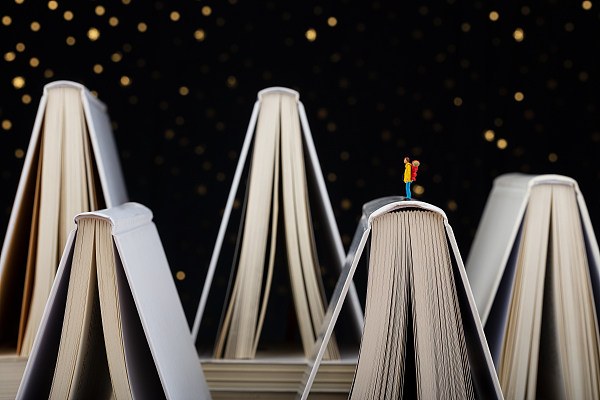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上学时候学的那些东西我早都忘光了,书本知识也早都还给老师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这样说没错。从小到大,我们听老师们讲过许多堂课,忘掉一些东西也很正常,如果我们脑子里塞满了学过的知识,那么可能也就没有了更新资源的空间。有时候,遗忘正是为了更好地获得。事实上,我们学过的东西,早已刻在脑子里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平时用不到的时候,它就在那静静地蛰伏着,到了关键时候会被突然触发,为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打开思路。“书到用时方恨少”,恨少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忘了,而是因为储备不足。
对于老师,也没有必要因为多少年以后学生会把学过的知识还回来而沮丧,因为除了点点滴滴的知识灌输外,老师们在课堂上的苦口婆心,总会有那么几句话能触动学生的心。老师的影响力是发散型的,一些同学传承了老师讲过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另一些同学则实践了某些具体的知识,“润物细无声”大抵就是这样的。
德国学者斯蒂芬·格伦德曼与卡尔·里森胡贝尔主编的《20世纪私法学大师——私法方法、思想脉络、人格魅力》一书,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四十位德国私法学者的故事,讲述者正是这些学者们的“门生”,即他们的学生、研究助理、追随者或伴随一生的对话者。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门生视角”,是“门生眼中的导师们”。导师们的学术贡献自然是要重点介绍的,导师们对学生的指导方法、讨论课的氛围、对学生独特的影响力,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读完此书,我们不仅能提纲挈领地把握某位学者的学术观点,还能让我们浸润于大师们春风化雨般的感召力。
老师在课堂上“授业”的直接影响力,是其门生对老师学术观点的传承,而一代代人之间的薪火相传,就会在学界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派,“师门倾向于小规模,十位年轻学者在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的领导下跨越30—40年,他们之间经常相互融合、相互讨论”,而“属于同一个学派的成员很少在一个学院,他们大多数分散在不同的大学”,这样就可以使同一个学派的观点在不同的大学得到传播。
比如,德国学者库尔特·比登科普夫在介绍他自己有关反垄断法观点的形成过程中,就介绍了其师承关系,“我始终相信,企业采用私法的工具限制竞争及基于此种方式获得的势力损害第三人的自由,这与宪法精神相悖。从原则上来看,我的这种方法原则从克龙施泰因和柏默那里所学的知识,即对私法的理解。”
在经济法上的势力问题上,库尔特·比登科普夫也谈到了他的学术渊源,“在弗朗茨·柏默那里,我意识到企业以私法的方式组织经济势力的问题。我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同事麦斯特麦克也让我更加熟悉了相关问题,作为一个年轻的助理,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我的第一份反垄断法方面的研究项目。这样一来,一群人,有老师,有门生,提出了关于战后的经济势力和私法之间关系的问题。”有这样一个“学术群”共同研究一个或一系列问题,主张并传播一种学术观点,久而久之,学问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自然会扩大。
除了学术的传承这一途径外,老师还可以通过学生对社会实践发生影响。在学校培养的学生中,只有极少部分会在未来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绝大多数人还是要走上社会从事实际工作的。比如法学院培养的学生,其未来就主要还是以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为主,在这一群体中,老师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或许会影响他们对某类案件的裁判思路,这就间接地在社会上得到了传播。所以,老师们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观点“另类”,当自己培养的学生走向社会后,运用你的观点处理纠纷时,这种观点也会慢慢地被人们接受。
私法学者彼得·施莱希特里姆编撰的债法领域的权威教材,其序言中就提到了这种情形,“作者在阐明德国债法的基本结构及梳理未来继续发展的原则性新导向已产生或有待进一步处理的问题方面,有自己的确信,哪怕其观点与主流观点相违背。按理来说,作者在精要教科书中应该在细节处,放下自己也许与众不同的观点。但当讨论关乎法律未来走向这一根本命题时,它们无论于课堂里还是在精要教科书中,对此都不应当省略。在此种情况下,学生就是最为重要的谈话对象,理由是今日某种学派可能仅是单个的并且偏离传统的观点,但他日,当学生开始参与法律实践、散布于学界时,该观点很可能成为通说。”也就是说,老师的观点或许在当下不被接受,但当你在课堂上告诉学生,或者在教材里加以阐明的话,当学生们参与到法律实践中时,它就会像星星之火一样,发展成燎原之势。
因此,当人们说书本上学过的东西都已忘了的时候,不必当真,要不然怎么会有学术的进步呢。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知识所种的“因”,都会结出学术或法律实践之“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