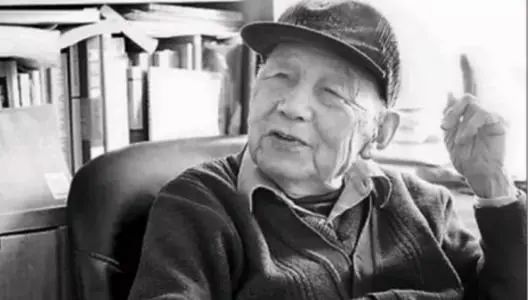对于学界来说,5月28日是悲伤的一天,知名历史学家何兆武、章开沅的相继离世,让许多后辈学人深感悲痛。
身为历史学家、翻译家的何兆武先生,1921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何兆武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研究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何兆武先生
章开沅先生则于1926年7月生于安徽芜湖。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中原大学,后来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章开沅先生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于2018年获颁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章开沅先生
2006年,何兆武先生推出了口述史《上学记》,这本书后来成为了许多普通读者都喜爱的“枕边书”。先生在书中谈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文史学者刘超曾评价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一经推出即受到多方瞩目,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上学记》写的是何先生青年时代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在阅读这本《上学记》时,作家龚静注意到许多蕴藏于简单话语间的“大哲理”,并在读完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将这本书放在案头随时翻阅,从中获益良多。她说:“为什么何兆武先生的幸福观那么令我难忘呢?还是因为‘有希望’吧。”今天的夜读,谨以这篇短文形成对先生的纪念。
何兆武先生
幸福感
目下社会都在说“幸福”这个词,某些机构还常常发布什么关涉幸福指数的报告,按照惯例,提什么缺什么,大家都感觉不幸福了,或者不觉得幸福了,才会如此风靡,甚或某主持人的新书名也是:“幸福了?”赫然问号,幸福与否自然是不确定的。
如此幸福惑自然在纸莎草、羊皮书、竹简线装书、石版活字、电脑打印诸多版本中可以找到多种讨论,先贤时哲也罢,普罗大众也好,每个人对幸福的想法感觉追求自然各各不同,有的以物质多寡为基础,有的重心灵感受,不过,当世幸福之题中要义大概总不离先从物质说起,确也是理,生存尚维艰,清风朗月尚一时清鲜罢,先吃饱饭有地睡觉再说其他。不过,何以吃饱了饭,或者说吃得还挺好,也有房住,仍然不觉得幸福呢?是幸福燃点太高,还是幸福太过精灵,就是不让你抓住?
大概阅读的时间段正与坊间讨论吻合,我总是会想到《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一本回忆录,从作者的出生年月1921年写到1950年,这是一段多么丰富跌宕的历史啊,尤其在西南联大的七年,其间的联大老师和学生风貌,分外传神,有许多作者特别的观察和体验。读完一年多了还是放在案头,随时翻翻,好像有许多牵挂在它身上,它也仿佛总是要引人思绪一番。我体悟深切的一部分就是作者的幸福观。
书中多处提到“幸福”。“到底应该怎么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如果单纯从物质的角度讲似乎比较容易,可是人生不能单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比如你阔得流油,整天吃山珍海味,这就表示你幸福了?恐怕不单纯是这样,百万富豪不也有跳楼的吗?……抗日战争期间,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这是何先生十六岁时的思考。
谈西南联大生活,又说到了幸福,“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所以,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生活也非常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什么影响,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还有一处又提到幸福,是作者和同学王浩(后来的逻辑学家、哲学家)讨论幸福,何先生认为:“幸福是一种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rch Leiden,Freun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这次谈论何先生说服了王浩,“不禁心里一阵快慰”。
作为作者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不只停留于个人的幸福,而和社会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如他在书中所说到的“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好比英国诗人堂恩(John Donne1572-1631)有首诗叫“no man is an island”(每个人不是一座孤岛),在一个大环境中,个人其实是无法置身于外的。好比克里希那穆提所说的“你是怎样的,那么世界就是怎样的”(大意)。也因此,在艰难的环境中,这一代人始终保持着希望和乐观,在“上学”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怀,而这种关怀也使他们将自己的志业与社会进步、发展联系起来。
为什么何兆武先生的幸福观那么令我难忘呢?还是因为“有希望”吧。虽然,过去、未来,其实都是一种现在,大家都在说生活在当下,静观当下的思维/感受/内心的声音,好比禅,吃茶时吃茶,做事时做事,身心安住于生命的这一刻。这样的时刻就是幸福的。是的,这是一种安宁的生命状态,无思无欲,静心涤虑,好比静坐时进入禅定的状态,此时外界是不存在的,惟有内观凝视。有心理学家认为,当你执著于某件事情时产生的一种“心流”,它给你带来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这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个体心灵浑然的美好状态。可是,当一个社会的人置身于社会中,听到的,体会到,直接面对的,有很多的不幸,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悲剧,能不内心波动?你会不忧虑你生活于此间的自己的未来吗?大概这也是何先生所说的“通过苦恼的欢欣”中的苦恼,然而欢欣在哪里?“心流”的状态是一种欢欣,有希望的生活或许更是一种欢欣。好比航行着的船是有目的地的,而非到哪是哪,海图不必,罗盘不必,随它去吧。如此,船上片刻的欢欣实在也是大悲哀中的欢欣片刻。或许,宿命地说,人能拥有的也只有片刻的欢欣?尽管个人还是希望“有希望”才是人在人间走一回的存在理由。
西南联大旧照
还是《上学记》,谈到其时学校/社会氛围,提到“高干子弟”,那时作者身边有不少同学家世显赫,父亲是谁谁谁的很多,但“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可见当时根本没有这个风气,对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分并不关心。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见该书P239)。这样的观念认同,也是给予人希望的社会氛围吧。希望中的心灵终是有福的。
白川静解释“幸”字:“象形,手枷之形。看古字形可知,此字形示铐住双手的刑具手枷。……‘幸’本义当为‘倖’(侥幸,幸好)。仅仅是双手被手枷铐住,就算通过了惩罚之关,真算得上是侥幸。得以免除严刑,算是幸运,由此,‘幸’生出美好、幸福之义”(《常用字解》)。
免于枷锁,当然是幸福。免于恐惧,当然就有希望,心生幸福。实在而言,幸福指数之类的调查恐怕是凌虚蹈空的,在土壤污染、食品安全时爆危机的时代环境下,人若有安全感了,有希望期盼之心了,当然个体生命也需拥有寻找幸福、“通过苦恼”的能力和努力,幸福指数不必调查,也昭然于人心的。
文/龚静
刊于《文学报》2011.05.12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