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这里坦白的是,在每一趟旅途中,我都濒临体能和心理的极限,穷尽所有的智慧。”刘骁骞这样写道。
2014年巴西世界杯前夕,为了表现赛事举办前里约的毒品、枪支、治安等改善情况,5月1日到3日,央视新闻频道《东方时空》播出了《走进“上帝之城”》。片中,记者刘骁骞深入圣保罗贫民窟毒品交易的最深处,介绍着毒贩们如何分工装袋可卡因。

周围,盯着他的是毒贩士兵,他们的手里拿着AK47(突击步枪)、AR15(自动步枪)。
这不是刘骁骞第一次“以身犯险”。
在9年的巴西驻外采访中,刘骁骞走访了亚马孙雨林深处的缉毒重镇,跟随警察在西南腹地拦截运毒的车辆,暗访乌拉圭与巴西边境的走私枪支黑市,采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贩毒集团,拍摄拉美“银三角”的可卡因制作工序,他和摄像沿着毒品枪支在巴西的足迹,试图拼凑出完整的贩毒链条。
根据这段经历撰写的图书《陆上行舟——一个中国记者的拉美毒品调查》下周正式上市,书中不仅系统性回溯了刘骁骞的调查经历,还通过他的探访和观察探讨了造成巴西当前治安问题的根源。“从新大陆的殖民史、奴隶制,再到军人独裁时期以及后来历届巴西政府的举措,都无法摆脱它们盘根错节的责任。”刘骁骞希望,读者能从书中窥见这张因果交映的无形之“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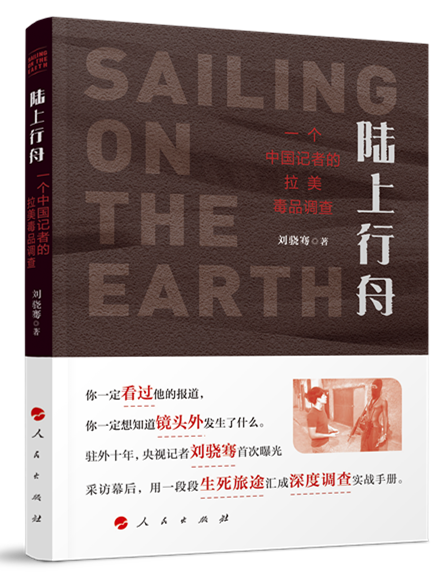
社会话题与巴西“愤青”
刘骁骞第一次去巴西是2007年,那时他还是中国传媒大学葡萄牙语专业的大二学生,去巴西参加为期一年的交换生项目。再回巴西则是担任央视驻巴西记者,从2011年一直工作到2019年3月份,前后加起来,他在巴西生活了将近9年。
巴西是个采访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度,狂欢节、足球、社会热点为记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选题。一开始,刘骁骞就盯上了社会话题。他发现圣保罗这座南半球最大的城市有个独特的现象,在城市工作的白领们为了抢一个车位,通常凌晨4点就把车开到了工作地楼下,然后有人睡在车里,有人直接睡在路上,还有人通宵听音乐。
很快,刘骁骞的兴趣就转移到了更硬核的选题上。驻外记者通常要和当地摄像合作进行拍摄。和刘骁骞搭档的摄像叫Ale,中文名阿力,之前拍过社会题材的纪录片,是个很有情怀的巴西中年“愤青”。
阿力的情怀有例为证。一次刘骁骞和阿力去亚马孙一个特别小的小镇采访,一个当地的小朋友把阿力错认成了巴西电视台一位著名的主持人,要求和他合影。遇到这种事,普通人一定会说:“小弟弟,你认错人了。”但阿力没有,他特别热情地和小朋友合了影,然后对他说:“你要好好学习哦,长大了你可以像我一样做很有意思的节目。”
这么有情怀的阿力把刘骁骞引向了亚马孙雨林保护、印第安文化存续的报道领域。对于“做亚马孙流域的任何报道都非常难,通常驻外记者要在巴西驻扎几年之后,才会深入这个领域。”刘骁骞解释说,“首先,这个地点太难到达了,你通常要转两次飞机,然后开十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再做小快艇,8小时一直开不能停的那种,中途休息都是在帐篷里,经常没饭吃。”

刷牙,在鳄鱼“深情”的凝望下
阿力特别能吃苦,他传授给刘骁骞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最实用的就是野外洗澡。亚马孙河畔的天体裸浴绝对是个技术活。“你想象不到夜晚,外面有多黑,是那种把眼睛遮起来的黑,一点点亮都没有。”河里还有鳄鱼,被咬一口,断手断脚,每年被鳄鱼咬伤的人不计其数,所以当地政府规定每三个月可以捕捞一批鳄鱼卖。
刘骁骞记得,有一天早上他在河边刷牙,发现河里有个反光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一条鳄鱼正在深情凝望着他。“幸好是早晨啊。”在这种情况下,夜晚下河洗澡,谁能不怕。
阿力倒是有个一个缓解恐惧的办法,“你要专注在洗澡这件事上,别想别的”。不过,刘骁骞说,尝试了很多次,他始终不敢往河里走太深。除了下河,在野外洗澡你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冲到热带午后的阵雨中,直接冲淋;比如采访哥伦比亚游击队时,在一面是挡板一面直面安第斯山脉露天地里洗澡。传奇吗?传奇!好玩吗?绝对不好玩!
有一次,刘骁骞在朋友圈留言,“接了雨水喝,喝前放点糖就当杀毒了”,有人留言:“你应该把水煮开了再喝啊。”
“但在亚马孙丛林里拍摄,你是真没条件为了喝杯水还生一把火啊。”
驻巴西9年,刘骁骞在亚马孙流域采访整整15次。
“奥斯卡别跟他去,他会杀了你”
难以抵达、条件恶劣之外,亚马孙的采访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让刘骁骞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他和阿力拍摄亚马孙丛林非法砍伐的那次经历。千辛万苦到了目的地后,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打了一个大雷,然后全镇停电,这还是亚马孙流域很发达的小镇。停电导致电话信号中断,刘骁骞几人只好每天开车两小时去联系人那询问采访进展,然后再开两小时的车返回小镇。
死磕了几天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非法木材商。他答应带领记者们带去雨林的最深处去拍砍伐现场。但当天,双方接上头已经很晚了,木材商提议“你们今晚就住我的庄园吧。”
与刘晓骞同行的还有一位路透社的记者,他常年报道非法砍伐题材,他苦劝刘骁骞:“奥斯卡(刘骁骞英文名),不要跟他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他会把你杀掉。”刘骁骞和阿力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去。“我们一直知道有非法砍伐,但根本不敢想象能去现场拍,这就跟你去拍毒品的交易现场一样,是很难的事。今天我要走的话,我这辈子都有遗憾。”
公开买命的木材商也有委屈
两人去了才知道,所谓的庄园不过是两间破烂的小木屋,人还是要睡在帐篷里。当晚,刘骁骞睡得很熟,“之前的行程太累了”,半夜隐隐约约听见外面吵吵嚷嚷,但就是累得睁不开眼。一觉醒来,天光大亮,木材商却说:“听见你们来拍摄,伐木的那批人连夜撤走了,我也拦不住。”结果还是没拍到。
这个故事还不算结尾。三个月后的一天,刘骁骞接到一个当地专门研究非法砍伐的学者打来的电话,他问:“奥斯卡,你有那个木材商的画面吗?”原来,那个木材商正在悬赏5000雷亚尔买他的人头。5000雷亚尔当时折合1万多人民币。实际上,因为曝光非法砍伐,木材商们杀了很多记者和学者,这也是路透社的记者规劝刘骁骞的原因。
那么,公开买命的木材商为什么会接受公开采访?刘骁骞分析:“其实这个人也很委屈,他买了亚马孙雨林这片地,有一天政府突然把这片地划成了印第安保护地,不许木材商动用地面上的任何资产,政府规划完后又不采取具体的措施。结果,木材商和印第安人激烈冲突,非法砍伐屡禁不止。作为木材商,他也需要一个平台诉求自己的利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线人,贩毒组织高层的侄子
毒贩也有“合理”的诉求吗?
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有736个贫民窟,刘骁骞在《走进“上帝之城”》中拍摄的那个是里约市最危险的贫民窟中的一个。
为刘骁骞铺路的是一个巴西线人,2012年,这位线人主动联系了刘骁骞。在他发来的邮件中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两个深色皮肤的男子骑着一辆摩托车,后座上的男子扛着一把长的狙击枪。“照片上的人是贫民窟里的毒贩……”两人就此有了联系。
“接触下来,我了解到,这位线人也居住在贫民窟,但并不是贩毒组织中的成员,他会摄影,有新闻理想,想有一点作为,后来一次采访后,我从背景音里听出,他好像还是贩毒组织中一个高层的侄子,这就难怪他能提供独家资源了。”一年交往之后,刘骁骞向线人表达了想要采访贩毒集团的想法。

毒品加工窝点
《走进“上帝之城”》中的毒品加工点原本是一户人家的车库,屋内有两张铺着旧报纸的长方形木桌,桌旁的人拿到碟子后用一根细细的铁勺将可卡因一勺一勺地舀进细长的塑料包里。负责分包的几个人效率很高,每包几乎只耗时一秒,一时间桌面上方穿梭着许多透明的塑料包,像是武侠小说里高手过招时飞舞的雪白衣袖。
毒品标签上写着“如有质量问题,请到购买处申诉”
刘骁骞在桌子上发现一沓厚厚的粘贴纸,那是毒贩设计的标签,上面印有可卡因的价格、贩毒集团的名称、贫民窟的名称、贫民窟首领的标志,和所有巴西人一样,毒贩也喜欢公开自己在球队上的喜好,所以还印上了弗拉门戈球队的徽章。标签上最显眼的位置则留给了一位桑巴女郎,她的身旁用彩色的字母印着:“狂欢节”。在标签的底部竟然还有一行字:“如有质量问题,请到购买处申诉。”
书中,刘骁骞写道:“这就如同干了坏事还特意留下家庭住址一样,完全是对警方的挑衅和蔑视。”但毒贩们并不这样考虑,在他们看来,毒品生意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行业,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持有枪支也是因为防备周围其他的武装团伙,“要保卫家园”。

贩毒集团的“士兵”

“保卫”贫民窟
既然毒品行业也存在竞争市场,所以就要像奢侈品广告一样,他们会按季推出不同的标签。每逢母亲节,他们会在标签上印上一位慈祥母亲的画像,画像原型据说来自其中一名毒贩的母亲。而在巴西世界杯期间,他们就印上了世界杯会徽和吉祥物……
“好好拍,只有这个机会了”
采访到了毒品加工点,刘骁骞还是不甘心。第二天,他们再次驱车返回贫民窟,要拍摄传说中的“烟口”,在贫民窟的黑话中,它专门指贩毒集团的毒品零售窝点。刘骁骞想拍摄一个大型的“烟口”,贩毒集团“值班经理”同意带他们去看看,但要乘车往更深处走。
线人突然说他不去了,就在原地等着。“好好拍,只有这个机会了。”线人低声对刘骁骞说。刘骁骞把车门拉上,没有作声。就这样,他们跟随着素昧平生的毒贩向贫民窟的深处驶去,“在世界上任何一本《采访指南》里,这或许都是最不被推崇的决定:我们不知道会被带去哪里,也许会被绑架,或者遭到警方或者敌对帮派的突袭。然而事实是,如果逐条考虑和评估,我也许连第一步都无法迈开。”
那里的粉果然比外头来得齐全,除了5雷亚尔一包的基本款外,还有各种不同剂量和纯度的包装。单价最高的可卡因装在一种半截拇指大小的透明塑料罐里,粉末略微偏黄——判断可卡因纯度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颜色,颜色越白,纯度反而越低,因为掺杂进大量的杂质和化学替代品。站在中间的毒贩穿着一件褪色的短裤,一把手枪别在腰间,他一看见摄像机,不但没有躲闪,反而从桌上捞起一大把细长包装的可卡因递到镜头前。“看吧,要多少有多少”……

探访贩毒集团的毒品销售窝点
“只看到今天,不去想明天”
刘骁骞和毒贩“士兵”的谈话中,你也许能体会到这些“刀头舔血”者的心态。
问:你担心这里的维和警察所吗?
答:生意肯定会受影响,不能这么明着卖,我们要保卫贫民窟。
问:你害怕死亡吗?
答:如果我害怕就不会选择这种生活,只看到今天,不去想明天。
书上,刘骁骞写道,“然而我并不相信他的话,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不怕死的人,只不过我们都坚信自己是唯一的那个幸运儿。”

阿卡立贫民窟的警方行动
刘骁骞多次出入贫民窟,他跟随里约警方前往过毒贩的凶杀现场,在双方交火的后方拍摄介绍死者被枪决的情况;同时,在跟随里约精英部队拍摄清剿毒贩的过程中,刘骁骞一边跟着部队前进,一边还拿着话筒解说半小时前被击毙的毒贩。几米之外,毒贩的鲜血流淌到他脚下。“身临其境,你会发现电影《上帝之城》、《精英部队》并没有夸大警匪缠斗的残酷,只是把多个场景集中到了一起。”
“我讲述的巴西即是我经历的巴西”
刘骁骞说自己热爱巴西,不仅仅因为他在这个国家常驻了九年,还是因为巴西人民的热情。“那种热情是自然流露的,两个陌生人同乘一座电梯,瞬间就能开启亲密的聊天模式,在第三眼中,他俩就像多年的老友一样。”
但这样一个热情奔放的国度却有解不开的社会问题。毒品、黑枪、贫穷、谋杀。一份调查显示,2012年全巴西共有56000人死于凶杀,其中30000人为15岁至29岁的青年,而在这些遇害青年中,77%为黑人,这相当于平均每23分钟就有一个黑人青年死于凶杀。另一项由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里约市区共有1275人死于警察行动,其中 79%为黑人男性,75%为15岁至29岁的青年。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陆上行舟》书中,刘骁骞梳理巴西的历史和多个武装贩毒组织的发迹史,他发现,“从新大陆的殖民史、奴隶制,再到军人独裁时期以及后来历届巴西政府的举措,都无法摆脱它们盘根错节的责任。”
“你很难说起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因为我每说出一个结论的同时,我个人经历过的某件事就可以完全推翻我自己当下的结论。”因此,在《陆上行舟》的前言中,刘骁骞写道:“我想在这里坦白的是,在每一趟旅途中,我都濒临体能和心理的极限,穷尽所有的智慧。让我诧异的是,经验的累积似乎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每一个调查报道都犹如亚马孙河系大大小小的支流,地貌迥然,有各自的风光和险阻。我既希望旅途尽快结束,又期盼旅途尽早开始……我讲述的巴西即是我经历的巴西。”
图片提供/刘骁骞
统筹/满羿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