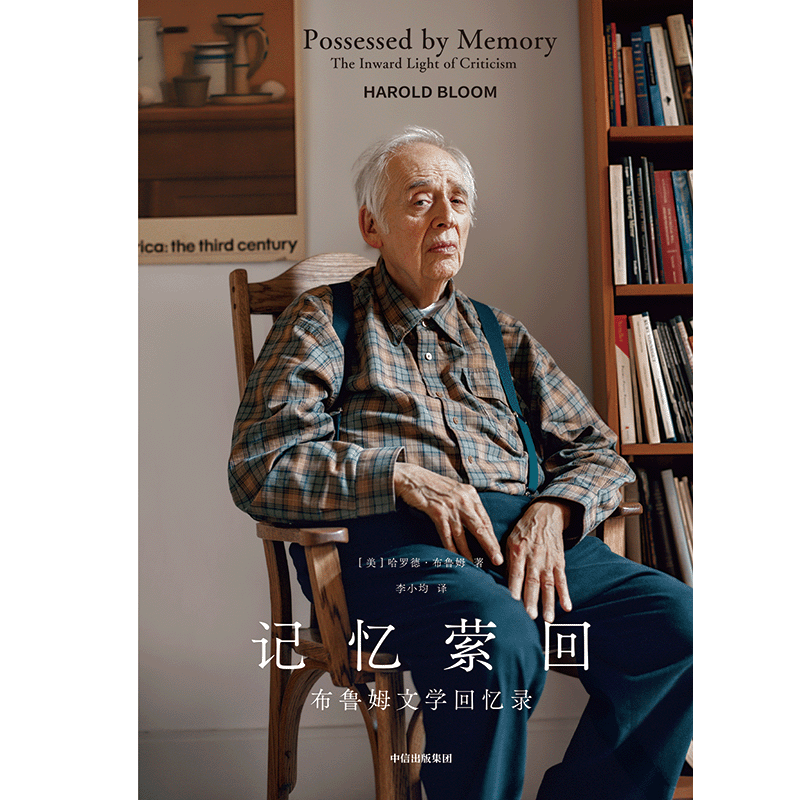多年前,我在英国剑桥参加了一个相当神秘的教师团体举办的一次会议,他们相信你可以与亡灵沟通。这是一次不安的经历,大家围着一张旋转的桌子,不时听到传来亡灵的声音。我相当冒失地匆匆离开,因为我感觉格格不入。早前,我迷人的导师乔治·威尔森·奈特极力劝我相信,降神会是真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驳说,我认为这是对人之欲望的过度解读。乔治哈哈一笑,说我还太年轻了,理解不了一个重要的真理。
诗人詹姆斯·梅里尔是我的熟人,他有时会调侃我的怀疑主义。与威廉·巴特勒·叶芝一样,他也召唤亡灵,为他诗歌提供隐喻。无论亡灵是否帮助了他们的想象,反正从他们留下的诗作的结果来看,是令人惊奇的。
现在,我自己的关切完全不同。当我读到我亡友的作品,我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他们还在这间屋子里。我也接触过许多普通读者,他们会激动地说起,每当阅读或重读他们深爱的逝者高度推崇的一本书时,会感到一分慰藉。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当我们经历悲伤时,可以得知这悲伤的尽头。但我们是世俗中人,所以也就别指望。我写本书的目的,不是想哀悼我这一代批评家和诗人。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是想向他们在作品中的来生致意。前天晚上,我瞥了一眼我的写字台,看见许多亡友的作品,诸如约翰·阿什贝利、A. R. 阿蒙斯、马克·斯特兰德、埃尔文·费曼(Alvin Feinman)的诗歌,理查德·罗蒂、杰弗里·哈特曼、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er)的批评。我和他们所有人的私交至少有半个世纪,与其中大多数甚至长达六十年。
本书付梓时,我将要八十九岁了。这本书写了好几年,我开始把我持续的写作理解为与我亡友的对话。有时是我的导师,如M. H. 艾布拉姆斯、弗雷德里克·波特尔(Frederick Pottle)、格肖姆·肖勒姆、汉斯·约纳斯、肯尼斯·伯克;有时是我的老友,如弗兰克·克默德、安东尼·伯吉斯、A. D. 纳塔尔(A. D. Nuttall)、诺斯洛普·弗莱。
本书的性质属于沉思而不是争论。我用了一个动词短语做书名。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possessed by memory”(记忆萦回) ?记住逝去或失落的朋友和爱人,与记住情感强烈的诗文,这两者有何区别?英语动词“possess”的语义很丰富,它可以表示“占有财物”“施加影响”“掌握知识”“恶魔附体”“沉着镇静”“享受性爱”“篡夺劫掠”等。
“poti-”这个印欧词根暗含了“主宰”或“影响”之意。“possession”一词源于潜力,是一种预知某些事即将发生的感觉。其中有一种逐渐点燃的努力、期待和渴望,然后是欲望的退潮,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欲望死了”。康德定义的形而上学有三个理念:自由、上帝、不朽。这三个理念在诗歌中转变成了对应的三个理念:个体化的声音、降神或巩固一个逐渐衰败的神、赋予我们更多生命的神恩。记忆就包含在诗歌的这三个复合理念之中。
在一首诗歌中,声音的意象总是一种喻说,倾听在你的世界创造出来之前你可能听到的声音。神恩经常以你之名与一个改变同时发生。当你对一首诗了然于心,你就更真切、更奇妙地占有了它,甚至比你占有一处居所更真切、更奇妙,因为这首诗歌也占有了你。降神可能是一个神秘的过程,但诗歌会在其最强烈的时刻敲击诗琴,然后神就变成了琴弦的问题。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