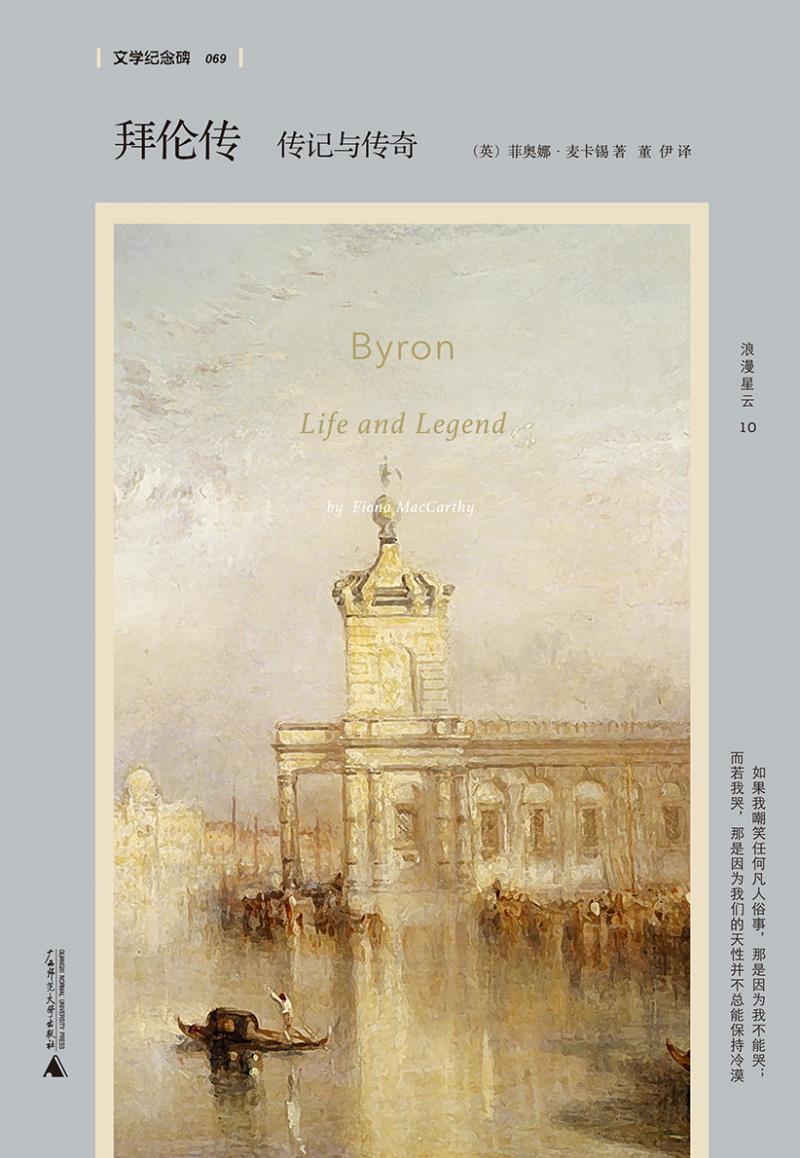《拜伦传:传记与传奇》(英)菲奥娜·麦卡锡 著;董伊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文学纪念碑
假如你回到一八一六年的欧洲,你可能会碰巧遇到拜伦的车队:黑色马车庄严肃穆,从布鲁塞尔出发,途经日内瓦,向着意大利的方向徐徐驶去。乘着这辆车,拜伦将自己流放。四十余年前,拿破仑大帝曾有一辆著名的座驾在热纳普被英军截获。拜伦的马车仿自这辆座驾,但改造得比后者还要奢华: 车上有床、书柜、橱柜和各种炊具,需要四至六匹马牵引,可谓是装上轮子的宫殿。整车造价五百英镑,由马车制造商巴克斯特设计建造。一八二三年,可怜的制造商还在催促付款,拜伦却轻描淡写地回道:“巴克斯特要再等一等。至少再等一年。”据推测,当拜伦于一八二四年四月在希腊去世时,这笔账仍没有付上。
拿破仑长长的影子笼罩着拜伦的一生,鼓舞他,刺激他。拜伦出生于一七八八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而夸张的时代,这让高格和马戈的一切都显得渺小。”拿破仑比他大近二十岁,他的幽魂激发了拜伦的野心、异见、傲慢和随之而来的魅力,以及弥漫在他作品中的纵横交错的历史感。拿破仑的华丽,他的耐力,他的衣着,他的姿态,他用来修饰自己形象的勤奋的样子,滋养了拜伦一边嘲讽、一边创新的思维习惯。正如他对布莱辛顿夫人所说的:“拿破仑说得对,我离崇高和荒谬都只有一步之遥。”
比起情人,拜伦与拿破仑的关系要近得多。他对拿破仑吹毛求疵,眼尖的布莱辛顿夫人说,只有“情人之间才会如此挑剔”。他对拿破仑是真动了感情。一八〇三年当拿破仑已成为英格兰的国家公敌的时候,这位义愤填膺的小学生却在为他的拿破仑半身像辩护,大骂那些“无耻的守旧派”。几年后,他对摩根创作的拿破仑肖像越看越爱,干脆请匠人为画包上了镀金的边框。他个人对皇帝的认同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拿破仑的失败引起了他的具身反应。在一八一三年莱比锡之行之后,拜伦绝望得四肢乏力,消化不良,并在日记中呻吟:“哦,我的头!好疼!消化不良真恐怖!我想知道波拿巴是如何一口口地咽下饭菜的?”
第二年,在拿破仑退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拜伦记录道:“今天我打了一个小时的拳击。为拿破仑·波拿巴写了一首颂歌,抄了一遍,吃了六块饼干,喝了四瓶苏打水。把剩下的时间都消磨掉了。”这首颂歌悲愤交加,拜伦不允许英雄人物卑躬屈膝,觉得他理应像战败的罗马人一样死在自己剑下,或者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或“理查三世”那样毅然死在叛军刀下。尽管他的幻想破灭,但拿破仑的光辉仍然令他折服。对于拜伦来说,拿破仑是他的第二天性,是他思想活动的一部分,深深地镌刻在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拿破仑去世后,拜伦收藏了一些纪念品: 一缕头发,印着拿破仑的鼻烟盒,印着拿破仑的金币。还有一枚印着拿破仑的胸针,拜伦在热那亚送给了布莱辛顿夫人,他用一个潇洒的手势将它从胸前取下,但第二天还是要了回去。他说“带针的纪念物”不吉利,这个借口颇为可疑。在一八一六年离开英国之前,也就是分居丑闻发生的时候,拜伦预订了拿破仑加冕时的一套礼服,一直保存在皮卡迪利的一个经销商手中,但其实拜伦从未去取。虽说如此,启航前不久,他确实用从马尔迈森的帝国局抢来的盖有拿破仑之鹰的信纸给美塞·艾尔芬斯顿写了一封深情的告别信: 他附上了几张备用信纸作为临别礼物。当他的岳母诺埃尔夫人去世后,拜伦终于可以把NB作为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诺埃尔·拜伦,同时也是拿破仑全名的首字母缩写。,他欣喜若狂地告诉利·亨特:“波拿巴和我是唯一的名字缩写相同的公众人物。”要知道,记录这一幕的亨特为拜伦立传时没少说他的坏话。
从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二三年,拜伦在意大利流浪,脑海中充满了对拿破仑的怀念。他注意到,在米兰附近,原本为拿破仑设计的圆顶拱门遗骸“美到让人后悔它没有完工”;在伊索拉·贝拉岛,他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月桂树,在马伦戈战役前不久,拿破仑曾在这棵树上刻下了“不胜不归”的字样。拜伦本人不喜欢在树上刻画,他仔细检查了这几个字母,发现字样已“近乎磨损殆尽,像是有人故意将其擦去”。
在意大利,拜伦眼里的拿破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维苏威火山,在最终被推翻的那一刹那,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后,政治侏儒遍布欧洲大地:“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傻瓜的奴隶。”毫无疑问,他看到了涉足欧洲政治的自己——先是作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一名游击队员,然后是希腊独立战争的吹号手。但就算是把自己与拿破仑联系到一起,他也不忘自嘲一番。
一八二三年,他形容自己为希腊军舰中队提供的二十万毕阿士特的资助“规模不是很大,但比皇帝拿破仑进攻意大利时的金额多了一倍”。他喜欢并熟谙军队的装束:头盔,制服,隆重的敬礼仪式和阅兵式。在拜伦精心安排的迈索隆吉翁入城式中,可以看出一种对拿破仑的致敬。当时围观的人中有一位叫作西奥多罗斯·弗里扎基斯的画家将这一幕刻画得像神话或史诗一样,拜伦在画上被塑造成一位军事英雄、民族救星。这幅画现收藏于希腊国家美术馆。拜伦的拿破仑主义,以及他积极参与同时代政治事件的态度,都是他与其他英国浪漫派诗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早在拜伦去世之前,他和拿破仑皇帝就成了英国报纸嘲笑的对象。拜伦在一八二一年写给他的出版商约翰·默里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现象:“我认为‘人类虚荣心在当代有两个最伟大的例子’,首先是‘前皇帝拿破仑’,其次是‘尊贵的诗人阁下’——意思是您卑微的仆人——即‘可怜的无辜的我’。可怜的拿破仑!他怎么也想不到,历史的车轮会拿他与‘如此卑微的人’作比。”言语间明显有一丝自鸣得意。从今天的视角看,他们之间有更多的联系。麦考利在一八三一年写道,二人都年轻有为: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已经有两个人去世了,他们在一生中完成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把自己提升到了巅峰。其中一个死在朗伍德,另一个死在迈索隆吉翁。
两年后,卡莱尔在《衣裳哲学》的一篇文章中将他们放在了一起,认为二者的生平都极具戏剧性,这可谓一语中的:
你笔下的拜伦发表了《乔治勋爵之伤》,有诗歌、散文等文类,内容丰富。你笔下的波拿巴发表了歌剧《拿破仑之伤》,气势恢宏壮阔,剧中可以听到火炮的轰鸣和杀戮的惨叫;舞台灯光是熊熊的火焰;节奏是守城士兵列阵的步伐,宣叙调取自沦陷城池的哀鸣。
在集体想象中,二人坚定不移地并肩站立: 身材健硕的拿破仑和英俊绝伦的拜伦是那个时代极为奇特的一对形象。年迈的花花公子乔治·“花花公子”·布鲁梅尔在加莱度过了他流浪的日子,他正在为约克公爵夫人制作一幅装饰性的屏风,这是一幅由版画和素描拼贴而成的作品。屏风的第六扇也是最后一扇再现了拿破仑和拜伦,布鲁梅尔对后者记忆犹新,怀念他在伦敦的宁静日子。拜伦的身影镶嵌在鲜花中,但喉咙处却卡着一只黄蜂。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位默默无闻、穷困潦倒的英国贵族是如何将自己提升到与拿破仑平起平坐的历史地位的呢?这位早期“三句一叹”的情诗写手是如何让自己转变为欧洲言辞之王的呢?这个来自南井镇的“胖乎乎羞答答的男孩”,这个“留直刘海”,即使在英格兰郊区也是招人怜爱的对象,其挑逗性的“俯视”会让最老练的上流女士心悸的男人,究竟是如何牵动各国民众的心弦的呢?“这幅美丽苍白的脸就是孽缘的开始”:卡罗琳·兰姆夫人在与拜伦勋爵会面后在日记中写下这句话剧腔十足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痴恋他的女人的心声。
拜伦是欧洲第一位现代文化名人。一八一二年三月,第一部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章一经发表,就在伦敦大获好评,拜伦一夜成名,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觉醒来,我竟然出名了!”当然,事情并非像他说的这样简单。这本传记花去了我五年时间,为此我前往威尼斯、罗马、拉文纳、比萨、热那亚、雅典和迈索隆吉翁,以及他度过童年的城市阿伯丁,我要去看看是什么原因在背后驱动着他,这件事情十分有趣。在布莱辛顿夫人看来,当她在一八二三年第一次见到拜伦时,“拜伦渴望成名,为此他无所不用其极:这经常导致他表达的观点与他的行为和真实情感完全相左。有时候,他甚至不惜脏了羽毛,沽名钓誉,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本书与拜伦出名的前前后后有关——他那“最叫人兴奋”的野心;他对自己人设的维护和管理,对肖像的细节和副版的把控;他在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名声之间搭的那座桥;声名狼藉后他和家人、随从吃的苦、遭的难。拜伦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但他的影响留存了下来,且在许多方面方兴未艾。因此,本书不仅讲述他的一生,还讲述他身后的名声。
拜伦的成名当然离不开他的出版商约翰·默里二世,是他们家族的后代约翰·默里七世委托我撰写了这本新传记。我很享受这种延续。我追随拜伦一生的足迹,皮卡迪利的阿尔贝马尔街50号是这一程的起点和终点,这座官邸是约翰·默里二世用畅销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赚来的钱买下来的,现在仍然庄严肃穆。同代人戏谑道: 购置了这座宅邸,曾经的书商摇身一变成了绅士。诚然,约翰·默里的文学圈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迅速上升与一夜成名的拜伦不无关系。
被拜伦迷到癫狂的卡罗琳·兰姆夫人对约翰·默里说:“你的房间里每一处都有他的身影。”拜伦的回响依然存在。在阿尔贝马尔街50号的客厅里,我坐在菲利普斯为拜伦画的肖像下面,研究世界上最大的拜伦档案,这笔财富让我两眼放光。默里家族与拜伦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利和他的朋友兼遗嘱执行人约翰·卡姆·霍布豪斯(后来的布劳顿勋爵)交情很深,档案馆里不仅有手稿和信件,还有肖像、模型、衣服、奖章、纪念品,以及各种阶层女性写的求爱信,其中许多拜伦不认识。这些女人写的话要死要活,有些要地址,有些求见面。此外,还有一堆阴森森的头发,都是各种女人送的,每个人的头发都包得整整齐齐,成熟后的拜伦分别做了标记,看来他也是个惜物的人。还有一只小拖鞋,有说是拜伦和克莱尔·克莱蒙特生的女儿艾蕾歌的,她五岁时死在巴格纳卡瓦洛镇的一家修道院里。这样的小物件可以带来一种既视感,把我带到了特定的时刻、场景、人群中。可以说,默里档案馆的资源像一处宝藏,等待像我这样的传记作者仔细辨察,找回过去。
约翰·默里出版的最后一本拜伦传记是莱斯利·马钱德开创性的三卷本传记,出版于一九五七年,是后来所有拜伦学者的起点。从那时起,出现了大量新的材料,例如,拜伦与权势强大、“徐娘半老的牛津夫人”(她只有四十岁)的亲密关系;他与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灾难般的婚姻;他与特蕾莎·圭乔利伯爵夫人最后一次在意大利的同居。一九七六年,在巴克莱银行的一个保险库里,人们偶然发现了拜伦的朋友斯克罗普·戴维斯一八二〇年一月匆忙离开伦敦以躲避债权人时遗弃的手稿和信件箱,这些新的传记素材让我们重新认识拜伦与男性朋友的关系。学者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前人忽视的那部分拜伦的生活,比如服侍拜伦的那些纪律松散但忠于职守的仆人;他饲养的那些咆哮、尖叫、抓人的动物;他家庭富裕与贫穷时的经济情况;他的跛脚、厌食症和抑郁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传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马钱德在立传的时候,同性恋行为仍然违反英国法律,因此在写到拜伦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的乱伦关系以及他对少男的偏好时,马钱德不得不收笔。他回忆起一九九五年时任出版社负责人的约翰·默里爵士的规定:“不允许从这些事件和证据中得出任何直接明了的断言。”在他写较短的传记《拜伦肖像》(1971)时,管控放宽了,此时约翰·默里爵士已去世,英国修改了有关同性恋的法律。但马钱德自己心里明白,他在这方面介绍得不足,当然,这不是他的错。
今天,不会有人再质疑性是人乃至时代、地方传记中的重要部分,我始终没有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拜伦是双性恋,这在他自己的密友圈子里是公开的秘密,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他的生活模式。多丽丝·兰利·摩尔在其著作《众人眼中的拜伦勋爵》里的一篇文章中坚称,拜伦与女性的恋情是他情感的主要对象,他与男孩的关系不过是消遣而已。我相信事实恰恰相反。拜伦喜欢追逐女人,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征服的满足感。但总体而言,拜伦对女性的喜好无法长久。拜伦自己半开玩笑地给了她们三个月的时限——这个时间段相当准确,例外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和他末年的意大利情妇特蕾莎·圭乔利,虽然后者风情万种,但拜伦对她的感觉最终还是变淡了。
拜伦招女人喜欢,但这种喜欢很容易转化成从内到外的反感。他不喜欢看到女人吃饭,这成了他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极具喜感。相比之下,即使双方长时间不见面,拜伦对男性的爱情似乎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汹涌澎湃。他的性幻想最终落到了理想化的男孩形象上。且去品一品他末年见到衰老的哈罗公学时的最爱克莱尔勋爵时的一怀愁绪,以及他在希腊最后几个月里对随从卢卡斯·查兰德里萨诺斯单相思时的惆怅吧。
在公开场合,他小心翼翼地从著述中剔除那些他自己认为在接下来的三百年内不应该被披露的东西。他开玩笑说,在撰写准备发表的日记的时候,要是“泄露一些秘密或其他东西,子孙后代将永不能翻身”。但私下里,比如给他的密友写信时,他对待自己双重情感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那一半”则更为坦率。
拜伦天生就喜欢男孩,知道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解开很多有关他的谜团。他私下承认玩过鸡奸,这在当时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罪行,也是他一八一六年的流亡的唯一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是因为,围绕拜伦与妻子分居的传言最初只集中在乱伦上,后来便扩大到了对他的鸡奸的指控。
长期掩饰他的性取向,导致他的写作风格凌乱,少有章法可言。在他的文笔中看不到贵为勋爵的他。拜伦在现实中“生活在夹缝中”,导致他的文字闪烁其词。这种各方面的不安全感让他沦落到了社会的边缘,这反而方便了他直抒胸臆。他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 英国贵族和欧洲流浪汉;失去了土地的地主;上议院心怀不满的演说家;放弃了英格兰,自认为是无国籍的游民,穿着拉德克利夫夫人的斗篷在威尼斯这儿住两天;那儿住两天,盘算着去南美种地,虽说这是对新生活的向往,但不切实际。在“国际主义者”这个词出现之前,拜伦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正是他自相矛盾的天性、游离不定的思绪、作品中的多声部,将他与今天种种错乱的生活观念联系在一起。
我在这本书里故意塞满了引语。十九世纪初是一个文学繁盛、笔酣墨饱的时期。拜伦的名声成于社会的赞扬和鼓励,毁于同代各阶层的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在嘈杂的社会舆论中,拜伦有女性的自信和男性的脾气,他会用简洁的文风自嘲,这在那个时代不可多得。有人指控他从修道院抢走一个女孩,他则自嘲道:
到底是谁被抢走了?不就是我嘛,真可怜。在特洛伊战争以后,还有谁像我这样受众人抢夺?
就是这样的言语让拜伦成了英国上层文风的鼻祖,这种文风的继承者包括奥斯卡·王尔德、罗纳德·菲尔班克、诺埃尔·科沃德。
在重估拜伦勋爵的过程中,我有幸接触到了默里档案馆的新材料。这是约翰·默里与拜伦完整的通信,最近由著名拜伦学者安德鲁·尼科尔森誊抄了下来。此前,这里只提供零星的材料。翻阅一八一一至一八二二年底的通信,我发现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保守的默里指责拜伦的诗歌写得越来越出格,认为作品引发的争议会损害出版社的声誉。约翰·默里出版了《唐璜》的前五章,这首诗通常被认为是拜伦的杰作,但随后的诗章和拜伦的大部分后期作品都是由约翰·亨特出版的。
对于拜伦本人来说,与默里断绝关系是一个原则问题,这彰显了他对自由的热爱,亮出了他敢于抵抗到底的立场,抵抗着我们现在称为“思想警察”的东西:“世上所有的恶霸都不应阻止我写我喜欢的东西,出版我写的东西,为此我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可以将拜伦对言论自由的主张等同于他支持希腊独立的英雄主义行为。但对于约翰·默里来说,对作者的投资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商业领域,更多是出于多年的交情,因此,失去拜伦对他而言相当于一场人生悲剧。
拜伦在今天还重要吗?经历了相当于五年的朝圣之旅之后,我相信他仍然重要。他的诗歌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他的思维粗糙草率。歌德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认为拜伦作为一个思想家几乎是一个孩子的水平。但即使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发声者,一位情感的传递者。他有一种同理心,一种穿越几个世纪的、几代人的同情心。他一八一六年写于日内瓦的灾难诗《黑暗》像一场噩梦,以晦黯的笔触预示了今天荒芜、血腥的世界。拜伦虽然英年早逝,但比其他活到老的人要重要,这位饱经风霜的人看到了世界最糟糕的一面,在革命暴力的时代过着光怪陆离、荒淫无度的生活。但他拒绝失败。他总有一句话保底:“给我一叶希望之舟。”
在写这本传记的这几年里,我的一位密友因癌症而去世了。他们邀请我在葬礼上朗诵一段文字,她的丈夫最希望我诵读的那一句是:“就这样吧,我们别四处流浪。”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诗,还是在诺特列伯兰山坡上的一座灰色的小教堂里,那是一个初夏。拜伦道出了我们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