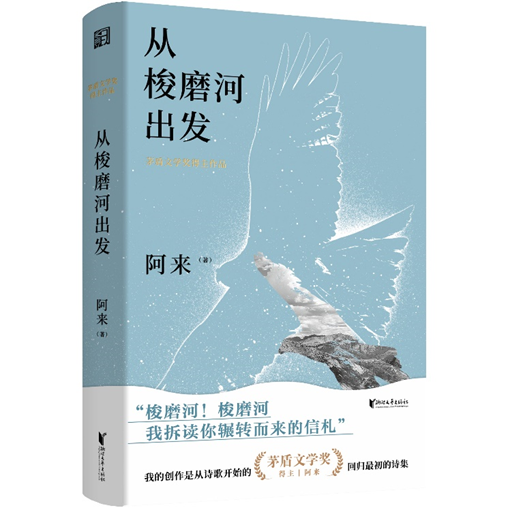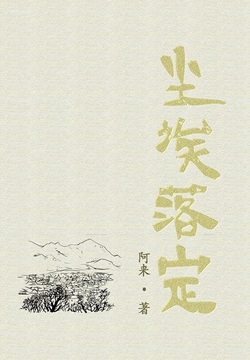“‘告诉我爱是什么?’‘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这是一句傻话,但聪明的父亲听懂了,他笑了,说:‘你这个傻瓜,是泡泡都会消散。’‘它们不断冒出来。’”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发表已二十余年,除了获“茅盾文学奖”,小说中对爱情感觉的描述二十多年来在读者的头脑中萦绕不去,接受新民晚报专访的阿来笑言:“爱情就像泡泡,让人变得轻盈。人永远会有那种感觉。”
阿来给新民晚报的题词 受访者供图
用小说,面对复杂
这次上海书展,浙江文艺出版社带来的《从梭磨河出发》是阿来的诗集,也是目前收录阿来诗歌最全的一本诗集。但,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诗的阿来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诗歌散落在图书馆的杂志里,也未可知”。
如今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的阿来小时候没想到自己会当作家靠文字吃饭,他闯入文学境地是无意的。年轻时他是乡村中学教师,志趣在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身边有一帮同龄的年轻教师,学数学的、学化学的、学地理的、学英文的,独独没有学中文的,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在写作,只有阿来陷在故纸堆里。一到星期六,朋友们每人出几毛钱到小县城小镇的饭馆里吃一顿,喝着廉价的酒,吃点便宜的菜,朋友都会把习作小说、诗歌拿出来,借着酒兴朗诵,然后问:“看我写得怎么样,请大家评判?”而阿来在读古典文学,标高就是李白杜甫苏轼,经常“口出狂言”说:“你们写得不好。”于是大家打赌阿来能不能按我们的方法,按自由诗的方法也写两首。
年轻好胜的阿来,晚上就回去“把日记改写了”两首《振响你心灵的翅膀》和《母亲,闪光的雕像》。第二次喝酒时拿出去,得到一致肯定“确实比我们写得好,我们帮你投稿”。阿来不知道什么叫作投稿,不知道投稿要掌握很多报纸和杂志的地址,而朋友们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早就驾轻就熟。过了一个多月,终于有个“录取通知书”到了,是给阿来的。从此,这颗年轻人的虚荣心得到鼓励,就开始写诗,那一年,阿来23岁。
《从梭磨河出发》一书中收录了一首名为《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的诗,阿来不断提起,因为它标志着自己在艺术上的成熟,“是我写在香烟盒子上的,我走到一个地方所有的感应”。写完这首诗后,阿来决定不写诗了,他说:“写诗歌要保持抒情言志的传统,当我明白诗是什么也就明白了文学的道理是什么。我觉得我要找一种更复杂、更能面对当下世界的方法。既然我要从事文学,我就要做一件大一点的事,光靠分行的诗歌完不成我想做的事。我更愿意把诗当作一种宽泛的文学方式。”
1994年,阿来在新买的286电脑上,落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
用读书,印证现实
波斯诗人萨迪曾说过:“一个人应该活到九十岁,用三十年获取知识,再用三十年漫游天下,最后三十年从事创作。”阿来遵循着这番话前行,只是,漫游、获取知识、从事创作,三者交替往复。
“我的学校教育在1980年已经结束。”阿来说,接下来的知识储备都来自自学,他这一代的作家,自学能力非常之强,“我植物学的段位很高,研究了植物学,就带出了地理学,为了搞清楚植物的来龙去脉连带学了气象学。”
自学的途径就是读书。阿来的家堆满了书,书像藤蔓一般从书房中长出来,长到床上、洗手间,盘踞了半张餐桌,出差、讲学他经常随身携带着研究书籍。采访的房间里,打开的电脑上铺满了植物的照片。
“我一边读书,一边到现场印证”,抵达地理上的远方,也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在上海的早晨,他沿着淮海路向东行走,经过国泰电影院,思及建筑背后的历史,满街的树影他用植物学的眼光来看就是“这些树的学名叫悬铃木,家乡在欧洲,把它们称作法国梧桐是中国人巨大的误会”。“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阿来背起了李贺的诗来印证古已有之的梧桐来历。
阿来 新民晚报记者 王凯 摄
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可以说是阿来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他对中国叙事文学传统感觉复杂。叙事文学中“暗黑”的生命观与人际关系,动不动就杀人,人与人之间诡计多端,一切向下走,让他产生本能的距离感。藏族相信“万物有灵”,一草一木能寄魂,对生命本身更敬畏有加。他只为内心写作,始终独立在流行的文学潮流和创作方式之外。别人抛弃了故事,他却成为故事高手;同时代的作家转向了故事,他又重回抒情传统。“我拥有一个巨大的写作领域,这里没人书写,在这个领域中我就是王。我把文学当作终身事业,我基本按照自己的心愿达成了目标,这就是世界对我最大的奖赏。”
64岁的阿来最爱的运动是行走,“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谁知道会遇见什么呢?
文/新民晚报记者 徐翌晟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