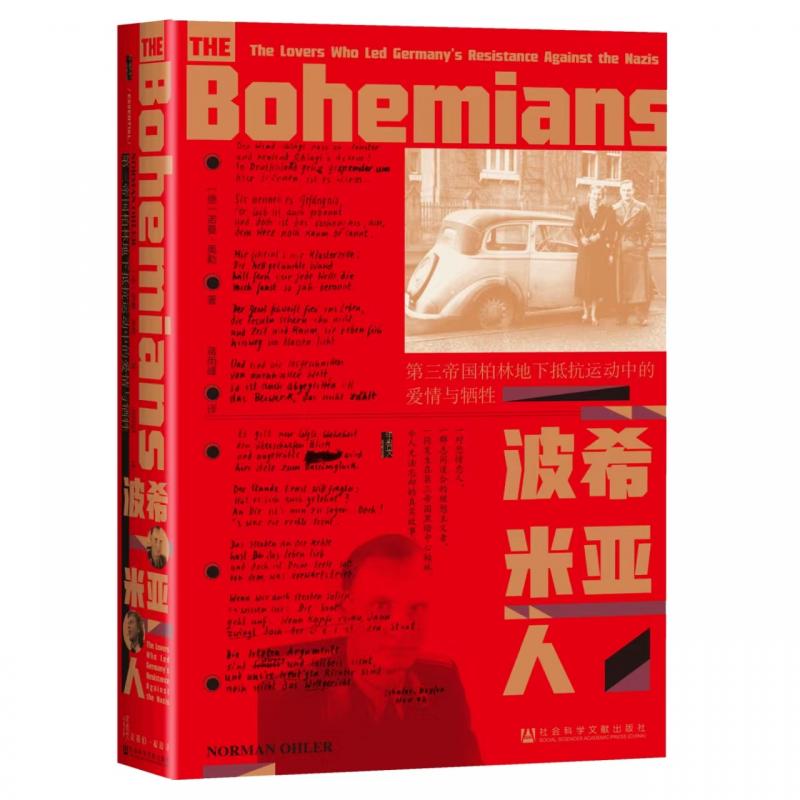大约12岁那年,我坐在祖父母家的花园里。祖父母家在克林格尔谷(Klingeltal)中,位于德国西南部一座小城郊区,靠近法国阿尔萨斯(Elsass)地区的边界。1945年3月,这座我出生的城市在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次空袭中被夷为平地,95%以上的巴洛克式建筑被毁。像许多人一样,祖父母的财产在轰炸之后荡然无存。于是,我的祖父在战后用“自己的双手从废墟中”建了一座新房子。他把它命名为“晨光之屋”(Haus Morgensonne),并把那条穿过克林格尔谷、通往房子的田间小路称为“草场地”(Wiesengrund),后来官方的地图里也是这样命名的。
我们常在“晨光之屋”的花园里玩“不要生气”游戏。每回第一次掷骰子之前,祖父总是会说:“比赛会很激烈,但也会很公平!”这句话总让我有一些害怕,尽管公平竞争无可指摘,并且我们也不会把所谓的“激烈”太当回事,毕竟玩这个游戏基本上是为了获得乐趣和消磨时间。然而那天下午我也不管是否公平,一定要让祖父给我讲一个战争的故事,否则就不开始这一轮游戏。上午我们在文理中学看了一部关于解放集中营的纪录片,片里有堆积成山的眼镜、憔悴的面孔,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国民众欢呼的画面插入其间。观看期间我们所有人都不准离开教室。
我想知道这事与我的祖父是否有关系。起初他摇了摇头,打算开始玩“不要生气”。但我把两个象牙色的骰子都拿起来攥在手里,并且迫切地望着他。阳光透过苹果树的树叶洒在我们桌上,用光与影在黄底的棋盘上勾勒出一幅迷彩图案。然后祖父告诉我,他曾为德意志国铁路(Reichsbahn)工作。然而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新闻,我催促着他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情。
祖父盯着构成了“草场地”边界的那排蓝冷杉,陷入了沉思。随后他咳嗽了几声。终于慢慢地,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他一直是一个真正的、热情的铁路工作者,因为他喜欢铁路带来的可靠性和精确性。然而,他永远无法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立即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祖父迟疑地告诉我,他曾经当过工程师——他问我知不知道工程师是什么?尽管并不十分清楚,我还是点了点头。祖父说,在战争期间,他曾被调到波希米亚北部的布吕克斯(Brüx),那是一个位于奥西格—科莫陶线(Aussig-Komotau)、比尔森—普利森线(Pilsen-Priesen)和布拉格—杜克斯线(Prag-Dux)三条铁路线交会的偏僻城镇。
一个冬日的夜晚,厚厚的落雪覆盖了铁路黑色的双轨,还有草地、树木与结冰的奥赫热河(Eger),祖父用迟疑的声音告诉我,一列进站的列车被调度到一条旁轨上,那是一列载着牲畜车厢的长货车,它必须为紧急弹药运输让道。车轮在道岔上发出尖啸,人们的喊声回荡着,一声拉长的汽笛响起,牲畜车厢被脱钩解下。白色的山谷复归静谧。
凭着铁路人的直觉,我的祖父察觉到有些不对劲。片刻之后他离开了办公的平房,走向了那条旁轨。他只听到奥赫热河冰封的河面下低沉的水流声。他不安地沿着长长的一列车厢走动着。正当他打算再次转身离开时,有东西从车厢拉门上半部分一个狭窄的通风口里掉了出来。一个系着绳子的锡杯从通风口被放下来,碰撞着木制车厢壁发出声响,一度缠在了门把手上,然后又松开了。它缓慢地摇摆着下降,最后杯子落入铁轨旁的积雪里。很快绳子收紧,装满雪的容器又被收回去。拉门上露出一只手,接住了杯子,而能穿过通风口的只有孩子的小手。
车上的不是牲畜,是人!把人装在牲畜车厢里是违反运输条例的!真是糟透了,德意志国铁路是不会这么做的。祖父气愤地回到办公室,查询到这列火车本来要去的目的地:特莱辛施塔特(Theresienstadt)。这个地名没有包含多少信息:一个在受保护国边境线上的终点站包朔维茨(Baushowitz)以北几公里的小地方。他又跑到外面,想去仔细看看车厢,但此时有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哨兵沿着铁轨快步走来,手里端着冲锋枪。是党卫队。祖父转过身匆匆往回走,身后传来一声带有威胁的暴喝。
这就是战争,他想着。过了一会儿,他透过因为太热而蒙上水汽的办公室窗户向外看。战争中没有人会管运输条例。那些估计是战俘,俄国人。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火车是从西边开过来的。那只手属于一个孩子。他也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我怕党卫队。”
在他漆成黄色的房子后面阳光明媚的花园里,祖父向我讲述了这一切。虽然我爱他,他是我祖父,我总叫他“爷”(Pa),但那一刻我恨他,他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玩起了“不要生气”。
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玩到一半祖父的双手开始颤抖,为了避免直视我,他把目光瞥向一侧,用沙哑的嗓音说道:“那时我想,如果有人发现了我们对犹太人干的勾当,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我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我的祖父好像突然之间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虽然我可以用手触到他,但是我们之间有着极远的距离。刹那间一切都显得很遥远,我们身处的花园,我们小桌后面的那些苹果树,乃至桌子本身也像是在另一个维度里。我无法再摸到桌子,也无法移动我的棋子。在我左侧视野的边界,我的祖母像一座雕像一样坐在那里,变得模糊不清。我的祖父则坐在我面前的某处。我闭上了眼睛。一切都很安静,那是一种可以听见的沉寂。
1
柏林并不总是那样寒冷。在某些夏日里,城市酷热无比,勃兰登堡边区的沙子火辣辣地摩擦着脚趾。头顶的天空如此高远,以至于它的蔚蓝看起来属于太空。这样一来,在这座熙熙攘攘又无事发生的城市里,生活也有了无穷的意义。1942年8月里有这样的日子,一些人生命中最后一次泛舟于万湖(Wannsee);而75年后的8月里也有这样的日子,我遇见了一个名叫汉斯·科皮(Hans Coppi)的人。
汉斯说自己75岁了,看上去却要年轻些。他身材高大而瘦削(就像他外号叫“长人”的父亲),戴着圆框眼镜,眼神里含着警觉与讥讽。我不知道这次与汉斯的会面会导致什么结果。虽然我写过一部关于纳粹时代的纪实作品,但实际上我想写的是小说或拍一部故事片。这次汉斯·科皮告诉我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要写的还是一部纪实作品。
在冷战期间的东柏林,汉斯以一种尊贵的身份长大,因为他的父母在那里被追认为名人,他们是所谓的反法西斯抵抗战士。在纳粹的囚牢中,他的母亲得到允许将他生下,而后她受到审判,并且在8个月之后上了断头台。汉斯·科皮,一位取得博士学位、思维缜密的历史学家,终生都在试着理解他父母彼时的经历,以及他们和那几个1942年夏天最后一次泛舟的朋友为什么年纪尚轻就不得不赴死。
我原以为自己了解反对纳粹政府的抵抗战士中最重要的那些人:1944年7月20日带着炸弹的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chenk von Stauffenberg);格奥尔格·埃尔塞(Georg Elser),那个狂热的孤独斗士,1939年他自制的爆炸装置只差几分钟就能炸到阿道夫·希特勒;十分正直又格外叛逆的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以及她服用吗啡和“柏飞丁”的哥哥汉斯·朔尔 (Hans Scholl)。但根据汉斯·科皮的说法,还有一个故事也属于这类典范,这个故事围绕着他父亲的一对夫妻朋友展开:那两人曾与纳粹独裁抗争多年,于他们而言,这场战斗也始终是争取爱情中开放关系的抗争。他们的名字是哈罗·舒尔策-博伊森和利伯塔斯·舒尔策-博伊森(Harro und Libertas Schulze-Boysen),多年来有远超百人聚集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个光芒四射的社交圈,其中女性与男性人数几乎一样多。这在其他的团体中并不常见。这是一群青年人的故事,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活着——并彼此相爱,尽管他们在风华正茂之际就要面对死亡。
汉斯·科皮想要做的事情,即要找出当年的真相并不容易。当希特勒得知在帝国首都腹地的反抗运动后,他陷入狂怒,下令抹去所有关于这些非凡事迹的记忆,将之扭曲得面目全非。他要让关于哈罗和利伯塔斯,以及其他所有人的真相沉沦、消失。这个独裁者几乎得逞。
我在恩格尔贝肯(Engelbecken)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汉斯·科皮,那里是东西柏林的交界处,民主德国旧都的城市寓言和彼时围墙之中的西柏林旧城交相辉映。在这里,预制板建筑与奠基时代的士绅化住宅并排而立;在这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的一位门徒建造的圣米迦勒教堂(Sankt-Michael-Kirche)在一次轰炸后失去了屋顶却仍高耸入云;而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汉斯·科皮也怀疑地眯起眼睛望向天空,因为他知道积聚起来的暑热常在傍晚时分向这座美妙、有时又十分紧张的城市释放。
我的小儿子也来参加了这次会面,他刚过一岁半,却已有两岁孩子那么高。他觉得我们的谈话不如恩格尔贝肯池塘里的鸭子有趣。每当他走得太近,吓得鸭子从芦苇丛里的巢中跃进水里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拦住小步跑向岸边的儿子,把他按在椅子上,并拿一杯果汁给他喝。或许把他留在家里更好,这样我就能集中精力谈话。汉斯·科皮倒似乎不太受这些打断干扰。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们。
1942年9月,在哈罗被捕将近两周后,他的父母也被逮捕,而汉斯或许在他母亲希尔德·科皮(Hilde Coppi)的子宫里察觉到了这一点。她先是和其他妇女一起被送进了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上的警方监狱里,在10月底又被巴尔尼姆路的女子监狱收押,那时她已是孕晚期。11月底她得以在那里生下孩子,并且给他取名汉斯——这也是她丈夫的名字。
突然间我吓了一跳:我听到“当”的一声响,便望向了我儿子。他从面前装果汁的杯子上咬下了一块玻璃。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弄清楚状况。但杯子上的半月形缺口表明了唯一的可能。我小心地把手伸进他嘴里取出了那块形状完美的玻璃。还好小家伙没有伤到自己!我吃惊地看着他,而他也有些愕然地看着我。我原先不知道小孩子会咬玻璃,还能咬得这么整齐,他显然也不知道这一点。汉斯把脑袋歪向左边:“这孩子还真是精力旺盛。”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来参加这次会面,因为我突然希望未来儿子能像汉斯·科皮一样,通过思考历史来掌控人生。
那天下午的柏林很热。谈话结束后,我带儿子去了万湖游泳,因为那里有很多鸭子;此外,这片水域也与那些事迹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那是2017年8月31日,距离哈罗被捕的日子刚好75年整。起风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2
在柏林的米特区寻找线索。在昔日国家安全总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的所在地,如今有一座名为“恐怖地形图”(Topographie des Terrors)的纪念馆。这里曾是“盖世太保”的总部,海因里希·路易波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的办公室就在这儿,他每天上午在那里练两小时瑜伽,然后开始日常工作。奥托·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在这里策划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在这里,在建成监牢的混凝土地下室里,曾囚禁着哈罗,起初还有利伯塔斯,以及汉斯·科皮的父亲。像其他所有人的牢房一样,哈罗的2号囚室已不复存在。这座建筑在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次轰炸中被严重损毁,战后其废墟被拆除。20世纪70年代,一家拆迁公司曾在这里运营,在一个环形的试车场上,没有驾照的人也可以飞车驶过空旷的场地。而如今,在曾经的地牢区域办了一个展览,纪念的人物包括哈罗·舒尔策-博伊森。
我在展板前遇见了汉斯·科皮。他那天看起来很憔悴,问我的儿子过得如何,而后我们沿着昔日的提尔皮茨(Tirpitzufer),也就是如今的赖希皮特舒弗(Reichpietschufer)走到施陶芬贝格大街(Stauffenberg-Strae)上的本德勒街区(Bendlerblock)。“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Gedenksttte Deutscher Widerstand)坐落于此,毗邻国防部。在这座坚固的建筑四楼的一个房间里存放着“红色交响乐队的藏品”(Sammlung Rote Kapelle),其中许多是由汉斯·科皮和他的战友们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找到,或者从时代见证者和当事人亲属那里得来的,用以阐明哈罗与利伯塔斯,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故事。那间屋子里满是信件、相册、档案,还有谈话记录、对见证者的访谈、日记、审讯记录。
无论下文的一些事情听起来多么奇怪、戏剧性乃至不真实,它们都并非虚构。所有引号之中的引文都有来源印证。故事发生在柏林,一座历经诸多变迁的城市,这里一直生活着许多有相似生活需求的人:他们爱美食、爱电影也爱跳舞——他们组建家庭、抚养孩子或20只想彼此相爱。尽管有穿黑制服的人坐在邻座,他们仍会在咖啡馆里见面。那是在灰色和更多是棕色的包围之中逐渐增加的亮色。他们思考该如何应对难以为继的政治局面:在要求顺从的时代里该如何行事。他们和我那位继续为德意志国铁路局做工程师的祖父截然不同。
诺曼·奥勒
于当下的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