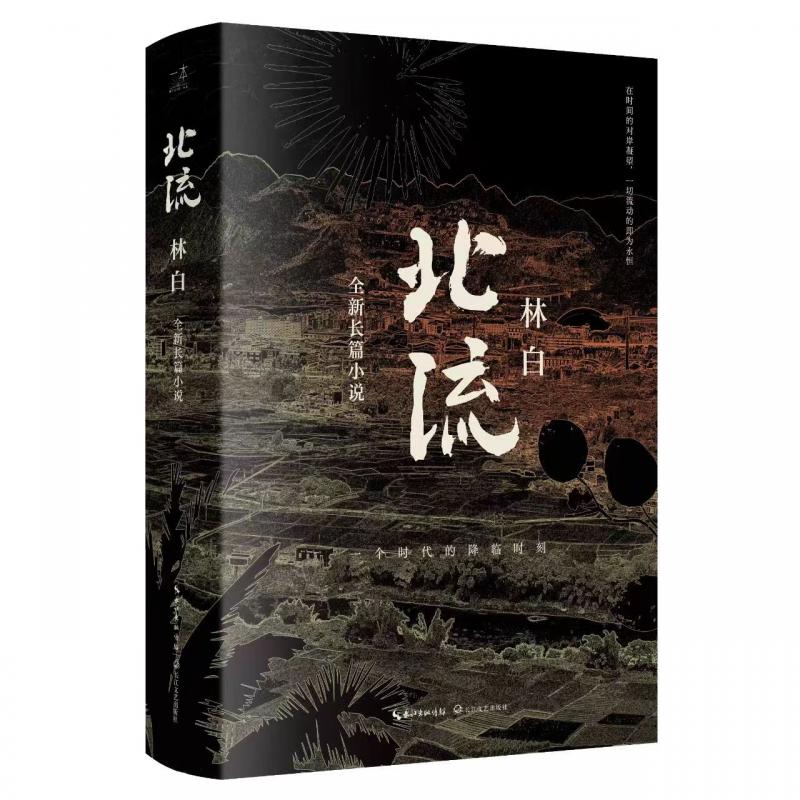有一些浩瀚复杂的书最好老老实实地读纸质书,比如林白的长篇巨著《北流》。最早我看的是电子版,我发现自己欠缺耐心,难以进入林白极其私人化的世界一隅。面对小小的电脑屏幕,我想先锋作家林白怎么如此私人事无巨细啰嗦没有逻辑完全任性的字纸篓一样东一记西一记地写自己一生的回忆录,是不是当一个人足够老了,把一生日记整理出来都可以?
后来调整自己的阅读心态,因为哪怕是电子文本,总有一些词要来抓住我,就这样弃读是不甘心的。于是一晚读几章,不能太峻急,面对一个已经身经百战的女战士,阅读者的姿态要宽容一点,就越来越能体味到了《北流》的好,我甚至以为《北流》一点不比几位跟林白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女性诺奖得主的作品逊色。
李跃豆词典里的词语们。它们带着南方幽蜜的气息,让我想起南方甜到有一丝臭的水果:芒果、波罗蜜直至榴莲飘飘的气息。但那些李跃豆式的词语又交织着北方大风的凛冽。等到我手边捧上了纸质书,我调整了自己的阅读状态,手拿一支笔,回到我最舒适的阅读状态时,《北流》的世界飞流直下三千尺。我意欲接纳林白倾尽全力倾倒而出的一切,人事岁月情绪故乡男女家长里短亲戚往来故人故交风俗等等,万花筒式的,一部林白的《追忆逝水年华》。如果说小马德莱娜饼干打开了病床上的普鲁斯特的所有记忆,那么是南方的那些幽密繁茂,色彩饱和度极高的植物,打开了林白记忆中那个纷乱的、喧嚣的,紧张的,怀疑的,疼痛的,怅然若失的,一次次想投入又一次次想逃离的故乡北流。
她以最自由最任性的方式书写,而我们有幸这样贴近地阅读到她的生命之书,读到她所有的真诚和坦率,这是有多难得啊。一个丰富多彩的女人老去也是一件美妙的事,因为经历了足够多的时代悲欢,看了足够多的红男绿女,她如巫如妖如佛如女流氓,从提笔的那一刻起她就拥有了至高话语权,加上足够强大足够高拔的诗人的才华,她驾驭《北流》如骑上一匹烈马。
因为她是林白,她不怕骑上烈马。骑上烈马写作的林白一向是先锋的。她从《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的盛年走来,走到了头发白了的暮年,化身一个叫李跃豆的一言难尽的女人,她既热爱故乡又站在故乡的对立面,她既拥抱亲人又冷酷无常,在《北流》中,我们看到了先锋女作家在故乡和都市之间的灵魂飘移。故乡有她喜欢的植物食物,有她愿意亲近的母亲河,有或庸常或烦闷或正在老去渐渐丧失人的尊严的故人,她偶尔与故乡的他们勾肩搭背,互诉衷肠,更多的时候,她离开故乡之后才能谈论故乡,并使故乡真正进入她的书写,她的文本。
有时候觉得写《北流》的林白是任由自己的感官在前进,在游弋。引领她的词语的本质是感官的,在感官之上的,才是美而短的词语:香港。县城。北流。滇中。火车。《北流》是流,所有的意象都是动态的,流动的。这是一本流动的书。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一直流动到当今。不是“贵妇还乡”,是一个成熟且对世界略带倦意又依然好奇心炽的周游过世界的北流女性,她回到北流。
用时下俗语来描述的话:在《说吧,房间》发表25周年后,这个叫林白的女作家野蛮生长,她率性得汪洋恣肆,终于成了《北流》里的李跃豆的模样。
序篇《植物志》的部分使出手不凡,“寂静降临时/你必定是一切”;“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你也可以认为整部《北流》就是一首长诗,如果我们对林白诗的记忆尚停留在《过程》的深情独白时代,那你得快进了。但你也不必太失落,因为你听到了《北流》的流水诗意在时间深处喃喃有声。
《北流》是什么?怎么形容一部记忆与当下交织之书?我以为《北流》就是在“瓢泼大雨之后重新看见了”。
林白,或者化身为李跃豆的林白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北流故乡的人们,无聊琐碎之事无穷无尽,日积月累。每个人都是许地山所言的“缀网劳蛛”。
看见了要强的一生的母亲,在《北流》中母亲的形象干脆从“母亲”这个过于亲密的称呼中剥离出来,她是梁远照。是货真价实的做过无数妇科手术的医生。她的一生都是一个独立的有爱有恨的女性,她甚至是叛逆的,她变成别人的后妈,将跃豆米豆们的日子中疏离而去。她是一个从母亲身份中挣扎出去的女人。65岁闯荡广东。她勇往直前的勇气远远超过了儿女。
看见了故乡县城。女性有委屈也不能说出。她们要去大城市,并非出于爱慕繁华,更是因为小地方太窒息。熟人社会是个大家庭,从头到脚,压抑多了几层。女性又多一层。县城是香港的对立面。
看见了发小们的生长态和各自的命运。
看见了特殊年分,比如恢复高考,改变无数人命运,加剧了社会变迁与人口流动的那一年。
看见了历史语境中的小人物们。看见了知青时期的男女关系,以及不能光明正大谈论的个人史。青春史。隐秘史。禁忌史。
看见了故乡物质史。从前的衣柜。菜摊。饭菜。河流。稻米。牛。青苔。猪油。土豆。茶。蘑菇。披风。
看见了李跃豆,如看见镜中的自己。“她从未记得母亲抱过她”。看见了李跃豆一路走来的爱情、谎言与背叛。她与故乡亲人(长辈、同辈兄弟、发小闺蜜)之间长达半生的纠缠。她亲近他们,排斥他们。观察他们。批判他们。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长度,既勾连又时常将要脱钩的,既天然亲近又疏离隔膜的亲密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故乡的这些人,承载了李跃豆人世间亲密关系的大部分所在。跃豆与遗腹子弟弟米豆这一对姐弟关系,跃豆与远照的母女关系都突破我们所见的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血缘亲情关系的描述,抵达到了另外的疆域。跃豆与少年闺蜜之间的关系,是“空山回音”式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林白将女性情谊的书写,提升到了哲学高度。
看见了在时代的大浪里故乡人物北上南下四处漂流的人生状态。梦想、现实、情和欲。每个人仿佛都伸长了脖子,要积极向上,但命运也可能会抛下其中的一些人。
看见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文本。
“当年他是个狂人,把一切不放在眼里。他打碎了泽鲜并改造她,使她崇拜服从,并相信女性的智商不如男性,女性应该为爱情牺牲,而为爱情牺牲的本质就是为男性牺牲。我大三大四那两年不停与泽鲜争论,写信或者当面,决裂之后又复合,讲了狠话之后又后悔,终于几十年不再联系。“
泽鲜“貌美、天真、纯朴,本来一切在正常轨道,忽然喻范来了,瞬间席卷而去,她坚信智力不如他,为他献出一切是件幸福的事情。早早结了婚,以她教书的收入维持两人生活。男人一事无成。后来两人远迁桂林乡下,泽鲜辞职。生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不上学,自己教育。又远迁云南,落脚滇中。
”我眼睁睁看着她渐行渐远,这位第一密友、自十岁起的多年玩伴,没多久,我就完全望不见她了“……
如今,她来到了他们开的六和茶庄,泽鲜却不在。泽鲜是真的有事不能来见,还是故意避之不见呢?
三十几年后,跃豆再审视喻范和泽鲜这一对她的朋友,当年以为的神仙眷侣、才子佳人。大有今是而昨非之感。最终,两个观念不一样的旧友并未相见。
“她变了,不再关心人类、宇宙、光年、改变大自然这些遥远的事物,她关心爱情。而我对爱情是鄙视的。多从未料到,会有某一天,我也会像她那样,遇上爱与痛。“
直到2021年底,“我才偶然知道,泽鲜和喻范已经分手十多年了。泽鲜说,我们仍然是灵魂伴侣。“
李跃豆与泽鲜的战争,谁又是胜利的那一个?泽鲜一个人的“个人史“,比整个北流的历史沿革更牵动我心。也可以说,每次当林白站在女性立场,她显示出的力量便是不容质疑的。
仿佛《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延续到了《北流》的生命历程之中。北流史也是一部生长女性史。或许可以说,这是一场两个人之间的战争,既可以认为是两性之间的战争,也可以是两个女性之间的战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战争。
《北流》,就像彼此缠绕又彼此独立的植物们。高大的是树,矮小的是灌木,再微不足道的灌木都有自己的根系。这就是从林白的记忆深处走出来的众生。
一部作家返乡之书的《北流》,众生在说话。普通话。粤语。北流方言。作家要返乡,说的是方言,所以有了“李跃豆词典”。朝花夕拾,繁花衰花、新叶败叶,只要在时间的缝隙里还能捡到的,她一一拾起,附之以修辞。只有修辞能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林白的魔力。而“李跃豆词典“最终也汇入了众生,汇入了北流,词语也随之流向了拼多多和抖音的新时代。流向了小城的独身女子。结婚三天就闪离的北流青年。林白是写了中国南方众生的福克纳式的作家。鉴于我从整个《北流》的南方谱系中,读出了阴性潮湿丰润的气质。如果要附和一下这个时代正在崛起的女性主义,不妨在作家林白之前,加一个曾经或许被嫌弃的,”女“字,因为《北流》除了对故乡有所打量之外,也同时深刻地触及了女性的命运。
《北流》也是一部从内心到万象的几何量级倍级的《说吧,房间》。
《北流》即万象。
文/萧耳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