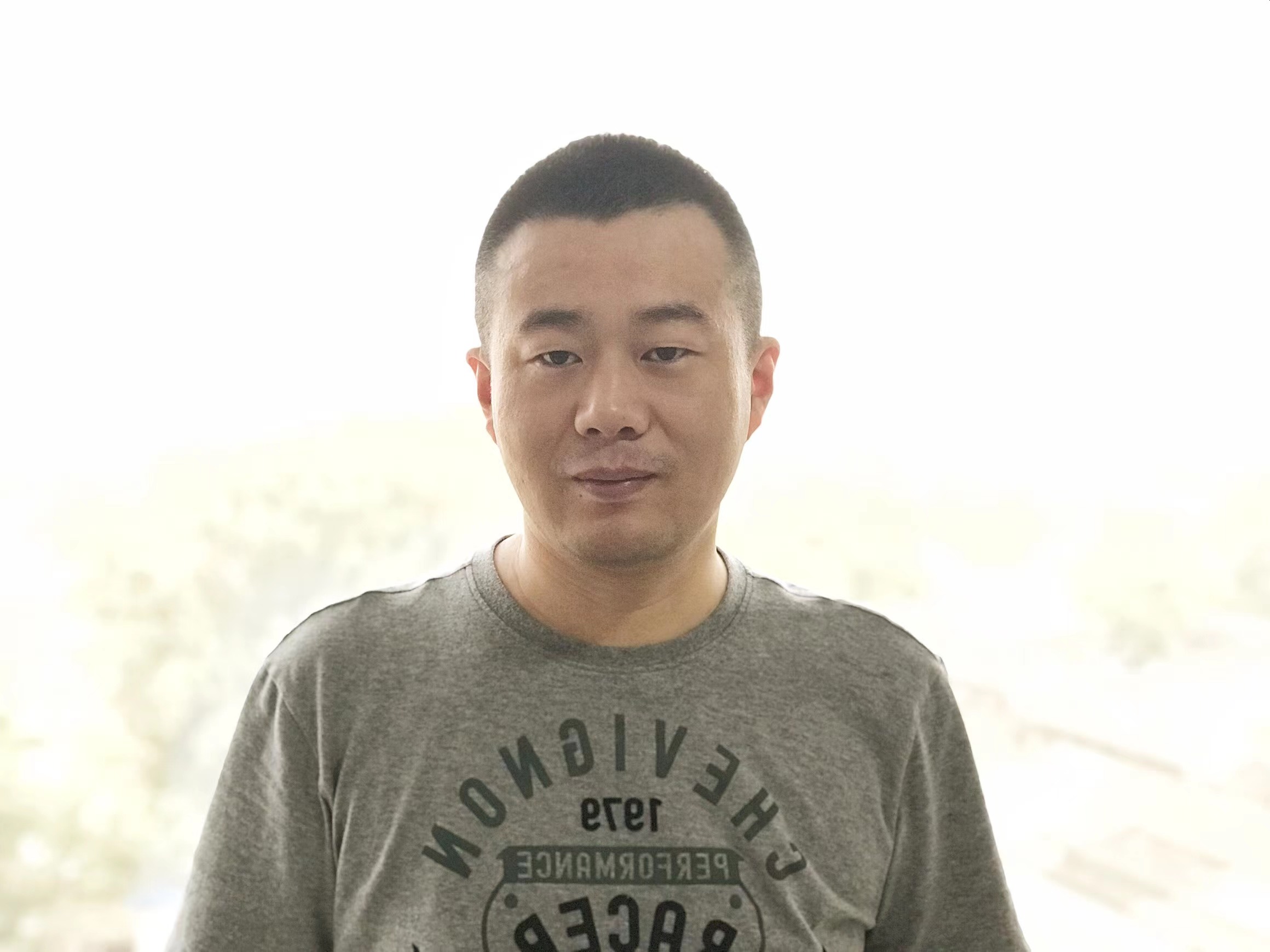
章子怡监制、周可导演、卢靖姗领衔主演的话剧《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后简称《娜拉归来》),上周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
引导女性也启蒙男性
该剧由美国剧作家卢卡斯·纳斯于2017年写就,他以续写易卜生1879年创作的经典《玩偶之家》的方式,完成对这位挪威戏剧大师的致敬。剧作字里行间既有对男权社会驯化女性等原作内容的重述,也有对女性追求独立人格等原作主旨的升华,是一部带有思辨意识的作品。
该剧的导演手段融入了即时拍摄、邀请观众参与表演等方式,舞台设计参考了艾略特的诗歌《荒原》、莎乐美的评论集《阁楼里的女人——莎乐美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以及易卜生原作中出现的荒野、天窗、火炉、圣诞树等元素和意象,服装造型尤其娜拉的装束没有过多的古典意味。它们与文本一样,属于创作者在当下的思维产物,为演员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和观众一起探讨女性的困境与出路、自我价值的实现与障碍、爱情与婚姻、家庭与责任、自由与边界、阶层与认知等带有辩论色彩的社会议题。
《玩偶之家》问世以来,与其他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一道,帮助世界各地的众多女性完成主体意识觉醒,挣脱神权、父权、夫权的桎梏。娜拉离家出走时那记响亮的摔门声,不仅惊醒了女性,也让不少男性反思社会与家庭结构,促使他们在家庭内部乃至社会分工层面,尝试与女性建构平等的关系,助推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
百年前,《玩偶之家》(其时译为《娜拉》或《傀儡家庭》)开始被中国的剧院及校园剧社竞相排演,出走的娜拉化作象征妇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符号,成为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引导他们勇敢逃离由封建家庭和婚姻构建的思想藩篱。可以说,在供女性亮相、青年登场的社会大舞台上,娜拉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各国作家纷纷效仿易卜生,书写符合本地与时代特征的“娜拉”形象,而随着女性主义观念的衍变与成熟,娜拉出走之后的故事,也在被不断续写。
中国作家亦提笔写下中国式的“娜拉”故事。比如在鲁迅的小说《伤逝》里,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在被父亲、叔叔等长辈阻挠时,她对涓生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续写娜拉泼点冷水
不过鲁迅没有让《伤逝》里的子君在不远的将来看见辉煌的曙色,而是安排了她以死亡收场。他在国人效仿娜拉出走成为时代风潮之际泼下冷水:1923年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发表演讲时,指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经济权和社会势力还被男人紧紧握在手中。
有意思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弗丽德·耶利内克在1977年创作的剧本《娜拉离开丈夫以后,又名“社会支柱”》中,表达了类似鲁迅的观点。这部剧作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剧中的娜拉凭借做家庭主妇时习得的做家务的能力,成了一名纺织女工,身份从中产阶级家庭的妇人变成了收入低微的无产者,由丈夫的玩偶变成了资本奴役的对象。但她没有打算像厂里绝大多数希望持续用可怜的薪酬适度改善家境的女工一样,将这份工作视为“终生事业”,不过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新生活”,她又不太清楚。
时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工厂因为机器设备老化面临被关停的风险,闻风而动的资本家看中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勾结官员谋划策略,欲将它变成进一步积累财富的工具。这一过程中,脸蛋漂亮擅长跳舞的娜拉成为资本博弈中的棋子,她被情人当作玩物送给官员及竞争对手——更悲剧的是,娜拉情人的对手是她的丈夫。当娜拉像工厂的老旧机器般不再具有被利用的价值,她被情人无情抛弃,沦为风尘女。娜拉不甘在家中做丈夫的金丝雀,在社会上成了男人们的笼中鸟。
对此,娜拉似乎有清醒的认知。她在为男人跳舞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当男权社会通过玷污女人而不断得到神圣化的时候,性感和色情就是一种屠杀女人的行为。这无非是一种维护父权统治的仪式罢了。”娜拉最终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因为那时的女性尽管争取到了基本人权,但远不足以撼动男性的话语权。
做出于本心的选择
而此次上演的《娜拉归来》中,娜拉似乎拥有了经济权。她出走后,将自己出走前围绕丈夫、孩子打转的家庭生活,以及由这种生活引发的顿悟与行动——即《玩偶之家》中的内容,用笔名写成了一本引发女性读者共鸣的畅销书。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让她有了很多钱,不仅买了一栋坐拥湖景的可爱小屋,还可以重新谈情说爱。
但鉴于不少家庭主妇效仿她的行径,这本书和她本人,成了许多男性的眼中钉。一位男法官在妻子离开他之后,着手调查娜拉的过往,发现她隐藏在笔名背后的真实姓名是“娜拉·海尔默”,以丈夫并没与她离婚、她冒充单身欺骗大众为由,威胁她如果不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发表声明,撤回书中一切言论,他将会行使手中的权力,公开她的真实身份,让她身败名裂,失掉所有财富。
这引起了她的恐慌。因为按照法律,一个已婚女人不可以做诸如签订合同之类的事情,也不能拥有财产。同时,法律规定,只有丈夫有权无条件离婚,妻子如果申请离婚,必须证明丈夫对她犯下了可怕的恶行。而她错就错在想当然地以为,在她离开后丈夫已经办理了与她的离婚手续。
娜拉不想让自己15年的努力所得化为乌有,归来的目的只为让丈夫补办离婚。但她围绕这件事与女仆、丈夫、女儿交谈时,逐渐显露出她头上虽然顶着女性主义作家的光环,但她的思维方式却受到男权社会及“唯金钱论”的影响。甚至,不自觉地,她成了自己所批判的男性群体中的一员,自私又冷漠。
她以不想让三个孩子的心灵创伤反复发作为由,切断了母子的一切联系,放弃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见到替她行使母职的女仆时,她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却以可以送女仆一大笔钱为筹码,让女仆帮自己想出能让丈夫补办离婚手续的办法;已经订婚的女儿不想像娜拉一样以爱情之名游戏人间,渴望能与爱人建立稳定持久的婚姻关系,娜拉却试图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观点强塞给女儿;她的突然出走带给丈夫的精神伤害,她更是毫不在乎。
某种程度上,她的女性主义观念,与网络盛行的田园女权、传统男权的主张并无区别,都是为了建立对立阵营,以便把另一个性别阵营里的人们打倒在地。
但易卜生也在其他剧作里说了,女性可以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只要那是她们出于本心的选择。《海上夫人》里的艾梨达,以为自己心向大海,但她最后没有跟随旧情人踏上驰往远方的航船,而是坚定地留在了丈夫身边。而放任无度的自由,则可能会让女性像《海达·高布乐》里的主人公一样“不作不死”,最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好在,《娜拉归来》中的娜拉最终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当丈夫拿出补办好的离婚手续,她选择了拒绝接受。随后,她做好了为尚未取得的合理权利战斗的准备,以更加勇敢坚定、属于女性的姿态,彻底离开了莎乐美在《阁楼里的女人》中提到那间禁锢女性灵魂的阁楼。
文/梅生
摄影/尹雪峰
编辑/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