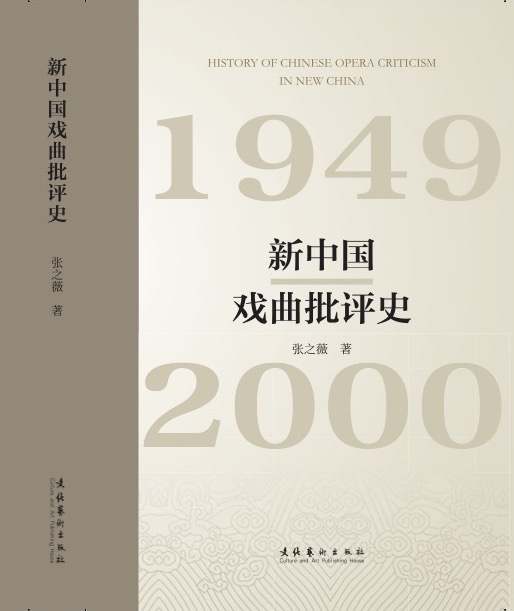作为中国“独一份”的表演艺术形态,戏曲在中国千年的文化进化史中,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在影视媒介出现之前,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和以国家级或地方院团主流形态出现的戏曲艺术,都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正因戏曲所具备的重要价值和功能,令它在近数十年的时代发展与变迁中经历了各种惊涛骇浪与起伏转折。其间的大事件与风云人物,其戏剧性可能比舞台上还要精彩三分。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张之薇的《新中国戏曲批评史(1949-2000)》一书,是从2013年开始立项并着手研究的。著书过程经历了沉入历史的海量资料及信源的搜集整理,主客观笔法及观察视角的选择也不断困扰着作者,其中的波折坎坷几乎让她产生放弃出版的念头。但可喜的是,最终她在跨越半个世纪的庞杂史料中,以“戏曲批评史”为切入口,通过对“批评”的浓缩采样,以“更接近真理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历史事件,不但为我们复盘了中国戏曲发展的波澜壮阔,也揭示出戏曲批评被种种非学术性因素掩盖的草灰蛇线。
改造
《新中国戏曲批评史(1949-2000)》一书聚焦戏曲改革、戏曲现代化和戏剧的传统与创新三大核心问题,清晰地刻画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问题通过评论领域所呈现出来的当时当刻的焦点与样貌。
全书按照时间轴将新中国的戏曲批评史分成五个主要时段。首先是1949年之前,由延安平剧研究院代表的边区戏曲改造阶段。二十世纪30年代末,在延安及西北、华北各根据地土地上的戏剧,开始了“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服从于战争”的“改造”过程。改造以宣传、动员、战斗、鼓舞为主导功能,与旧剧(戏曲)、秧歌、小调等群众基础很好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目的明确地将革命内容和政治倾向注入其内。这也可以被视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改”的先声。
同时,对传统戏进行套用,将现代故事和人物植入其中——这种“旧瓶装新酒”模式与编演新剧的模式并存。二者都是将戏曲这一娱乐化的民间形式与政治相契合,让承载着民众狂欢、伦理教化、精神愉悦的戏剧与革命话语嫁接,共同构成了1949年之前的“戏改”主流。作为“戏改”最初的实践者阿甲,便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他“推陈出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且将工作重点放在了解决“旧艺术形式和政治现实的不统一”这个主要矛盾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打渔杀家》改编的京剧现代戏《松花江上》是这种作品的代表。
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戏改”工作全面拉开帷幕。由戏曲界代表人物和戏剧专家等组成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和戏曲改进委员会,一方面在制定戏曲相关政策和组织力量整理、改编、创作戏曲剧目上下了大功夫;另一方面也从改革戏曲班社制度、团结和改造戏曲艺人方面入手,开始触及人与制度的问题,称为“改戏、改人、改制”。
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在这个过程中承担起至为重要的“新旧剧联系的桥梁”的职责。他在1949年至1950年写给周扬的三封信中,阐述了自己对旧剧进行修改和创造的思路,同时也为《四郎探母》这种因为“民族立场”而被禁的戏鸣冤,认为应当看到其中的艺术性和戏剧性。1951年《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出台,提出各地不能擅自禁演,提倡“百花齐放”,注意地方戏、民间小戏的珍贵——这些,都为当时地方戏曲恢复生存空间提供了可能。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式作为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彼时关于《琵琶记》等旧剧的激烈讨论与争锋,也可视为对古典戏曲代表作品如何改编的复杂思考与学术探讨。
此后,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批评与关于旧戏的形式革新的讨论,一直激烈进行。从导演这一身份在戏曲中的介入,到对“丑恶”脸谱的清除等争论,逐渐过渡到戏曲改革的“移步”与“换形”层面——一场关于戏曲本体方方面面的大讨论拉开序幕。在这场争论中,根据所持观点的激进与否,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其间大批学者、戏剧理论家和演员都参与其中,包括马少波、老舍、吴祖光、梅兰芳、赵树理等。
“十七年”时期承接了1949年以前的延安及各根据地、解放区的戏曲创作导向,同时又开启了之后十年戏曲发展的命运。作为中国众多文化艺术形态中曾经受众最广、最接近民众的艺术形式,戏曲随着时代的颠簸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推至浪潮顶端乃至落下”。
经历了京剧样板戏的“一枝独秀”,以及《海瑞罢官》这种作品的跌宕起伏,戏曲艺术的批评生态在“文革”中退化成一种完全依附于政治风向的批评史。
恢复
《新中国戏曲批评史(1949-2000)》中,以两章的篇幅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戏曲批评进行观察。作者描述,“文革”结束后,戏曲一方面要面对影视等覆盖更广泛观众的艺术形式带来的竞争挤压和生存困境,另一方面要面对自身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的难题。但无论如何,这些难题已经比之前动辄被裹挟的处境要宽松多了。戏曲自身的探索与发展,戏曲理论和批评的正常对话生态,也开始逐渐恢复。
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广阔的视野为戏曲批评导入新鲜的视野和空气。像李洁非等跨领域的文化批评者,用“第三只眼”看戏曲理论建设的时候,更直接地指出:“它经常用某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逻辑和观点来谈论艺术问题。这些观点实际上大部分来自于五十年代的那种苏联文艺概论体系教条。而这种体系的主要特点却是以社会史逻辑代替艺术史逻辑、以政治经济学代替艺术本体论。”
在今天的舆论环境和戏曲理论领域,一些陈旧的观念和烙印在慢慢淡化,关于戏曲自身艺术规律和创新发展的思考,正在越来越回归本体。而张之薇的这本《新中国戏曲批评史(1949-2000)》,为我们忠实描摹了这样一段筚路蓝缕的路程与足迹。
书中收录的作者与评论家林克欢的对话录中,林克欢先生有一段锥心之语:“我们遗忘了太多的东西……我说学者一定要做好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反历史,而是深入历史的真相。”如林克欢先生所言,张之薇的这本“史”书,不仅在学术上拥有扎实的底座,更难得的,是她以耐心和勇气,十年磨一镜,替我们照见那些被遮蔽的历史。
文|水晶
编辑/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