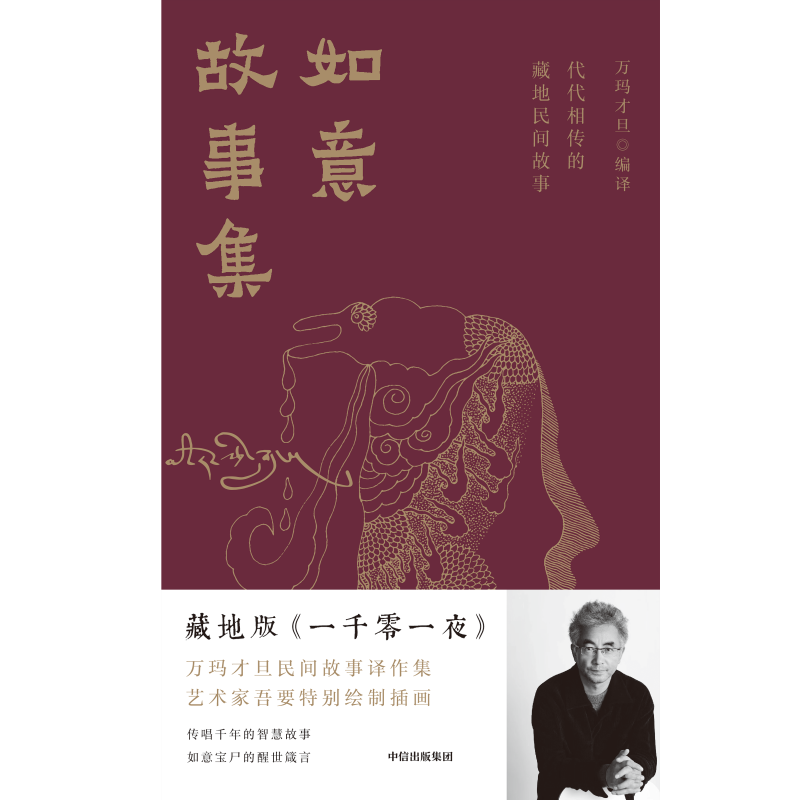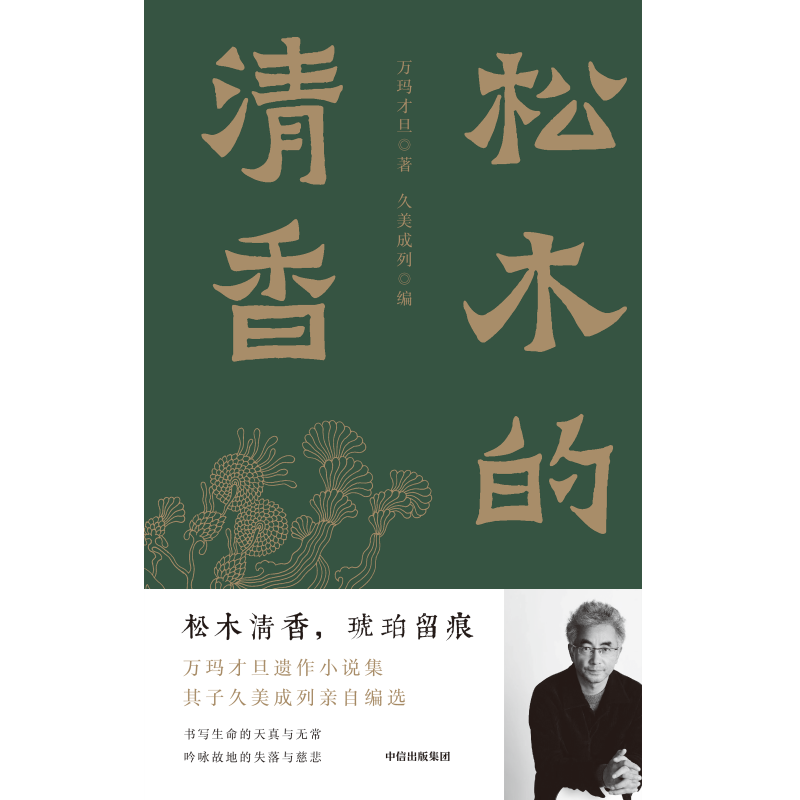万玛才旦(刘大雁 摄)
2024年5月8日,是导演、编剧、小说家及文学译者万玛才旦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中信出版·大方推出了万玛才旦的遗作小说集《松木的清香》和译作集《如意故事集:代代相传的藏地民间故事》作为纪念。
《松木的清香》收录和整理了作为小说家的万玛才旦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篇目,这些作品经由万玛才旦之子、青年导演久美成列编选确定,以久美成列和陈丹青撰写的怀念文章为序言和跋。《如意故事集》则收录了万玛才旦所整理翻译的藏族民间传说尸语故事(中国藏族民间故事,源出印度,融入了西藏地域文化等,可以看做本土重新再创作的文学作品)。
5月6日,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谢飞,作家、批评家李敬泽,作家、《西藏文学》主编次仁罗布,青年导演、编剧久美成列和媒体人余雅琴以“亲爱的万玛才旦”为主题,一起讲述他们眼中的万玛才旦,并从电影、文学、翻译创作等角度,讨论了万玛才旦对于当代文学和艺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读就知道很会写”
经过他的加工 凡人琐事都闪现着人性的光彩
耄耋之年的谢飞导演想起万玛才旦的突然离去,有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作为万玛才旦的恩师,谢飞回忆起初见万玛才旦的缘由。
2002年前后,万玛才旦从西北民族大学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编导班进修,彼时的谢飞导演已经退休,但仍然关心着电影学院的教学工作。他发现录像带兴起之后,北京电影学院为了节省经费,学生们的毕业作品不再使用胶片拍摄作业。谢飞导演为此感到可惜,认为应该让学生多接触胶片,因而提议学校多拿出经费让学生用35mm的彩色胶片去拍摄作业。同时,谢飞导演得知当时的导演系没有本科毕业的学生,剧本的编写成为了关键问题。于是,向全校各专业的学生发出邀请,600多名本科生都可以写剧本,被挑选出的学生就可以当导演、拍摄短片。
就在那时,谢飞看到了万玛才旦的剧本《草原》,“一读就知道很会写,而且能看出是有过藏族生活的经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谢飞导演曾两次到西藏拍摄关于藏族题材的电影,深感当地的影视创作虽然有过一些美术和摄影人员的培养,但是在编导方向却较为欠缺,所以非常希望电影学院可以培养出藏族的编导人才。
2004年,谢飞导演第一次见到了万玛才旦。当时,万玛才旦给谢飞看了自己在文学系拍摄的录像带短片《静静的嘛呢石》。谢飞认为,万玛才旦已有拍摄能力和经验,于是同意他回家乡拍摄《草原》。这也是万玛才旦首次使用35mm彩色胶片拍摄短片,该片后来获得了第3届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中国学生最佳短片奖。“我很喜欢万玛才旦,这部片子拍得不错,后来也在电影频道放映了。”谢飞回忆道。2005年,万玛才旦还将短片《静静的嘛呢石》拍摄成了剧情长片,这是万玛才旦自编自导的长片首作,获得第25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2006年,万玛才旦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继续攻读硕士。“那些年一直跟他有联系,而且我每次到青海去,他都请我们吃藏菜,非常友好和热情的一个人。中国现在称得起作家导演的可能只有两位:一位是贾樟柯,另一位就是万玛才旦。万玛才旦是真正的作家导演,先是写小说,然后才当导演。贾樟柯有写作品的能力,但他不写小说。所以,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又出版了,我很高兴这些作品能够跟读者见面。”谢飞感叹道。
谢飞导演曾与万玛才旦探讨过写作的问题,他认为万玛才旦写的是凡人琐事,而这些事情经过万玛才旦的加工,都闪现着人性的光彩。谢飞导演曾问万玛才旦能否写一些凡人大事,比如写一个普通人生生死死的大事、爱情大事或是生命意义的大事,而不是写琐事。万玛才旦听罢直笑,不说话。后来,谢飞导演认为:“任何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抱负,万玛才旦可能就爱写小事,而不是长篇的大事,他有他的艺术特点。”
“我们两个都是笑眯眯地沉默着”
万玛才旦的力量在于庄子的“齐物而观之”
对于作家李敬泽而言,万玛才旦的主要身份是一位作家。李敬泽几乎没有看过万玛才旦的影片,“但是万玛才旦的小说,基本上都读过”。
提到与万玛才旦的关系,李敬泽坦言两人没有过很密切的来往,甚至没有过单独的个人来往。李敬泽回忆道:“我和万玛才旦有两三次面对面地坐在那里,我们两个都没有很多的话可说,最后都是笑眯眯地沉默着。有时候,万玛才旦也寄书给我,我能够看的都会看。”
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中,李敬泽阅读了《如意故事集》。尽管这本藏族民间故事集是由万玛才旦翻译而成的,但是李敬泽认为将这本书放入万玛才旦的作品序列中,并不违和。“当我看了《如意故事集》,忽然想到有时候我们会把隐忍和克制当成一种艺术手法,其实对万玛才旦而言,这不是艺术手法的问题。我们体会到的隐忍和克制,在万玛才旦的处理上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就是他面对这个世界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根本的感知结构、感知方式。”
李敬泽用庄子“齐物而观之”的观点概括了万玛才旦的创作与选择,认为万玛才旦不在意文化背景的差异与界限。“万玛才旦在处理人类或者生活中的所有大的、小的、微妙的和直接的东西,都能够给一种淡然和自然的语调。我觉得万玛才旦的力量常常在于庄子的‘齐物而观之’,万玛才旦并没有非常刻意地把文化背景的差异作为他表意的中心。他是‘齐物’,就是站在‘我’的世界里讲‘我’的这个世界中很自然的事,并不是把‘我’和‘你’的差异当成多大一件事,或者是把‘我’和‘你’的差异当成一种艺术风格的界限,或者要在这个界限中获得什么。”
李敬泽相信万玛才旦的创作力量、独特语调、独到眼光会永远留在读者与观众心中,“万玛才旦之所以是万玛才旦,其根本力量可能还是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文字之中”。他认为万玛才旦独特的语调,让读者能在众多的文字中一眼辨认出万玛才旦来,尽管读者可能遗忘了故事,但这种语调始终让人铭记。
在参加活动的前一日,李敬泽忽然翻到了普希金的诗歌《纪念碑》,普希金写道:“不,我不会一整个地死去。”李敬泽由此想到:“尽管一个生命完结了、终结了,但对一个作家来说,或者说对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他的力量、他的非常独特的语调,以至于在电影中非常独特的那副眼光,我觉得是不会离去的,会留下来。”
对此,媒体人余雅琴感同身受,她感叹道:“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跟万玛才旦老师也有过很多次的接触,我到现在还是特别不能接受他已经离开我们的事实,因为总觉得他的微信好像还在微信列表里面,我们可能只是没有见面。因为一直想着他,也一直有他的作品,也会看到他出的书,总是感觉这种离去的体会是很恍惚的。可能正是因为他留下的这些东西被我们看到和记住,他似乎并没有离开我们很远。”
“万玛才旦老师,我想认识你”
在他的身上,看不出任何陌生感 他让人很容易亲近
作家次仁罗布与万玛才旦的初识是通过文学。他们年轻时都在《西藏文学》上发表过作品,对文学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当万玛才旦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时,次仁罗布则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次仁罗布在当时体会到了万玛才旦的改变,即“从文学创作跨越到另一个新的领域”。此后不久,当次仁罗布看到万玛才旦的毕业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之后,产生了一种心灵的震撼。他认为万玛才旦通过这部藏地电影对人性进行了深刻地挖掘,因此很认同万玛才旦所走的电影之路,对万玛才旦充满着期待。
每当次仁罗布到北京时,万玛才旦都会对次仁罗布的作品提出建议,同时提出很想要改编文学作品的想法。次仁罗布回忆道:“因为我当时是在报社,我说我人生最伟大的终极目标就是出一本小说集,能够有一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我这一生就无憾了。万玛才旦当时说要把我的小说《杀手》改编成电影,但真正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已是之后五六年的事情。后来,他在拍片过程中跟我说给我的价格偏低了,要给我补偿。因为他认同作品的价值,也知道这部作品出来以后的效果,同时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万玛才旦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值得尊敬、值得信任的人。”
次仁罗布认为万玛才旦是一位特别低调和执着的人,他对文学的梦想和对电影的追求,让次仁罗布深受感动。此外,从万玛才旦的身上,次仁罗布看不出任何陌生的感觉,万玛才旦就是普通人的气质。“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容易亲近,是一个特别诚实、可以把心交给这个人的一个人。”次仁罗布再次感叹道。
余雅琴通过次仁罗布的分享,回想起对万玛才旦的印象,“其实他很少讲话,但好像总是在关键的时候讲两句,让我们觉得特别幸福”。在余雅琴的印象中,在很多电影活动现场,万玛才旦的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年轻人。余雅琴解释道:“因为对于年轻人的提问也好、寻求帮助也好,他从来都不拒绝。我感觉在任何场合只要有人走到他的面前,说‘万玛才旦老师,我想认识你,能不能加你微信?’他都会同意的。直到现在,很多年轻导演在推出作品时,我们还能看到监制是万玛才旦老师的名字,是因为只要对方提出要求,他都会伸出援手。”
“再见,阿爸”
父亲是一个很完整的人 “真实”两个字是他给我最深的影响
“我想写些什么,但每次看着空白的文档,坐了很久也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从何开始。”这是《松木的清香》的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来自于久美成列写给父亲万玛才旦的一封信——《再见,阿爸》。
在过去的一年中,久美成列一直在克制着不去想自己的父亲,“一旦去想他,就会真的很伤感”。前不久,在万玛才旦执导的影片《雪豹》将要结束公映时,久美成列回到家中,偶然看到一个关于一些美国当兵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孩子面前的短视频,视频中的孩子们都在哭泣。他想到如果他的父亲忽然回来,自己会是什么反应,一想到这里,久美成列突然落泪了。
“其实这一年,我想的最多的可能是,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很完整的人。我是大学毕业23岁开始拍电影,一直做到现在。我会觉得我经历的太少了,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分享。”久美成列感叹着自己的经历太少,于是谈到了万玛才旦一生的经历。万玛才旦拍摄第一部作品时是36岁,在那之前,他放过羊,一个人从小山村考到兰州,学习藏文专业、翻译专业,读完以后又回到家乡的政府单位工作,结婚生子。“我觉得他完整地经历过这个世间的所有一切,而且正因为这份完整,他可以有源源不尽的东西去创作。他对这个世界有很完整的看法,即便身在电影行业面对这么多困难的问题要处理,也永远有一颗非常坚定的心。”
久美成列记得,父亲在电影学院读硕士期间,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手里都会有两个红色的大塑料袋,里面装有五十张影碟,从未间断。“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他愿意把所有的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电影上、文学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家庭氛围,就是会对精神上的东西有些追求。”久美成列解释道。
正如很多观众认为久美成列的电影作品《一个和四个》与万玛才旦的电影风格迥异,久美成列也愈发觉得自己与父亲是完完全全两种性格的人。如果万玛才旦会答应所有的要求,包容所有的一切,而久美成列则是相反的状态——“这一年里,我拒绝了很多事情,拒绝了很多人”。“之前我最喜欢我父亲的电影是《老狗》,因为看到了极度撕扯内心和让我心痛的世界,我很是感同身受。现在我又特别喜欢《寻找智美更登》,我看到了水流淌在整个藏区,乘着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所有很诗意的东西,这是我父亲在去世之前给到我的一种状态。但我不是这种状态,我就像一个刺一样,乱七八糟地生长,戳破一些事情,表达自己的想法,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虽然父子性格不同,但万玛才旦的影响仍旧真切地流淌在久美成列的身体里。“真实两个字是我父亲给我最深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拍什么样的故事,拍任何一个时代的故事,拍任何一个跟你有关的故事,去呈现一个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世界、真实地看到藏族人在现在是怎样生活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要传承的东西。我父亲的作品在那里,我觉得他就会永远在那里。”
在写给父亲万玛才旦的那封信末尾,久美成列写道:
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多人关心我。我很感动。我们会互相拍拍肩膀,紧紧拥抱。我只是感叹,您身边围绕着的怎么都是这么好的人。以后的路,会有很多人和我并肩同行。我会像第一次跟您上山煨桑一样,累了就看看远处宽广的河流,从山脚下密密麻麻的房舍里分辨出家的位置,再边走边笑着爬上山顶。在那里,我们将高声呼喊您的名字,伴随着无数的风马旗飘向更远更远的地方。不用再担心我了,好好静下心来喝杯酥油茶吧。再见,阿爸。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供图/中信出版·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