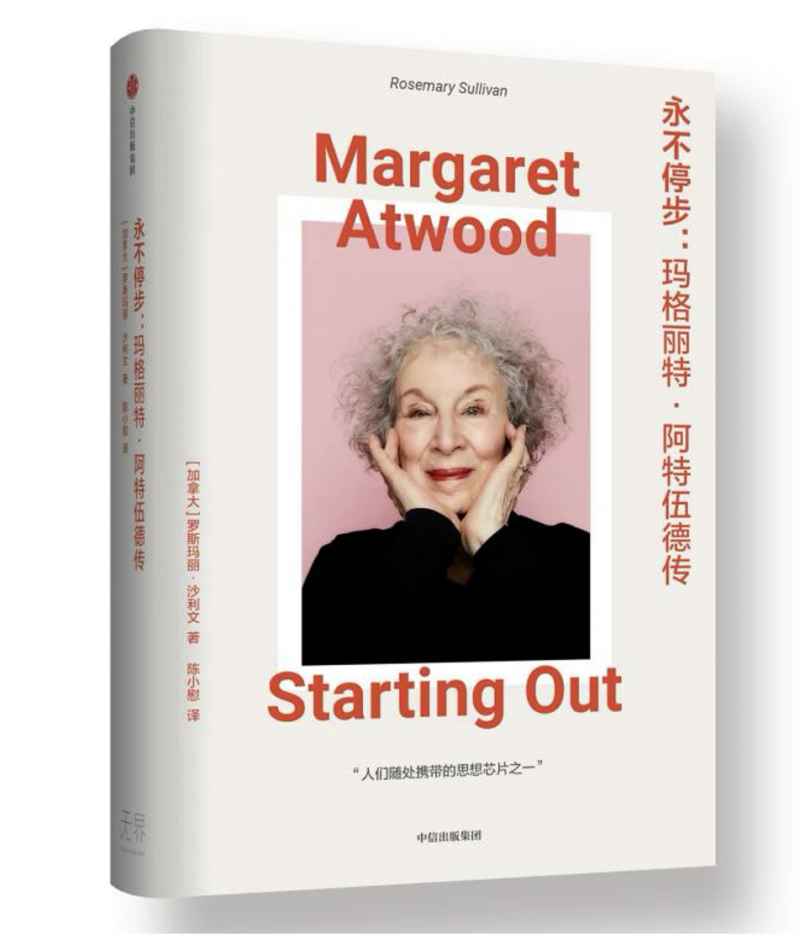记忆中,那是一个周四的夜晚,地点位于安大略湖边一角的多伦多海滨艺术中心。该中心负责文学活动的艺术总监格雷格·盖腾比组织了一场读书会,以支持位于巴黎的阿比书店(也译“修道院书店”)。那是一家加拿大双语书店。好些多伦多著名作家都被邀请来这里读书。
作家们坐在主楼多功能大厅前的小桌子旁,桌上铺着格子布,点着蜡烛,让人仿佛置身于巴黎的卡巴莱歌舞表演餐厅。被邀请的嘉宾中也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尽管声名显赫,她却有办法悄无声息地进入会场,不引起旁人注意。她身材娇小,带着某种紧致干练的磁场引力。有点像鸟类。喜鹊,她有时这样形容自己。
那天晚上,关于她的新作《别名格蕾丝》,各种说法可谓满天飞。在这之前,《环球邮报》上已经刊出了一篇冷静客观的评论。
她有一双蓝眼睛,很大,近乎透明。在她与人打招呼时,我注意到她眼神中带着点焦虑。或许这只是我的揣测。我在想身为一个著名作家意味着什么。写作是最具个性、最能暴露自我的艺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没有缓冲区。作者一旦失败,只能独自咽下苦果。
彼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已是声名遐迩。当晚她早已得知《别名格蕾丝》将在许多国家出版。它会变成一个个陌生的文本,用她完全不懂的多种语言写成,进入成千上万她从未见过的读者内心。然而,在我看来,她似乎担心文学界会如何看待她的作品。可我为什么要对此感到惊讶呢?
格雷格·盖腾比推荐我们读了一本书,大家一致认为这本书值得引起更多关注,希望它能译成法语,在阿比书店出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则读了土著作家托马斯·金的小说《芳草青青,流水潺潺》。她很搞笑,将书中魔术师的人物角色学得惟妙惟肖。我想,是的,她本人就是一个魔术师。恶作剧,变形人,挑战人们想当然的观念和惯例。有谁能够真正理解她呢?
而这正是我打算做的。那时,我正着手写一本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书。尽管尚不知该如何称呼这本书,但“非传记”最接近我原先的构想。
我想写她的创作生活。但我需要用一个词来描述我的站位。我想到了“中距离”。我会从中距离的角度来写,在塑造她的文化及其创作思想之间建立连接。它不会是一本八卦书籍。谁会告诉我那些东西呢?而且,道听途说的一点点八卦也引不起我丝毫兴趣。八卦是表面上的故事,通常意在破坏和贬低他人生活。
它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我知道,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只能在回顾中精心制作。它是一种怀旧的活动,是在收集了回忆录、信件和轶事之后,对有关主人公各种观点的综合。
相反,我想写一本关于创作生活的书。对什么使写作成为可能,人们有太多的困惑。我的书应该重点聚焦,是什么动力驱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断前行,前进道路上存在哪些疑虑与困惑,她又如何战胜它们,取得成就。此书会将阿特伍德置身于她所处的时代,那一代人曾经齐心协力,共同改变了加拿大文学的样貌。我希望用这本书表明,思维和想象力才是真正快乐生活的核心,而在我们这个注重现实的时代,这一点几乎已被人遗忘。在这个时代,关于个人的故事似乎只能在生活方式和卧室八卦的层面上被人津津乐道。
不过,我还有更深层次的动机。我想写第三本书,使前两本的叙事得以完整。之前两本都是名副其实的传记,也都是关于女性作家。但故事充满了挫折,甚至痛苦,最后归于沉默。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第一本传记的主人公伊丽莎白·斯玛特在27岁时写了一部杰作,之后沉寂了30年。据她自己说,是因为自信心缺乏。她总感到有一只模糊不清的手搭在自己的肩上,她称之为“男性文学大师”。这个幽灵告诉她,她永远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第二位作家格温多林·麦克尤恩死得很惨,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深信艺术不值得女性去付出孤独的代价。在书中,我将她们奉为杰出作家,心里却总有挥之不去的内疚感:我这岂不是在无意中延续了女性艺术家必定下场可悲的刻板印象吗?毫无疑问,我觉得,一定还有其他的叙事。我希望能写一个不同的版本。我觉得有必要写一个既独立自主,同时又能很好掌控艺术与生活的女作家。
当我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解释这个想法时,一开始她误解了我的意图。“我还没死呢,”她回答。我把自己的非传记理论讲給她听,她也只是稍稍缓和了一点情绪。最让她难以接受的似乎是,我可能会把她变成一个楷模,一个榜样;而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这样一个形象。或者,我可以从她生活的无数细节中创造出一种人为的秩序,只需要把它变成一种叙事。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编造一个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人,而此人与这个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奋笔书写的女性毫无关联。我不就是在延续这种感觉吗?
那么,我为何要写一本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书?原因是,私底下我对艺术自信的奥秘非常着迷。究竟坚信自己身为作家的力量从何而来?仅仅是出于个人原因吗?为什么许多有才华的人从不敢孤注一掷,冒险踏上成为艺术家的旅程,因为它代价高昂?为什么还有些人,比如伊丽莎白·斯玛特,因此而一蹶不振?是需要修养方面的支撑吗?
每当我想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脑海里就会泛起一件轶事:
那是1948年或1949年,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影院里观看电影。那时候,这可是难得的享受。是同学的生日会,家长请小朋友们看的。电影叫《红菱艳》,讲述一个名叫维多利亚·佩姬的年轻姑娘成为世界著名芭蕾舞者的故事。维多利亚很漂亮,她戴着钻石头饰,穿着轻盈的芭蕾舞裙,像个公主一样,在优雅的舞厅和各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欧洲城市里翩翩起舞。小姑娘看得如痴如醉,因为她也想变成这样的人。可突然间,她万分沮丧地瘫坐在座位上。影片中维多利亚的生活正演变为一场悲剧。大师对她横加训斥,年轻的丈夫离她而去。最后,她跳到迎面而来的火车前,被碾死了。小女孩感受到了影片传递的隐含信息,并为此震撼不已:如果你是女孩,就不可能既当艺术家又当妻子。如果想两者兼得,最终结局就是与飞驰而来的火车相撞,落个粉身碎骨的可悲下场。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是那个影院里的小姑娘。在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女孩们还会因为创作野心而受到打压,但她后来却成为了一名杰出作家。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讲述她幼年时代的故事,讲她观看《红菱艳》时受到的巨大心理打击,一个令我着迷的问题是:尽管她为此感到沮丧,却为何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如果这就是她看到的幻象,又是什么原因,通过什么途径,使她能够成功逃离?许多1939年出生的年轻女孩都仍然把影片中传递的思想铭记于心。而在前女权主义时代,这个年轻女孩又是如何培养出这种天赋的能力,毫不动摇地坚信自己呢?
在一次采访当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说:“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我们对作家的看法多少带着点浪漫色彩。我们认为‘写作’与作家做的事情无涉,而是与作家本身有关。” 这句话听起来无关痛痒,但一旦认真思考,会发现其涵义深远。
在以上含糊其辞的话语中,她将有关艺术家的浪漫主义历史瞬间消解。这种对作家的认知,比起其他任何东西,都值得尝试去挖掘。
当她刚开始作家生涯时,一个年轻女孩要相信自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年前,她曾说过:“与男性相比,很少有女性在早期就有强烈的动机认真写作……‘当作家’更容易被她们视为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一种工作状态。”一旦无法立刻得到认可,就很容易放弃。 “特别是女孩子,她们所受的教育,让她们学会取悦和安抚他人。一旦有人不喜欢她们,她们就会认为是自己的失败。” 为了写好作品——“而去钻研、去探索、去接受他者规训、去迎难而上,其中包括遭遇失败的风险”——在年轻女性中并不受鼓励。
关于一个人如何形成自信和勇敢的态度,“没有这些,成为作家的计划是否就会变成一个笑话”的问题,她解释说,“一个人作为作家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作为一个人的充分自信有很大关系……而这来自其童年时代。” 那么,她的自信是根源于其童年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一个在电影院里观看《红菱艳》的小姑娘,到成为一名在国际上声名遐迩的成功作家,其成长历程是本书叙事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我认为这个故事是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集体叙事的一部分。以下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同时期出生或同时期成名的作家名单令人印象深刻:A.S.拜厄特、娜丁·戈迪默、乔伊斯·卡萝尔·奥茨、安杰拉·卡特、汤婷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玛丽-克莱尔·布莱斯、玛吉·皮尔西、玛丽莲·鲁宾逊、托妮·莫里森、艾莉森·卢里、安·贝蒂、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还有其他许多。这些女性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贴在男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身上的传统标签。
如果我们回到1948年上映的《红菱艳》,当时战争片充斥着银幕,电影工业也在争相寻找新的主题,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部电影看作是对女性在艺术中所扮演角色的思考。最初的剧本由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撰写,主题是莫伊拉·希勒饰演的维多利亚·佩姬的芭蕾舞生涯。维多利亚是一个志向高远的年轻舞者,被著名的导演和编舞鲍里斯·莱蒙托夫聘用。他是一位老派大师,习惯使用无情的戒律和刻意羞辱的方式培养舞者。艺术对莱蒙托夫来说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维多利亚则是他创作的作品。
莱蒙托夫为她写了芭蕾舞剧《红舞鞋》,由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改编而来。他是这样向她描述这个故事的:“一个女孩从吉普赛人那里买来了一双红色舞鞋,一心想穿着它跳出成就。一开始她跳得很开心,后来她累了,想回家。但红舞鞋不累。它们不知疲倦,带着她不停地跳,从室内跳到野外。时间匆匆而过,爱情匆匆而过,生命匆匆而过。但红舞鞋仍在不停不歇地跳着。最后她死了。”
这个故事构思极其巧妙,简直就是一个关于女艺术家宿命的寓言。莱蒙托夫怀着嫉妒心和占有欲,把维多利亚视为自己创作的作品。她是能保证他名声不朽的可塑之材。但她犯了一个弥天大错,爱上并嫁给了公司的年轻作曲家。她成了两个男人争斗中的棋子。莱蒙托夫愤怒地高喊:“身为舞者,一旦沉溺于人类之爱那令人怀疑的舒适安逸,便永远无法成为伟大的舞者。绝不可能!”丈夫则要她为了他放弃艺术。他需要她陪在身边,当他的缪斯和灵感。她试图选择自己的艺术,但这个决定毁了她。在电影结尾,维多利亚似乎选择了事业而不是婚姻,她走向舞台入口,表演芭蕾舞剧《红舞鞋》。但突然之间,红舞鞋拥有了自己的意志。带着她来到阳台,俯瞰着她丈夫即将离开的火车站;又让她跃过阳台的栏杆。在她奄奄一息之际,她恳求丈夫为她脱掉红舞鞋。
显然,女性就应该是缪斯女神,而不是大师。难怪五十年前,年幼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会坐在影院的座位上垂头丧气。是什么导致一个拥有自己艺术事业的女性如此高危?答案很简单。在已经成为传统的行事方式中,女性只能一成不变地身为被动的艺术灵感,缺了她,男人便无法从事创作。
1948年,妇女在获得劳动力解放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加拿大各地的大小厨房,把自己从事的工作留给从前线回来的男人。对于那些享受过公众生活的女性来说,继续假装自己从未迈出过家门,一定感觉像是患上了某种无情的失忆症。而《红舞鞋》表明,艺术也必须当仁不让地重新确立为男性的专属特权。
男性艺术家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它从何而来,为什么必须如此拼命地加以保护?
男性艺术家的肖像画可以说浪漫得令人难以释怀。当然,我们对艺术家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是陈腐老旧的,还是那个从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中进化出来的形象。我想到了珀西·比希·雪莱,最早也是真正的波西米亚诗人之一。随着工业中产阶级把艺术家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浪漫的叛逆。艺术比生活更重要。它是一种宗教信仰。艺术生活是一种巨大的牺牲。(相矛盾的是,它也是一种极大的放纵。)于是,这样一位致力于自我表达的波西米亚艺术家便诞生了。
在那个世界里,女人必不可少,但只是作为缪斯而存在。而那位以滥交著称的男性艺术家,则需要众多女性陪伴其左右。女性被这种天才使女的角色所吸引,因为这意味着选择(通常以美貌为基础)。任何渴望成为艺术家的女人都是他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使女。如果她真的有足够的自信来实现这样的愿望,她就必须被打倒。毕竟,她是要让自己的艺术和男人的艺术同等重要,这便构成了威胁。
但世界真的就只能照此模式运转吗?当然,上述之说通常只是作为一种带有主导性的陈腐神话。尽管如此,它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令人瞠目。其结果是,艺术成了男人的专属游戏。女性艺术家在艺术界没有一席之地,将来也不会有。一直要到有足够多的女性挺身而出,消灭这个陈词滥调,这种现象才有可能改变。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一代的女性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也许更重要的是,她们摧毁了第二种刻板印象。在女性肖像史上,母亲和孩子的形象断然排除了艺术创作的可能性,除非作为写作对象。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不可能既是母亲又是艺术家。就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之前的上一代人中,许多妇女都深信,把生育和事业混为一谈是不可能的。例如,为了能够写作,梅维丝·加伦特在巴黎过着孤独的生活。琼·里斯、玛丽安娜·穆尔、弗兰纳里·奥康纳等人都没有要孩子。当然,的确有许多女性可以做到两者兼顾,但这一事实似乎从未进入集体想象。多丽丝·莱辛在决心成为作家后,从南非带了自己的一个孩子来到英国。但在那里她不得不面对独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处境。这么做并没有使她与广泛流行的神话相抗衡。艺术家的生活注定就是偏执狂的单身生活。据说这需要一种近乎贪婪的自我中心意识。如果有孩子,就等于要牺牲自己的艺术。时至今日,独自抚养孩子仍然不易。但在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的女性世界里,至少孩子可以奇妙地存在。与此同时,女人们还可以不受干扰地持续进行创造性探索,而又不违反艺术准则。
我认为,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助长了大量关于“艺术生活”的神话阴魂不散。20世纪60年代,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向我们灌输的仍然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是由禀赋不凡的人书写的,他们与普通大众全然不同,其中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是天才。与此同时,又有人告诉我:“文学不是生活。”作家的作品被横刀切断,漂浮在超空间中,与作者没有丝毫关联。这些作品被称为“精心制作之瓮”,它们是可以自行产生的人类器物,被封死在密闭的空间里,这个空间有一个名字:不朽。艺术从未与现实世界相关联。但这是个错误。我们没有能理解,艺术就是生活;它由数以百计的家庭小摆设、景观和记忆共鸣和合而成,构成了我们自身的存在。
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开始对女性发出的声音产生了极大兴趣:它们是否被人听到了;它们是否被听者歪曲;它们是否从说话者身上充分显现出来,或是因为自我怀疑而被削弱。
如果你听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话,你就一定会记得她的声音。她说话语调单一,面无表情。这种声音经常被模仿成百无聊赖、居高临下或不屑一顾,因为如果你不仔细倾听,往往会错失其中的风趣机智。她往往表现得成熟老道,足智多谋,拒绝被逼入绝境,因为她清楚这是世人的试图。这个声音清楚地表明,这个女人不会耐着性子听愚蠢之人的唠叨,并很可能极尽讽刺之能事反唇相讥。但是,在得到一个真诚的回应时,她也会表现得坦率直接,令人为之惊叹。
多年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是许多形象化描述的对象。一开始,她被形容为拉斐尔前派,有着随风飘动的秀发。但这一人设从来没有真正起到过任何作用,因为她缺乏维多利亚时代女主人公的绵柔温顺。此外,她总是在纳闷,什么样的男性作家头发会成为每篇评论文章的关注对象。后来,在她写出《权力政治》一书时,人们称她是惊世骇俗的绝代天才,目光犀利。她也曾被描述为“厌世者”,“她的东西暗淡、黑暗、消极。”再后来,她被形容为“趣味盎然”,最后,她又变得“充满母性”。 随着时代的变化,对她的人设描述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她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还是那个阿特伍德。
面对这一连串的攻击,很多人或许会被激怒,但她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不屈不挠地继续前行。当然,幽默感肯定给了她很大帮助。但让她能够持久保持不懈韧劲的真正原因是,一直以来,她都有一种内在的自信,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深信不疑。事实上,她的言行始终如一。她的声音是加拿大人的声音,是女性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她的声音唤起了某种独特的顿悟,在读者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
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看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站在一座桥上,丛林在她的背后,城市在她的面前,她同时支配着两个世界。水下有尸体,桥下有巨魔。当然,这是我虚构的一个荒谬形象,但它让人联想到一个女性的形象,由于多年的培养和专注于此,这位女性的写作有着深厚的神话根源。她说话犀利,其中隐隐蕴含着挑衅的乐趣。她为人坦荡直率。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
我认为这本书是一种思考,旨在探索一个特定女性对她所在文化及其读者所具有的意义,她纯粹通过写小说的行为进入了读者的生活。它旨在通过探索,努力发现造就作家及其写作生活的奥秘,同时伴随着喜悦之情,观赏一位杰出作家的职业生涯图景徐徐展开。
与此同时,与第一个故事如影随形的还有第二个故事。这本书也是对新一代的写照。阿特伍德开始她的职业生涯时,加拿大人还处于殖民主义的冰封之中,才刚刚开始意识到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她这一代人使一切改观。
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个被过度描述却依旧难以把握的十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60年代被形容为战争和迷幻药的十年(当然,这是故事的一部分),但也不乏其他叙事。随着60年代世界各国兴起解放伦理,这一思潮当时似乎同时冲击了所有地域,但加拿大却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那是加拿大文化民族主义的时代,加拿大已不同以往,再也不是原先的加拿大了。
从1966到1970年代末,加拿大的文学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60年,这个国家出版的小说数量用一只手的指头就能数得过来。诗集会多一些,这是因为诗集的制作成本相对低廉。到了1966年,小型出版社、文学杂志和新剧院开始如人们日常食用的蘑菇般迅速涌现,风头强劲。到上世纪70年代末,加拿大作家们有了明确的文化归属意识。曾经被诺斯罗普·弗莱失望地称为“长在想象力根基处的冻疮”的殖民主义思想已然复温痊愈,充满自信的本土文化随之出现。
那时候出现了许多特立独行的年轻人,阿特伍德就是其中之一。对她写作生活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文化和一代人的叙述。
这本书记录了一位女性作家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写作经历。它止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已经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国际作家。那个时候,滋养了她的文化也因天时地利,得到了应有的承认。戏剧性的开头总是最能引人入胜。阿特伍德曾经这样评价那些岁月:“一切都十分开心有趣,但至关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事实:我们自身作为加拿大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