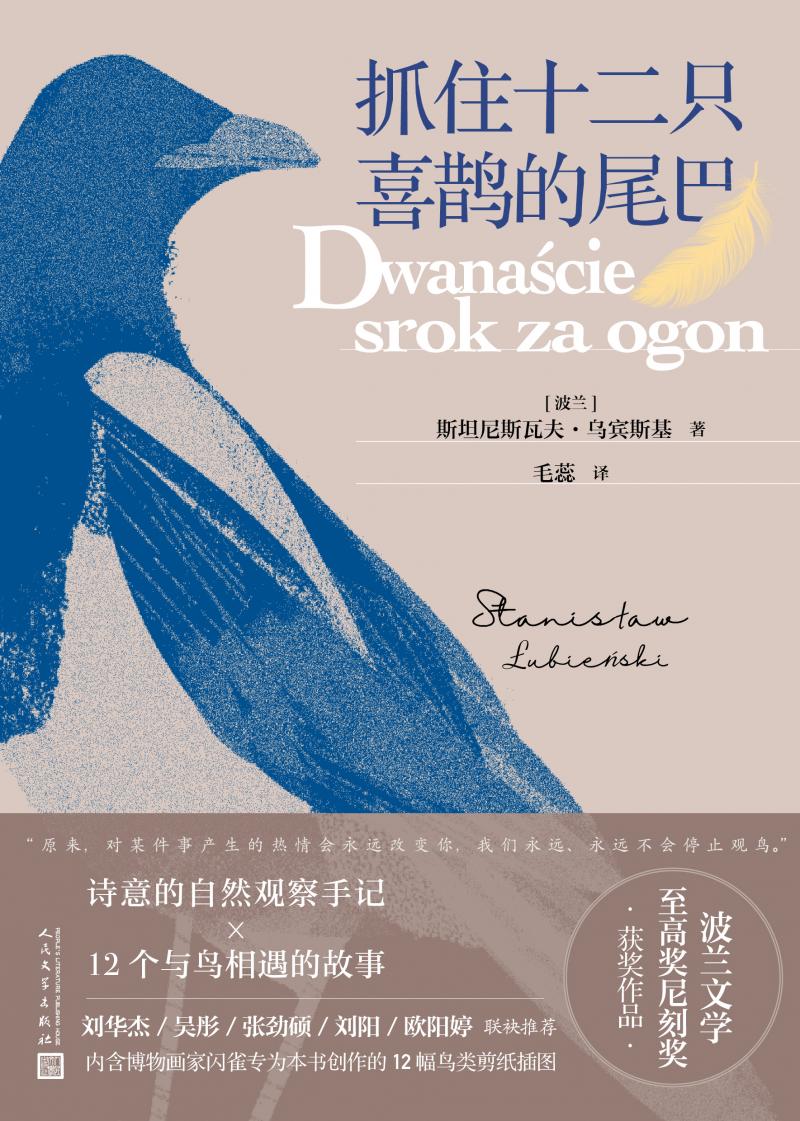库尔皮的这栋老房子,窗棂被虫儿蛀得千疮百孔,只剩下点点斑驳的蓝色油漆。每年春天我来到这里,都会感叹这老房子虽奄奄一息,却仍屹立未倒。老地方除了老房子,还有老朋友。总是这只啄木鸟,锲而不舍地敲打着窗棂,把我从梦中唤醒。这些年来,它大概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储藏室了吧。它还是那片白桦林的常客,风初起时,树枝摇曳,树叶沙沙作响,而当风呼啸,白桦林也变得躁动不安,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我把我的红色吊床挂好,鸟儿们很快就接受了它的存在——有一次,一只只顾着追蝴蝶的欧歌鸫差点一头栽进里面。白桦林的邻居是一片杨树林,树叶总是怯生生地沙沙作响,哪怕风止时树也不静,仍然颤巍巍的。只有老橡树站得笔直,沉稳坚毅的它们绝不会向突如其来的风低头。
一只老鼠拖着一团干面条从杂草丛生的门边经过。白天,处处宁静安详,狐狸十几年前就从哈尔伯特卡销声匿迹了,落叶盖住了它们旧居的洞口,洞穴内的通道常年无人问津,也早已塌陷。黄昏降临,老鼠就无法像白天一样镇静自若了,因为这里会被两只黑眼灰林鸮接管。它们一只橙棕,一只灰褐,总是形影不离。哪怕有时不同时出击,也会先互相通个气,商量捕猎计划。它们俩应该住在一只黑色啄木鸟留下的旧巢中。话说就在昨天,我又听到了那只黑色啄木鸟久违的鸣叫声,上一次听到它那余音袅袅的呼唤还是在好几年前呢。黑顶林莺在腐烂的茅草屋外踱来踱去,对于要和人分享这块领地显得不太情愿。“喳喳喳”,它一边拨弄着头顶的黑羽,一边瞪着我,喋喋不休地表达着不满。乌鸫也不太欢迎我——只要我稍稍向黑刺李丛迈出半步,它就立马尖叫着落荒而逃。虽然它像个惊慌失措的逃兵,但我仍对它充满敬意——因为我看到过它是如何马不停蹄地奔波终日,只为给孩子们觅食。有时它刚把衔着的蚯蚓喂到孩子嘴里,脚都没站稳,就又飞去寻找新的食物了。它的心焦也情有可原,这是它孵化的第二窝,又比预想的要晚,而寒冷的冬夜就要来了。
“小恶魔”雀鹰也会不时光顾。它最喜欢待在屋顶上方的干树枝上,目光锐利地四处张望。它做任何决定都是雷厉风行的,看来雀鹰世界的运转速度可比我们快多了。不小心脚下一滑,它突然从枝头跌落,却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个空翻便再次敏捷地穿梭于枝间。就在这时,我见它贪婪地伸出利爪,想要一把抓住上下翻飞的欧洲丝雀和红额金翅雀。但这一次却没能成功,它只能若无其事地飞向河边。也许在河岸的灌木丛中能抓到一只毫无戒心的小倒霉蛋吧。
*
这片名为“哈尔伯特卡”的土地有什么特别之处? 据说,这里的继承人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在小丘之上边品茗边欣赏整个河谷的全貌。老屋后的那些橡树总该记得他吧——我不知道在那里爬上爬下多少次,一到秋天就投下一颗颗橡果,砸得满地砰砰乱响。林中的松木十字架总该还记得他吧——那是为了纪念某位在一战中牺牲的无名战士而留下的,当地人都说,哈尔伯特卡的夜晚不太平,常有灵异事件发生。这片森林是采蘑菇爱好者的乐园,然而哪怕珍贵菌菇的吸引力再大,也没有人愿意晚上过来。
此时此刻,我体会到继承人的快乐。站在山顶,河谷草甸与原始森林如一块块马赛克艺术拼图镶嵌在眼前。向南望去,树木枝叶间隐约可见斯特罗米耶茨教堂高耸的尖塔。向西是同样高耸林立的科杰尼采发电厂烟囱(这可是继承人当年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河岸边的一片桤木林中,一阵鹤鸣打破了夜的宁静——它们肯定住在河对岸,就在以前摆渡船停泊的小木屋后面,木屋的房间看起来就和凡·高那幅《卧室》别无二致:一桌一椅一床,仅此而已。
河岸边有一片果园,一直绵延到山脚下,与草甸相连,我们以前经常在圣母升天节的时候来这里采摘野花。给拖拉机走的路是用废弃的石棉瓦碾碎铺成的——众所周知,这种材料对身体有害,但离这里最近的房子也在200米开外,哪怕有毒也伤害不到当初丢弃这些材料的那位仁兄(再说了,如果只把它扔掉而不再利用的话才是真正的浪费)。茂密的桤木林右边是一片近年来特别流行的水果——野樱莓种植园。站在岔路口,我选择向左走,一棵棵柳树如同高筑的城墙,把后面的河水挡得严严实实,不一会儿就走到了桥边,这里应该是整片森林中最原生态的一段。河床边是一大片宽广的浅滩,我记得曾和父亲沿着上游走了几百米。在我的记忆中,这里就像亚马孙雨林。藤蔓盘根错节,灌木丛密不透风,整片绿色小岛不曾有任何人类踏足。我那时疯狂迷恋小巧美丽的黑头芦鹀,以前我们把它们称为小苇雀。我从早到晚喋喋不休,张口闭口都是“小苇雀”,结果到了晚上我就开始发烧了,然后接连一个星期病得起不来床。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是着了芦鹀的魔。
我们一般都会沿着水草丰沛茂密的古老河床向右走。从匈牙利归来后,我们就一直把这片草甸称作“普斯塔”。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片草甸无边无际,特别是在夏末,草色渐浅,渐渐与天际相连。有人在这里搭建了球门,可是我从没见有孩子来踢球。这里以前是一片牧场,而如今整个村子连一头牛都没有了。
“普斯塔”变了,十几年前,从春季到六月,这里每年都会形成一片湖泊。我还记得那时这里聚集了成百上千的鸟,一群群北极燕鸥扇动着闪闪发光的羽翼,从湖上翩翩掠过。当水位下降,河流在展示了自己充沛的力量之后,心满意足地重归河床,草甸上除了铁锈色的长嘴黑尾鹬外,只余凤头麦鸡那惊慌失措的身影。只要有一丁点风吹草动,它们都会伸展开圆润的翅膀,东摇西晃地仓皇起飞。我还特别喜欢它们如泣如诉的叫声,让人想起给旧收音机调频时断断续续的信号声。
这里的河水水位很低,将将没过覆盖住泥泞河床的浮萍。我把衣服顶在头顶,不顾水中泥泞,大踏步地蹚过去,一心追逐那些机警敏感而又难得一见的林鹬,夏天的时候它们最喜欢在黏腻的岸边泥塘里穿梭。这里还是一群黑浮鸥的领地,当入侵者靠近它们的巢穴,它们依然无所畏惧。伴随着厉声呼啸,这群家伙会俯冲而下,掠过途经此地的人和动物头顶。一只心思缜密的白头鹞看似在悠然飞翔,实则放慢了速度,在草丛中找寻着老鼠或鸟巢的踪迹。
当水位不断升高,河床看起来黑洞洞的,令人望而生畏。河段转弯处堆满了垃圾,有老旧的冰箱、破损的马桶盖,还有挂在低矮树枝上的脏裤子。那些布料脏兮兮的,都褪色发白了,远远看去差点儿让人以为是在捕捉小鱼的苍鹭呢。
夏日里,河水缓缓流淌,卷着河底微黄的泥沙淙淙拍岸。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滩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大,鸻鸟像上满发条的玩具,在那里一路小跑。索科沃夫斯基曾写道:“它一秒之内能走九步。”水面上,翠鸟像离弦的翠绿羽箭一闪而过,说它出生在天寒地冻的时节其实是误传,说它是在“地洞”里出生的还差不多,确切地说是在河对岸的沙坡洞里。从村里开来一辆辆拖拉机,将这河滩据为己有,拖走一片片沙地。他们可曾问过这河中的泥沙,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说什么也没用了,河滩就这样消失了。
旧的河道已经被水生植物盖得严严实实,今天在岸边肯定找不到凤头麦鸡了。草甸不再任由温柔的奶牛轻轻啃食,而是被轰鸣的割草机无情地砍去。每年有数以千计的鸟儿命丧割草机锋利的刀片之下,或死于接种了狂犬疫苗的狐狸之口。夜幕降临,狍子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在高高的菖蒲丛中做窝,此时传来一阵阵如同猪叫的怪声,这可能是在波兰自然界中最奇怪的声音:原来是沼泽中的隐者——水秧鸡,它们总是在夜幕降临之前大声宣告自己的出现。
*
黄昏时分,随着彩霞散去,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当最后几缕霞光褪去红晕,黑暗中唯一可见的只有黄色鸢尾的光芒。雾霭俯身拥抱大地,带着一丝黏腻,在闪光灯下甚至可以看出水汽中漩涡状的原子结构。森林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噼啪声,接着又是树枝断裂的声音,再然后是狍子七嘴八舌的叫声,听起来像喝醉了酒的球迷在胡言乱语。
鸟儿的私语渐渐消失了,芦苇丛中的窸窣声也戛然而止,只剩下一只不知疲倦的夜莺还在坚守岗位。一只长脚秧鸡“嘎、嘎、嘎”地加入了夜莺的独唱。草丛深处传来几声带有金属质感的鸟鸣,那是河蝗莺,听起来更像是昆虫发出的声音。这样的交响将一直持续到天亮:夜莺、长脚秧鸡、河蝗莺是主角,时而会混进一两声姬田鸡的低吟浅唱。
凌晨四点天就开始蒙蒙发亮,奶白色的雾气笼罩着地平线,能见度降至三十米。欧歌鸫醒了,反复吟唱着千篇一律的乐章,仿佛日日都在排练同一首断断续续的歌。河蝗莺暂时停止了单调的鸣唱,它需要在枝头换个位置。长脚秧鸡正一步步靠近,除了刷羽声,它还发出了奇怪的嗡嗡声,仿佛是从录音带里播放出来的。我看不清它的样貌,只能欣赏它轻盈的舞姿,所到之处寸草不惊,只有草尖上的露珠轻摇几下,耳边只听得到它那纤长的脚趾轻点草地发出的簌簌声。
受惊的长脚秧鸡宁愿大步流星地逃跑也不愿振翅而飞。一次,当我捧着一只长脚秧鸡的近亲——水秧鸡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和小巧的身体比起来,它那肌肉发达、强健有力的双腿是多么不成比例。当我将它放飞,它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前飞奔几十米,方才腾空而起。它跑起来的样子别提多像一只母鸡了(话说回来,母鸡也有很强壮的腿)。
这时,一只藏在草丛中的长脚秧鸡围着我转来转去,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它的叫声可高达一百分贝,我感觉耳膜都被震得一抽一抽的。刹那间,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长着小尖嘴的小灰脑袋从草叶中探出来,转眼间又消失不见。不一会儿,“嘎、嘎、嘎”的声音传来,它已在五十米开外了。我知道,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了。我慢慢后退,回到林边,望着这只无忧无虑的鸟儿低飞过草丛,两条粗壮的腿无力地耷拉着。过于短小的尾巴令它无法完美刹车,它像一个减速中的滑雪运动员,在完成了一次垂直于飞行路径的转弯之后,跌跌撞撞地倒在了草叶之间。
快五点了,河蝗莺的声音渐渐淹没在成百上千种鸟鸣的喧嚣中。我像一只淋过雨的小狗,身上沾满了湿漉漉的草叶,被露水打湿的裤子紧贴在腿上。在雾中很难判断距离,声音穿过草甸,听起来与晴日时完全不同。每走十几米我都会停下来,感觉河蝗莺就近在咫尺,然而目之所及,却一无所获。它依然端坐在几十米开外的枯树枝上,仿佛周遭的整个世界都不存在。它歪着头,放开嗓门,大声演唱着单调的金属摇滚。
编辑/韩世容